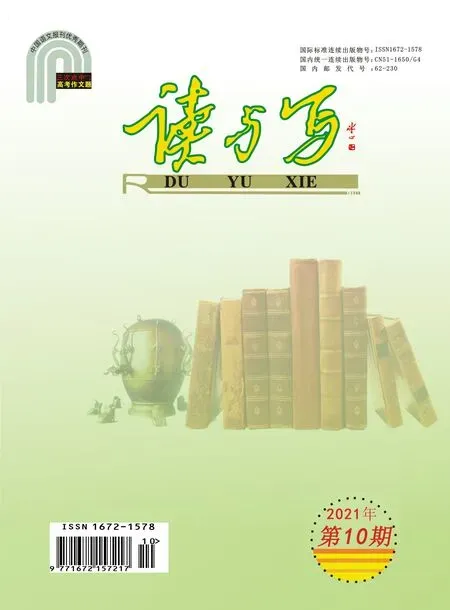曼斯菲爾德小說中的女性主義主題
——讀《一杯茶》有感
謝寶花
(廣東省東莞市高埗鎮低涌中學 廣東 東莞 523270)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文化女性主義者,英國最著名的短篇小說家,同時也是新西蘭文學的奠基人。她的作品關注女性的生存處境和情感世界,通過呈現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被動地位,刻劃了心理和經濟上處于雙重困境中的女性形象,體現了男權社會對已婚女性的操縱、愚弄和精神扭曲。
女性主義(Feminism),又稱女權主義,是主要以女性經驗為來源與動機的社會理論與社會運動。女性主義認為:現實社會建立于父權體系之上,給予男性比女性更多的特權。“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會和文化人為地建構起來的。
曼斯菲爾德以善于寫作女性主義主題的短篇小說著稱。20世紀初,以她為代表人物的女性主義作家對當時英國文學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意義深遠的推動作用。
1.歷史文化背景和作者生平
談到女權主義運動的由來與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創作生涯的關注所在,就不能不提到維多利亞時代。
維多利亞時代,即維多利亞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1837年至1901年)統治時期。其時是英國的黃金時代。工業革命使英國在國際上處于政治軍事強權地位,國內涌現出大量人才。這一時期文學藝術空前繁榮,整個社會崇尚道德修養和謙虛禮貌。
19世紀末20世紀初,維多利亞時代的舊傳統受到挑戰。婦女解放運動的第一次浪潮興起,形成了男女平等和種族平等的進步觀念。爭論的一個焦點是強調男女在智力和能力上是沒有區別的。其主要目標是爭取家庭勞動與社會勞動等價、政治權利同值,因此也被稱為“女權運動”。同時,底層人民也開始要求公民權和政治權利,反對貴族特權。
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后來享譽英國乃至世界文壇的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其中曼斯菲爾德是不可不提的一位小說家。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出生于新西蘭,15歲到英國倫敦求學。20歲時,她說服父親同意她定居倫敦,開始寫作生涯。但現實生活遠非如她所想,她時常感到孤寂無助。第一次婚姻僅維持一天即告終。她的人生經歷,讓她對當時英國女性所處的心理和經濟上的困境感同身受。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被譽為二十世紀杰出的英國短篇小說作家之一。當時及后世的文人學者對她一直不吝贊美之辭:“(她)通過女性獨特的視角和體驗方式,用女性話語發出女性自己的聲音。”[1]
下面就以短篇小說《一杯茶》為例,分析曼斯菲爾德的小說如何呈現了女性主義主題。她在小說上的創作,又是怎樣與當時的英國文學和文化遙相呼應,并對后者產生了意義深遠的推動作用。
2.分析短篇小說《一杯茶》
羅斯瑪麗是個時髦、闊氣的少婦。某次購買奢侈品未果,路遇一個窮困少女向她討一杯茶錢。她為了顯示自己的人格高尚,把少女帶回了家。但中產階級與社會底層地位有別,丈夫菲利普并不贊成,便故意在羅斯瑪麗面前夸少女很標致。羅斯瑪麗大吃一驚,立即將其打發走,然后精心打扮一番去見自己的丈夫。
羅斯瑪麗并不美貌,靠著青春和時髦,苦心經營著世人眼中的成功人生。但一件精美的小擺設需要28個幾尼,便令她望而卻步。她得向丈夫要這筆錢。
小說里這樣寫道:“……凝視著這冬日的下午。雨下著,……周圍刮著凜冽的寒風,因而燃明的燈也顯得很慘淡。……羅斯瑪麗感到一種莫名的痛楚。她把她的皮手筒按在胸前,她真想要那小匣子。”[2]為什么沒有凍餓之虞,一件小擺設便令她感到痛楚?因為她的渴望,必須絞盡腦汁討好丈夫,換來金錢,才能如愿。那一刻,她感覺到了挫敗感。
這時,凍餓困窘的少女戰戰兢兢地來討要一杯熱茶的錢。羅斯瑪麗生出了同情心。她的挫敗感,可以從比她更不幸的少女身上得到補償。她邀請少女到她家去,小說里寫道:“她體會到一種勝利感。……她準備向這個少女證實,……仙女教母是存在的;證實,富人也有慈悲心腸;……”[3]
她與少女年紀相當,卻自居為仙女教母。當她把少女帶進自己家時,“羅斯瑪麗以優美的、愛護備至的動作扶持著那一個進了大廳。”“平易自然可是件了不起的事。”[4]
羅斯瑪麗一直在為自己的開明和風度而沾沾自喜,可見她是新潮人物,炫耀著自己親近底層的姿態,享受著雙方的強弱懸殊給她帶來的財富、地位、教養等方面的優越感。在這里,作者并沒有直抒胸臆去批判,而是采用了接近俄國現實主義小說的做法,追求文字簡潔,意在言外。羅斯瑪麗的言行矯揉造作,反映了英國中產階級的虛偽,對地位不如自己的人是不著痕跡地碾壓。
小說接近結尾,男主人登場了。
羅斯瑪麗的丈夫菲利普回來了。看見衣著寒酸的陌生少女坐在自己家里,他“睜大了眼睛”,卻處處彬彬有禮。他把妻子叫出去,問她打算怎么辦。當聽妻子說打算幫助對方時,“我的寶貝,”菲利普說,“你是真的在發瘋,你知道。這簡直不可能辦到。”[5]
羅斯瑪麗覺得自己是這個家的女主人,可以決定些什么,那是錯覺。在這個家里,丈夫叫她是寶貝,下一句便指責她在發瘋。妻子被當作無理取鬧的小孩子一樣,丈夫不需要尊重。菲利普太清楚該怎么操縱妻子了。他暗示少女“很標致”,讓自己很動心。
羅斯瑪麗是那么吃驚。她甚至都沒有感到生氣,而是惶惑,后悔自己考慮不周。她給了少女3英鎊,把對方打發走了,然后精心打扮一番,去見丈夫。丈夫這時對她的表現滿意極了。羅斯瑪麗“神情恍惚”,問丈夫自己標致嗎?
她不夠標致,又沒有經濟來源,人格上被丈夫牢牢控制著。《一杯茶》成功地塑造了心理和經濟上處于雙重困境的女性形象,體現了男權社會對已婚女性的操縱、愚弄和精神扭曲。在曼斯菲爾德的所有小說中,這篇小說較為知名。20世紀60年代,兩種最權威的英語教科書都選取了它用做語法練習文本。
3.結論
20世紀20年代,曼斯菲爾德因短篇小說而成名。她的作品脫離了傳統小說的題材形式,著力于對日常生活的記錄,多以關切女性的生存和命運為主題。其敘事風格與英國傳統短篇小說極不相同,以細節刻劃見長,能很好的披露女性內心歷程,深刻精辟地描摹人物關系。言簡意賅,見微知著,世人認為她的創作風格更為接近契訶夫等俄羅斯名家。這一切推動了當時英國文學的改變。維多利亞時代結束后,是曼斯菲爾德以自己眾多作品呈現出來的女性主義主題及寫法上的探索,豐富了英國文學的敘事主題和敘事技巧。自此英國短篇小說面目一新,開始廣受世人矚目。
維多利亞時代后期,英國最重大的時代主題之一,便是男權社會所帶給女性的屈辱感和心靈創傷,由此男女平等的呼聲日愈高漲,終于發展成為如火如荼的女權運動。曼斯菲爾德的小說,與時代主題息息相關,可視作是對其時英國文化、人情百態和道德價值觀最為貼切、冷靜的注解。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被譽為20世紀最為著名的短篇小說作家之一。她刻畫了廣大女性在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所迫下產生的孤獨感、幻滅感、恐懼感和她們的叛逆與反抗,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息息相關。
同時代的作家如詹姆斯·喬伊斯(1882-1941)、D·H·勞倫斯(1885-1930)、維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在小說領域的探討似乎更為極端,過分追求不同于流俗,普通人也就更難以理解和親近。其中伍爾夫,作為意識流和印象派文學的代表人物,被譽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與曼斯菲爾德可謂是20世紀初英國文壇的雙生花,同以女性主義主題見長。而曼氏35歲因病離世,伍爾夫59歲自殺,更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人生命運對所處的男權社會作出了文如其人的反抗,最終以靜默無聲卻又轟轟烈烈的謝幕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