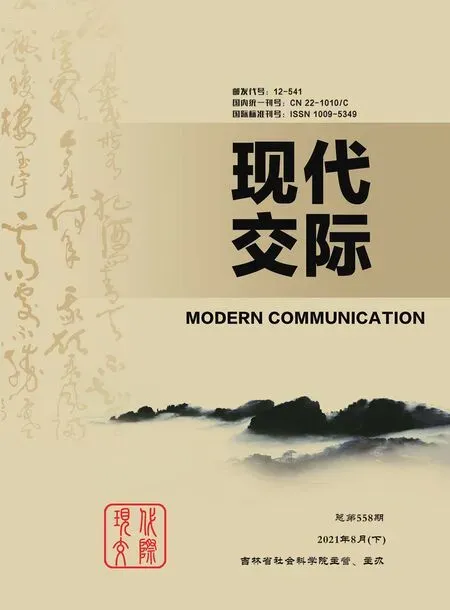自由始發、困境和歸宿
——基于弗洛姆自由思想
張涵婷
(安陽職業技術學院 河南 安陽 455000)
埃里希·弗洛姆認為人類的存在和自由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在近代人類歷史文明中,人類始終在追求真正的自由,并將擺脫政治、經濟等外在束縛作為爭取自由的核心。而在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明都有了長足進步,人類也邁進了更加民主化、獨立化、個體化的階段,但人們沒能享受真正的自由,甚至出現了孤獨、恐懼等逃避自由的心理狀態,這點引人深思。自由,究竟緣何成為人們逃避的對象,這儼然已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經濟問題,其在蘊含人文關懷價值的同時,究竟在人的心理層面上經歷了怎樣的變遷?
一、自由的始發——前個體化階段
在個人生命的歷史中,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人把自身看作獨立的存在物,在對自身的認識和評價的過程中不斷完善和修正其對自由含義的理解。最初,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渾然一體,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個人身心功能的發展,人們將逐漸意識到自身與自然、社會、他人相分離。雖然人對“自己是獨立的個體”有部分的意識,但仍和自然界、社會有密切的聯系,仍將自身看作周圍世界的一部分,在這里將這一時期稱作“前個體化階段”。
(一)家庭組織中的自由
從生物學角度來說,人從出生之后就成了一個嶄新的個體,與母親的身體處于相分離的狀態。但從功能層面上來說,嬰孩與母親的關系并沒有達到徹底的分離階段,他們仍需要母親的照料和養護,即兒童與母親是一體的。家庭組織給孩童提供了安全的保護,以及周圍世界相聯系的基本條件。但家庭教育和要求并不妨礙和壓抑孩童對外界產生興趣,他們雖然意識到與周圍世界、人相異,卻并沒有明確體會到“別人”與自己的真正區別。
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曾經提出三個重要概念,即“本我”“自我”和“超我”,分別代表了本能的我、現實的我和理想的我。人們在兒童時期總是與父母、家庭維持著密切的情感聯系,自我才剛剛形成,并隨個人身心的發展而得到不斷加強,但并沒有強固到能夠指揮本我的程度,此時兒童就需要通過借助父母、家庭的力量來壓制本我的沖動,父母所展現出的權威在兒童看來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不管是對于父母家庭的教育,還是其他權威類似的刺激,兒童都足以將其納入自己的“宇宙”,這個宇宙是孩童生命的一部分,服從于它與兩個個人完全分離時的那種服從狀態有著本質差別。換句話說,孩童的“宇宙”與世界仍是不可分割的關系,沒有個人行動的必須和責任,也就用不著害怕,他們不必獨自面對外界的危險和壓力。正是這種內心無壓力的心理狀態,使得人們在孩童時期享有最初的自由,其所感、所想、所為、所識皆出自本心,世界對于這一階段的人來說,意味著無限的可能。
(二)傳統社會中的自由
從社會發展歷史方面來說,在傳統社會中,個人與自然、部落、宗教渾然一體,這些原始的組織、紐帶為人類提供了有組織的整體固定位置,個人將自身定位于原始部落、組織、共同體的一部分。在此類的傳統組織中,個人能夠與周圍社會、自然世界建立一種和諧無間隙的聯系。
弗洛姆認為,西方中世紀的人們是不自由的,但他們并沒有感覺深入骨髓的孤獨,因為傳統社會中的人一出生,就在社會中擁有固定位置,身處一個結構穩定的整體中,給人們提供了自在明確的生活意義。[1]人們獲得了一種生存的安全感,在生活上有明確安全的保障。個人身處頗具限制的社會范圍之內,事實上能夠在勞動和情感方面擁有很多自由來展示和表達自己。由此可見,在中世紀的西方傳統社會里,傳統的社會秩序、固定不變的社會地位、宣揚福音的教會等,在給人以原始束縛的同時,給予了完全的安全感和明確的自我定位,使得人們在享有一定范圍內自由選擇生活方式,雖然自由是以犧牲個體性為代價的自由。
二、自由的困境——個體化階段
弗洛姆認為,先于個體化進程存在,并導致個人完全出現的紐帶稱為“始發紐帶”,諸如家庭、原始組織、宗教共同體等紐帶給人們帶來歸屬感和安全感。[2]然而,隨著個人逐漸從“始發紐帶”中解脫出來的同時,需要面臨新的任務和挑戰,即對自我進行重新定位,人由此成為真正的“個人”,并致力于尋找新的不同于“前個體化階段”更為安全的存在狀態和方式,此時的自由含義與“前個體化階段”的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個人在掙脫“始發紐帶”的安全束縛的同時,真正進入“個體化階段”。
(一)自由成為權力的面具
一切權力斗爭都反映了某階級的利益和價值追求,弗洛姆認為歐美歷史爭取自由的階級斗爭都有積極的一面,如廢除專制統治,解開封建束縛。自由的斗爭往往是在被壓迫階級和特權階級之間進行,而自由的結果則是權力所有人的更替,自由作為人類社會中政治斗爭的工具,作為一面旗幟號召人們反對壓迫獲取自由。諷刺的是,一旦權力到手,當初揮舞自由旗幟的領導者卻舉起權力的大棒,成為新的統治階級。這種自由掩蓋下的權力欲望使得人們在自由的斗爭中屢戰屢敗,歸根結底,真正的自由實現的基本條件不僅依賴于外在的專制統治的廢除,更依賴于人的權力欲望的根除。
從心理學層面來看,人們內心的權力欲望來源于軟弱,而非力量。對此,弗洛姆明確指出了一點,“權力”具有兩層內涵,一方面是擁有統治的能力,并有統治的權力;另一方面是擁有權力做某事,是指有能力去做,能夠做到。[3]其中,后面一種含義是指人在能力方面是否勝任,這與統治無關。盡管看起來自由在人類的權力斗爭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屢屢成為人們爭取權力的旗幟,但一旦了解到其中所包含的自由與權力欲望的關系,就不難明白自由在階級斗爭中注定最終被拋棄的原因,那是具有權力欲望的人們在政治斗爭中利用自由的面具把戲,也是人在個體化階段面對自由問題的孱弱表現。
(二)自由成為難以忍受的負擔
在經歷個體化的過程中,人總被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因素所影響,弗洛姆指出,如果整個人類個體化進程所依賴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沒能為積極意義上的個體化實現提供基礎,人們同時又失去了為他提供安全的那些紐帶,這種滯后便使自由成為一個難以忍受的負擔。如封建社會的社會現實雖與現代意義上的自由精神相悖,但對當時的人們來說,并不妨礙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做出具體的個人主義行為。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從傳統紐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越來越獨立和自主,但個人在被賦予最大程度的自由時,也同時被切斷自身和他人之間的紐帶,自由成了難以忍受的負擔,個人反而陷入到了孤立和焦慮之中。
人在個體化進程中,在心理層面上將呈現出與之前不同的生命狀態,首先,個人從“始發”紐帶中解脫出來,意識到自己身為個體與別人是相分離的,會產生一種微不足道的無力感,對生命產生越來越多的懷疑。其次,作為個體,在失去“始發”紐帶的束縛同時,擁有了自由管理自己的權利。這種自我領域為個人的自由提供了舞臺,個人傾向于在孤獨中展開自我交流,在獨立的思考中接近完整的自我,但對不懂獨處的人來說,這種孤獨的自由會成為最難忍受的負累。再次,個人在處理內在世界之外,還要處理外在世界的疏離問題,人擺脫大自然的束縛,沖破宗教等神秘因素的控制,不斷地取得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等。如經濟方面,社會允許并期望個人獲得經濟成功,這種成功甚至成為個人的生活目的,而在人人皆敵的經濟競爭中,個人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敗,個人與外界走到對立面上,個人在世界中的自我定位是充滿挑戰且變動的,隨之而來的孤獨感可見一斑。
三、自由的歸宿——后個體化階段
自由是人類永恒的追求,人類的歷史發展存在于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從前個體化階段到個體化階段,個人在理解和追求自由上不斷變化。針對人類追求自由的本性和逃避自由的行為矛盾,弗洛姆提出要從積極意義上來追求“自由地發展”,進而創造性地提出一個個體化階段的人處理與世界關系的解決方案。
(一)消極自由:兩種逃避機制
1.放棄自我的權威主義機制
“始發紐帶”的瓦解,人的個體化出現和完成,均是無法扭轉的客觀事實。人們失去“始發紐帶”,失去安全歸屬,只有再次尋找新的“紐帶”來代替。于是出現逃避自由的一種方式,即為了獲得自我欠缺的力量,放棄自我的獨立性,需要依傍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即“權威”,這個“權威”是指個人在與人相處的過程中,將對方看作比自己更具優勢的個體,但不僅僅是指財產、身體等方面的優勢。權威主義包括外在、內在和匿名等多種存在形式。外在權威是易于發現的,其存在命令、責令似的指示,內在權威則更為隱蔽,常常以責任、良心、道德等面目來偽裝。匿名權威比外在權威和內在權威更具影響力,它裝扮成常識、科學、輿論等形式,對于人們的行為不必施加任何壓力,就可以達到完美的束縛效果,因為這些內化了的權威所營造出的氛圍充斥了人們的社會生活,也就沒有擺脫此類束縛的意識了。
2.消除自我的機械趨同機制
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在政治、經濟相對開明的民主氛圍中,個人從外在的限制和束縛解脫出來,個人也理所當然地保存其完整的個性,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大多采用機械趨同的方式來逃避自由,所謂機械趨同就是指個人為了融入周圍的社會環境中,為了能夠與他人、自然、社會建立和諧的聯系,而不惜放棄自身所獨有的個性,而去承襲社會文化模式所給予他的人格特性,從而減少自由帶來的孤獨和焦慮感。機械趨同具有隱秘性的特征,一方面個人在此心理機制的主導下,會從主觀意識上認為自身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個人會不斷地失去自我和批判意識,其真正的個性和自我感覺也會受到壓抑。現代社會的人們總認為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是自由的,但弗洛姆通過催眠實驗發現,很多人主觀上認為是自己的思想意識內容,實際上是被灌輸和影響的。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安和恐懼感可以在這種機械趨同的方式中得到寬解,只要將自己的所思、所感、所想塑造成別人期望的狀態,自己就可以獲得安全感和歸宿,但同時也放棄了原本的自我,與真正的自由也失之交臂。
(二)積極自由:追求自發活動
弗洛姆對自由問題的思考不僅著手于社會歷史發展層面,還從心理學層面剖析了他對自由思想的見解,他堅信真正的自由是可以實現的,認為獲得自由的方法在于一種自發性的活動,即他所提倡的“積極的自由”存在于人的自發性活動中。自發活動不是強制性的活動,而是代表了愛與自發,屬于自我活動的自由開展,其中的思想觀點、感情內容和行動目標都是一種真實的表達。[4]
首先,“愛”是自發性活動的核心。“愛”可以使得人們之間的關系更加融洽,是在保存個人自我和肯定他人的獨立性的基礎之上,與他人聯系在一起,又不泯滅自我的個性,屬于一種自發地肯定他人,愛他人的能力。正如弗洛姆所說:“生產性地愛一個人,意味著關心這個人,感到這個人的生命……生產性地愛意味著對所愛者的成長付出勞動,加以關心、負有責任。”[5]
其次,作為自發活動的要素——勞動,是一種全面發展自我個性的途徑。這種勞動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人們在這種情況下將不必依賴于權威或是他人認同,而能得到安全感和歸屬感。例如,藝術家算是能自發表現自己的人,他們的思維、感覺和行為都是自我的呈現,他們在創造性勞動中不斷肯定自我,以促使自我與他人、自然恢復形成了聯系,詮釋并獲得了自身及生命的意義。
再次,諸如愛、創造性勞動等自發性活動在對自我個性進行肯定和確證的同時,還可以使得個人與自然、社會融為一體,人若能將擁有強大力量的自我作為倚仗,將更有能力去積極地生活,以填補個性的維持與孤獨不安感之間的鴻溝。個人的力量和安全從愛、創造性勞動等自發性行為中獲得,那么這種新的安全既沒有建立在依賴外部世界的某種力量對自身保護的基礎上(如權威主義),又沒有建立在壓抑自身以求外部認同的基礎上(如機械趨同),而是建立在于保存個人完整性和個體性的基礎上。這種積極自由模式下提供的安全也不同于在“前個體化”階段下的安全,人在“前個體化”階段下接受家庭、部落、宗教組織等“始發”紐帶給予的安全和歸屬感的同時,是以犧牲自由為代價的,而弗洛姆在“后個體化”階段提出的自發性活動下的安全則不僅以個人自由為前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追求自由的消極影響。
——評《伊坦·弗洛姆》的藝術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