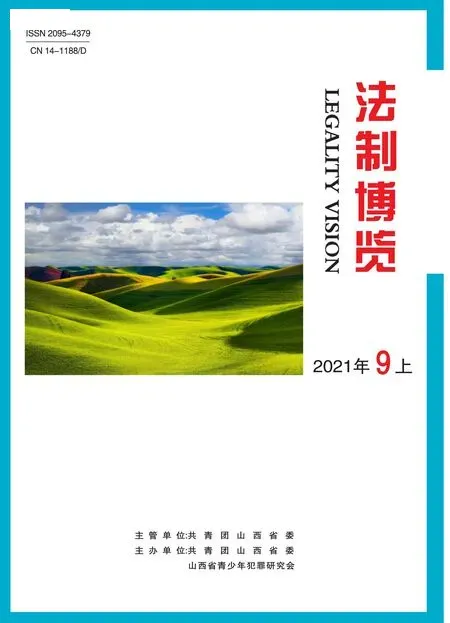消費外部性問題的經濟法規制問題分析
陳禹璇
(吉林財經大學法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隨著消費活動的不斷增加和消費對象及方式確立的不規范(如瀕危產品消費、過度包裝消費等),消費外部性的負影響隨之增加,對其的研究也不得不重視起來。經濟法治規則在市場調節方面一直有著突出的作用,其在控制市場消費外部性問題上也存在一定的優勢,因而開展其在消費外部性問題上的作用研究具有較高的現實意義。
一、消費外部性的基本概念
消費外部性指個人或家庭的消費行為對他人乃至整個社會帶來影響,但個人或家庭卻未因此獲得相應的回報及對應的補償,即消費過程中單方面產生的對外在環境的正面(負面)的作用(效應),而作用個體或團體不用回之以任何響應。消費外部性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產生主體為消費者(及其消費行為);第二,產生主體本身數量較大,且存在分散性;第三,消費外部性涉及范圍廣泛,貫穿于人們的衣食住行當中,因而正/負面的影響也較為普遍;第四,消費外部性是漸進的,可積累的,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市場環境的改變,也被經濟學家稱為“微小行為的惡行”;第五,消費外部性在消費者消費行為中產生,受宏觀消費結構水平影響,也與微觀的消費者消費習慣相關,因此消費外部性在不同消費者或區域上的體現也各不相同,其中正消費外部性和負消費外部性對比劃分在消費外部性的研究中較為常用。
二、消費外部性問題的表現
(一)綠色消費行為持續性低下
全球資源危機背景下,綠色消費為人們所廣泛倡導,從政府到商家都給予了這種消費形式以較大的呼吁與支持,希望消費者能基于環保考慮,在選擇商品時能夠有效減少有損環境的消費外部性行為,如減少一次性產品的購買等。然而由于綠色商品生產成本較高,人們考慮商品經濟性和實用性要多于對其環保效果的考察,使得這一消費行為的普及始終難以得到擴大和深化[1]。中國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在《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調查報告(2020年)》中指出我國公眾雖然普遍認可綠色消費,但是堅持踐行綠色消費的人群占比卻不甚理想,報告中有93.3%的受訪者認為綠色消費對生態保護十分重要,但僅有57.6%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而其余受訪者在現實的消費中則對商品的性價比考慮得比較多。這一情況的產生與綠色商品的較高價格有關,而不可否認一些綠色產品的質量問題也影響了消費者的購買意愿。
(二)正外部性導致成本代價大
消費的正外部性是指消費行為為外部環境帶去了正面的影響,但通常這種消費外部性無法為消費者爭取到對應的補償,有些甚至需要消費者獨立承擔較大的經濟代價,即正外部性所帶來的高成本,導致很多消費者并不愿意為這種商品消費進行買單。最常見的例子如公共設施建設、教育投資等,其中教育投資為消費者個人和家人帶去的利益是長效的、不可估量的,對社會和諧穩定發展也能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其正外部性體現得十分顯著。但教育投資的收效并非立竿見影,往往需要投資者(消費者)長期投入,巨大的成本加上短時間無法得到回報的壓力雙重疊加,常令一些投資者(貧困家庭)望而卻步。類似這樣的正外部性消費還有很多,但由于消費者需要在其中承擔較大的經濟(成本)壓力,所以比起負外部性的消費(消費行為為外部環境帶去負面影響而消費者不對影響給予補償),很少有消費者愿意主動選擇,即便是選擇了也難以堅持下去。
(三)正外部性消費行為的權益損害
正外部性消費行為不僅需要消費者付出較大的經濟成本,有時還會對消費者的其他正當權益形成侵害。很多消費者寧愿選擇負外部性消費的原因在于一些負外部性消費,如一次性商品的購買雖然對外部生態環境有著較嚴重的負面影響,但對于消費者個體而言是存在便利性的,而正外部性消費則正好相反,對消費者來說,一些正外部性消費為自己的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如進行信息消費后信息仍具有共享性,一些沒有消費的人群可以不付出代價而獲利,令真正的消費者們十分困擾,更有甚者會涉及版權保護問題,處理不好消費者的有關權益便會受到損害。目前來說正外部性消費無法完全避免這類問題,因為正外部性消費本身就對外部環境(公共環境)具有一定的服務性,當公共服務與個人利益出現沖突,消費者一些權益的損害也難以避免。
三、消費外部性問題的經濟法規制作用
(一)校正市場失靈
不論是完善的市場機制還是不完善的市場機制都有可能產生市場失靈情況。對完善的市場機制而言,一些公共產品存在非競爭性和受益非排他性(信息類產品),導致消費者不愿為這類產品付出較高代價,相對而言負外部性消費行為可為消費者帶去一些利益,因而即便會為公共環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也有許多消費者致力追逐,如生產力的發展中所涉及的諸多行業。此外一些市場壟斷現象在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同時也讓消費者不得不對一些集體非理性消費“買單”,令宏觀經濟呈周期性波動,給市場帶去短暫的失靈。對不完善的市場來說,不合理的壟斷與競爭也能造成市場的紊亂。而不論是哪一種失靈情況,都需要經濟法規制這雙“看不見的手”對市場進行調節和校正。如網約車作為共享經濟中的一個服務模式,其正外部性明顯,為讓其在激烈的車輛租賃市場中站穩腳跟,經濟法可采取謙抑規制避免其對市場機制盲從,將網約車從“不規制”導向“規制”,從而在保證其安全運轉的同時對其發展帶去促進,實現對市場失靈情況的正視和調整[2]。
(二)糾正成本溢價
所謂成本溢價即是商品成本已經超過其自身價值,這一現象的出現會對市場造成擾亂,導致正外部性的消費產生難度增加。為降低正外部性消費的成本,經濟法規制度的合理運用十分關鍵。比如規定政府提供公共物品,需要對提供物品的供應商進行一定程度的補貼,而補貼金額則來自享用公共設施的消費者,具體以稅收的形式體現。這種規定就能在較大程度上預防一些負外部性消費(不付出代價享受對商品、設施的使用)對市場的負面作用,通過降低甚至避免消費者“搭便車”行為的產生概率,保證公共設施提供商和政府的權益,進而推進正外部性消費的健康發展。當前相關經濟法規制便對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消費行為設置了補償機制,即根據消費端承載配額任務引入二次獎罰機制,將可再生能源配額和成本差距、罰金結合起來,以保證在經濟法規制度這一“看不見的手”的糾正下社會福利能達到最優水平[3]。
(三)規范預防權益損害
上文提到一些正外部性消費可為消費者帶去權益的損害,實際上這種損害還同時具備四個特點,即不確定性、無限性、不可預知性與控制性和公益性,令受到權益侵犯的消費者個體或團體的利益受損范圍、受損程度無法確定,且因為消費行為是無限持續的,所以其中產生的對消費者的利益侵犯也是無限的,同時消費者個體受損害的情況也是不可估計的,有時受到的利益損害還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質,如商品產生垃圾的隨意處置會破壞自然環境,也就是對公共生存環境的破壞。如對以上損害情形采取問責規制則傳統法律不容易在外部性問題的規制方面發揮作用,而若采用經濟法規制便能以事前方法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的消費權益損害風險,相關人員可將這兩種規制方法結合到一起,以預防和規范外部性消費導致的消費者權益損害。
四、總結
經濟法規制對于消費外部性所產生的一系列負面問題而言可以說是有效預防消費權益損害風險、調整市場波動的關鍵“操控手”,其可結合政府政策和一些項目補助的獎罰機制對正外部性消費進行引導與支持,從而抵消負外部性問題為市場環境帶來的諸多不良影響,令消費外部性問題得到進一步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