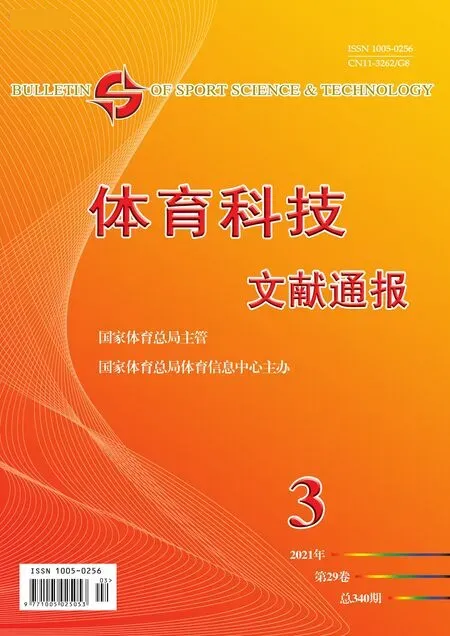體育強國背景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再出發
——民俗文化視角下滿族珍珠球運動的變革與展望
羅悅廷,張高華
前言
2019年9月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在鄭州召開,隨著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在當代被日益作為一種民族精神文化載體沿襲。滿族珍珠球運動作為一良性代表,囊括健身、協作、競技、觀賞等多種功能性于一身,既具有現代體育的社會責任感也頗具民族體育獨有的民族使命感,成為“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自1995年第五屆自治區民運會滿族珍珠球運動的首次亮相以來,2003年第七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定位為主要項目,并得到了社會各界的一致掌聲。而掌聲的背后,珍珠球卻遲遲未被大眾納入體育日常。這就務必應招致體育界民族主義至上主義者們的灌頂深思:這種民族傳統體育演進的滯后,關鍵癥候出自何處?
1 理性評釋:“泛民俗”下的珍珠球運動
民俗體育活動是我國各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依據不同的現實因素(地貌、氣候、宗教等),為滿足區域性民眾休閑,或以寄托美好情懷、傳承宗教文化等衍生出的一種地域性傳統體育形式。具體的體育項目和活動方式作為民俗文化的演進載體,既是我國傳統文化服務于民眾的重要途徑,其中所蘊藏的文化思想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代代民族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畢旭玲提出,“新民俗”的產生必須緊密結合該民俗閾下民眾的日常生活,表現民眾的生活愿望與訴求,進行生活化的思考,并引入查德.道爾森的“偽民俗”觀點即“去生活化”民俗實則是一類“偽民俗”。從歷史角度看,民俗作為民眾普遍遵循的種種行為活動方式的結晶,無論在過去現在或將來都將客觀存在。過去的民俗傳承至今稱之為傳統民俗,現在的被人們普遍遵循的種種行為活動方式將會演進為未來民俗,傳統民俗在演進為未來民俗的過程中或多或少的會受到歷史時代的影響演進為新民俗。“泛民俗”作為一類新民俗出現之前的民風,與民眾日常之間看似只是泛泛之交,甚至于只存在于部分人之間。泛觀之,滿族珍珠球運動作為少數民族民俗體育項目之一,作為民俗文化傳承與演進的載體,與其他民俗文化具有同根性。是滿族人民在歷史條件的約束下為滿足區域性民眾休閑、宗教文化的傳統體育形式之一,在服務滿族人民至今的條件下,極具民俗潛質。佇立現實,從長遠角度上分析滿族珍珠球運動歷史與現實交匯的“泛民俗”觀,正是民俗體育研究者們所匱乏的。
2 復興端倪:滿族珍珠球運動的民俗魅力
起初,珍珠球運動隨統治階級的意志,在民間有良好的底蘊,廣為流傳;近代來,由于晚清統治衰微導致的民不聊生以及列強入侵所帶來的體育文化沖擊,這項運動被民眾逐漸淡化;21世紀后,大型民族體育賽事的舉辦,滿族珍珠球運動在一次次公開亮相中嶄露頭角,為觀眾博得了視覺盛宴,被民眾認為珍珠球將不再是滿族人民的“專利”,逐漸出現了些許復興端倪[2]。
自2002年內蒙古第五屆自治區民運會首次邁入大眾視野以來,滿族珍珠球運動在民間體育界地位迅速升溫[2]。003年第七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的該項目的參賽地位確立,2008年6月7日被正式刊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熔鑄于我國博采眾長的優秀傳統中華文化的百花園中,如同花海中的一枝薔薇,雖顯嬌弱卻獨綻芬芳。成為推動我國全民健身事業發展的“生力軍”。
滿族珍珠球運動原名采珍珠,溯源可至300多年前清太祖努爾哈赤時代,青年男女在深秋采珍珠進貢統治者時為歡慶豐收之喜而進行的一種體育性游戲,對當時生活在白山黑水以采珠勞作為主滿族人民心中,既是生產技能的鍛煉,也是生存的競爭,所以在滿族人民之間很受歡迎。經過一定歷史時期的磨合,逐漸發展成有具體形式和具體規則的民間體育活動。在現時代下,根據體育傳播學相關規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轉型改變了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傳播背景,“互聯網+”和自媒體等多樣媒介的迭出,更是引發學術界對滿族珍珠球運動推廣途徑上的研究熱潮。可以肯定的是,不論在推廣始末,不論在深度還是寬度上,都是一項極具全民性的發展之路。
3 守正出新:珍珠球運動的民俗薪火
3.1 傳統體育與新民俗的依存關系
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是在社會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歷史產物,而歷史產物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關系,這種歷史關系本身又以長期的以往的歷史為前提”。傳統體育作為歷史民眾生活的一部分,其創作者并不是某天才個體而是民眾智慧的結晶,正所謂“源于民眾生活且無法脫離民眾生活”,這類受歷史民眾生活的積淀所形成的非意識形態產物既具有社會的普適性又具有體育的功能性,雖然得到了國家層面的充分認可,但必然逃離不了舊民俗的規約。
新民俗釋為未來生活中民眾蔚成風氣的生活文化,涵蓋了生活中的各個方面,是對歷史乃至當代民俗文化的沿襲。可以說沒有舊民俗的鋪墊,新民俗也就無法誕生。作為舊民俗的傳承者的我們同時也是新民俗的締造者。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說,傳統體育作為舊民俗文化演進的載體,其發展為新民俗的產生過程必然是歷史性與階段性、統一性與多樣性、前進性與曲折性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3.2 珍珠球運動蘊含的新民俗理念
現代珍珠球運動保存著舊民俗中勞動人民漁獵生活文化的底蘊上,結合手球、籃球等技能主導類同場對抗性項群運動相關規則進行改良,充分地將辛勤的勞動人民的美好訴求與體育應有的健身功能有機地熔鑄于一體,是一項具有現代氣息的傳統運動。學術界眾多科研工作者從多角度對滿族珍珠球運動的健身價值、文化價值及其所產生的社會效應樂此不疲,寄期于更好地傳承與發展。其中就不乏用民俗發展觀來詮釋珍珠球運動復興的可行性研究。
體技結合的表現效果完美的概括了珍珠球運動的項目特征,運動員們在給觀眾帶來一場場視覺盛宴的同時還展示了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群策群力。古今通論,珍珠球運動之所以被民眾所喜好,離不開以這一內在品質為理念的核心精神。現代珍珠球運動不同于其他同場對抗性球類項目,比賽在長28米,寬15米的場地上舉行,參賽運動員分為雙方,毎方7名,其中由水區(內場區)3名、蛤蚌區(封鎖區)2名、威呼區(得分區)1名運動員組成。獲勝需要在保證水區球員運傳配合的基礎上,威呼區球員需要根據己方球員投來的球完美地避開蛤蚌區球員的封鎖路徑,奪球入網得分,上下半場結束后得分多的一方為獲勝方。賽制雖簡單,但在舉手投足之間盡顯技體能結合之美。以運動員場上分配為例,水區球員主要負責進攻的組織、快速的擺脫防守以及適時地投球,這三類技戰術對體能要求較高,身體的對抗性較強,歸為技能主導對抗類;與之相對應,威呼區球員通過身體靈巧的移動避開蛤蚌球員封鎖路線后手持抄網奪球得分,幾乎沒有身體上的對抗,是一個靈活性與技巧性較強的位置,故歸為技能主導準確類;蛤蚌區球員通過雙手持哈蚌(蚌形球拍)或起跳或俯身合理運用封、擋、夾、按等技術攔截對方球員的投球,快準穩是對該位置球員的核心要求,大類上可歸為技能主導類。在一場完整的珍珠球比賽中,民俗風情與體能、技戰術的結合完美地展現出來,具有較高的觀賞價值。
此外,珍珠球運動所代表的辛勤勞動人民團結協作、集思廣益戰勝蛤蚌精獲取珍珠的核心精神,在復興的同時具有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積極功能。各民族團結且共同繁榮是我國民族愛國主義的價值追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要條件。近代著名作家魯迅以筆代戈,演繹了“民族魂”的光輝形象。學界在關注“民族魂”的這一精神形象時,批判的往往是中國近代上對西方文化的“拿來”主義思想與我國落后的“吃人”制度,而忽視了“民族的”舊民俗文化與“愛國的”“大眾”主義先進文化是一生二,二合一的有機整合體。珍珠球運動作為滿民族勞動人民淳樸民俗民風的傳承載體,以民俗文化復興的觀點進行審閱時發現,運動員在場上傳感于觀眾的不僅是場上拼搶的激情熱血,更多的是泛民俗文化背景下大家的心靈共鳴,而這種心靈共鳴正是源于對民族文化的底氣和自信,演繹對新民俗的展望。
4 樂觀因素:助力我國珍珠球運動民俗復興的催化劑
4.1 社會基礎——珍珠球運動的現代化進程
奕口民詩“漸覺春來喜氣浮,豐年里巷遍歌謳。暫從客里停征轡,閑向村邊看打球。一擊橫過飛鳥背,再拋高出短墻頭。兒童奔走渾忘倦,拄杖田翁笑喘牛”。描述了清代孩童在進行珍珠球運動時的歡快場景,字里行間還可以解讀出當時的珍珠球運動以娛樂性為主且不受階層束縛。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列強入侵中華使民眾生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列強在剝削中華財產的同時舶來了眾多“新穎”的西方體育文化,如:籃球、排球、健美操等。當時的國人對本國社會的落后表示無奈時,認為這種隨西方入侵的“舶來品”是高級的,眾多國內學堂聘請的西洋教師也一味地推崇自身的西洋文化。一時間,崇洋媚外成了一股風潮,西洋體育項目占據了我國民眾體育生活的絕大領域,無暇被大眾聚焦的珍珠球運動逐漸銷聲匿跡,僅存民間傳統體育項目只有太極拳、武術等。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諸多民俗傳統體育項目才有了復蘇之風,珍珠球運動亦是如此。改革開放后,經濟實力的崛起,民族的復興,綜合國力的增強,珍珠球承載著獨領風騷的地域性滿族文化,再一次映入了少數人的視野,成為當時的一種泛民俗文化。1983年,在北京市民族委員會各在京專家、學者的通力協作下,對滿族“采珍珠”游戲進行剖析、加工、整理,編寫了相應的游戲規則,并正式改名為“珍珠球”[2]。自此,廣大民眾逐漸走向了珍珠球運動的傳承舞臺,由滿族人民獨有的體育文化逐漸推演為民眾自發組織的全民性健身項目之一,既為快節奏化生活的現代民眾有效“減負”,更使這項運動起了承載中華優秀傳統民俗文化使命,由泛民俗體育運動轉變為當時代新民俗體育文化。
當下民族傳統體育賽事中,珍珠球運動規則參考了西方籃球、手球等運動相關規則制定而成,具有嚴謹的賽制規則、得分手段和犯規判罰,是傳統民俗體育項目與西方舶來體育規則、現代體育精神的完美融合,在新時代下孕育著燁燁生機。因傳統體育項目的本土性,以及其在傳承過程中的活態性、流變性,它在融入現代中國大眾體育項目的悠遠過程中就必然以“涵化”的方式接緣新鮮血液以增強其在全民環境下的生存本領。珍珠球運動以“本土性”而生,又以“涵合”而續,它的傳承演進過程就是一個良好的印證。在珍珠球運動被確立為民運會正式比賽項目之處,就與西方籃球和手球運動結下了濃厚的“情緣”,以二者的運傳球方式和得分判定為原型予以規則的制定,從而透露出“涵化”的屬性。在競技化的發展道路上,它一路博采眾長,向籃球、手球、英式足球、排球、橄欖球、棒球等西洋體育項目“納精”,革新出許多新式技戰術配合與得分手段。與此同時,珍珠球受到籃球、羽毛球、健美操、舞蹈等現代流行體育元素的沖擊也不容小覷。珍珠球運動是“國粹”,有著鮮明的民族特征和獨特的文化價值,而這就要求我們在世界體育文化的交互適應中適當涵化現代化元素,在傳承策略中整合創新中國傳統體育固有形態,在趨同適應中拓展本土體育地域范圍。
4.2 思想淵源——民眾的文化認同與自信
人們一提到“文化熔爐”,就會將不同的“語言”“文字”等不自覺地關聯起來。其實,語言和文字只是重要的文化傳播載體之一,具有非能動性;與之對應的能動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在文化傳緣中也功不可沒。前者作為古代帝王統一國家、民眾相互交流的工具被大眾所認可,后者則因為地域風俗、文化原點的不同還未能推廣普及。然而單一地推崇某個載體都會走入極端。伴隨現代人們思想觀念的升華,越來越多的人理性地認識到語言、文字等非能動性意識載體與體育這類能動性意識載體之間的關系。于是,一種融合的觀點——“文化基因體育強國”被社會各界認可。其中旨在正確處理文化自信與體育強國夢之間的互融共生關系,明確文化自信是核心,體育強國是文化自信的展示類,以文化自信為根基實現體育強國總目標,布局體育文化自信自覺體系。在眾多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中,滿族珍珠球運動以其民族歷史性、生活氣息濃郁、趣味多樣、道具易備成為文化基因體育強國的“佼佼者”。珍珠球運動的主體是中青年人,他們平時生活被工作學業所占用,渴求運動刺激興味索然的生活而無法承受高強度負荷,就只有通過“高趣味低負荷”的方式來代償生活的空缺。與推廣對字面文化的學習和單體運動甚至高強度競技運動相比,這種兼具文化合和、團隊協作、高趣味性以及可控負荷度的珍珠球運動更能實現“文化基因體育強國夢”,值得大力復興。
4.3 心理機制——國人理性的體育剛需
英國著名倫理學家、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了著名的《道德情操論》,其中認為:“責任感”應該是某種導向性和決定性的原則。近代體育中,“強種強國”的意志已經上升為民眾所肩負的歷史責任感。俗語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在民族傳統體育層面如何興,興何如卻已成為一個看似淺顯、實則值得深入探究研習的歷史文化課題。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偉大的教育家,被后世譽為至圣先師的孔老先生在他推崇儒家禮樂文化中,就在“六藝”教育中的“射”和“御”中滲透出體育的光輝,儒家的體育精神以實用性為原則,以滿足生活中的物質需求為主要目的,并沒有明確指向精神文明層面。現代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人們對美好生活需要早已不用通過體育滿足物質上的剛需,榮譽愛國、自強不息、超越自我、規范有序、信任寬容、辯證理性的體育精神內需成為民眾復興傳統體育內心的大勢所趨。其中,滿族珍珠球運動所體現團隊之間的寬容信任、協作配合在人們的潛意識中是位居于首的。
德國教育家、哲學家馬克思和恩格斯于他們的論著中多次強調集體命運與個人發展相結合,達到“集體化個人命運共同體”。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中,滿族珍珠球運動是一種以其個體與集體的分工表現的功能價值而定義的運動形式,以鍛煉人的個體運動和團隊協作能力為己任,以促推民族體育復興實現體育強國為終極目標。珍珠球運動的復興動機完美契合國家和民眾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共贏性綱求,所以自推廣復興之初,便為民心所向。珍珠球運動的“合”可以大致歸納為隊員個性展示與同心制勝而呈現出來的“心合”,民俗風俗與體育強國夢水乳交融相的“意合”,傳統體育與現代競技體育合二為一的“愫合”以及運動者與場下觀眾對場上一次次進攻、防守、得分、反擊所產生情緒上激動、驚嘆、開心、意外等各種“互合”。這諸種類別的“合”與國人對體育的理性剛需相合契。
4.4 復興途徑——以高校教育促復興
珍珠球運動是最具配合、協作的運動典范之一。各學校的受教育群體在重智育的教學環境下,往往都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所缺乏的正是這種團隊間的協作能力。因此,珍珠球運動在復興之初就被推廣入部分高校教育之中,輻射力度也一路高歌。其中首都體育大學開展“珍珠球”運動已有20多年歷史,“珍珠球”早已經成為該校的特色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中央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大連民族學院、天津體育學院、廣西民族大學、集美大學、河北體育學院、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哈爾濱工程大學等越來越多的高校將“珍珠球”列為公共體育課的普修或選修課程,部分高校甚至專門修建了“珍珠球館”。在高校體育教學的助力推動下,珍珠球作為一種體育措施與方法持久活躍在校園中,在習得群體享受其帶來的健身功效同時,也給其帶來了復興之勢,一次次校園珍珠球友誼賽的開展,也使其成了校園民族文化建設的生力軍。高校教育的大力支持為珍珠球運動的傳承和復興提供了優良的平臺。
高等教育的推廣可以加快珍珠球運動的新民俗復興進程。珍珠球運動的本質是一種“舊民俗”活動,在歷經高等教育的剖析衍義后,習得群體不僅可以準確掌握和靈活運用珍珠球運動的技戰術特點、得分技巧,更可以挖掘內在的“文化精髓”。由于高校生源的廣泛性,從而產生了重要的復興模式——“業緣復興”;青年人群因生活單調壓抑、身體亞健康狀態而需求尋找一種既能互動健身又能豐富生活的有效途徑,地方體育部門也需要培養該運動的傳承人,這一“自我需求”與“地域需求”促使社會各級體育機構在所屬地域范圍內推廣珍珠球運動的同時培養選拔珍珠球運動員,與此同時,各地對外開放的室內外珍珠球場館也為珍珠球的復興提供了有利的切磋平臺和復興媒介。地方珍珠球隊與民眾珍珠球愛好群體二者遙相呼應,共同促進珍珠球運動實現了良好的“地緣復興”;經過不同體育機構組織狀況區分了的復興方式,滿族珍珠球運動呈現出外族同質性,群化在全民健身中,內化為“泛民俗”觀下部分群體內心深幽蔚然成風的思想內蘊,通過思維加工又外化轉型為“泛民俗事象”;純粹的珍珠球“泛民俗事象”歷經時代演進,漸漸融合為代表中華優秀舊民俗文化的現代精神文明新民俗,同中華傳統武術與時代相結合而復興,從而衍升為一種新民俗文化。
5 緊張因素:滯礙我國珍珠球運動民俗復興的絆腳石
5.1 大眾對民俗延繼理解偏狹
在現代快節奏的社會生活中,占總人口基數91.5%的漢族民眾心目中普遍認為當下民俗事象集中存在于少數民族聚居地、旅游景點、人跡罕至的鄉土地域,諸多民俗民風被一些特定的節日、祀禮等所承載,而自身與這些民俗的關系僅僅是賞析與被賞析的關系。除此之外,學界在“民俗”與“傳統體育”兩個方向上的理論研究多以民俗溯源和傳統體育的過去為獵奇點,也鮮有研究者對當下社會的民俗事象進行浮光掠影式的總結。不論是基層民眾還是界內學者,皆認為自己是民俗的“觀望者”和“定論者”,而疏忽了自身在民俗社會中所承擔的“保護者”和“復興者”的潛在身份。譬如滿族珍珠球這樣曾經盛行的民俗文化事象,有著轉型為新興民俗的內在基因,或許在將來會成為民俗文化的中堅力量,無論在民俗界還是體育界理應成為國人的聚睛處。民俗主體對民俗延繼理解度是否寬泛繼而關系到整體民俗文化的興敗存亡。
5.2 全民健身體育項目的“輕”化轉型
全民健身與全民健康并稱為我國兩大國家戰略,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已經愈發深入人心,其意義是為滿足新時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保障,其戰略的構建體現以人民為中心,旨在從健康維度滿足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輕體育”是大眾體育領域下繼發而出的新概念,由歐美體育界最早提出,以靈活性、輕松性、普遍適用性為其主要特點,以消遣娛樂、貼近生活、通俗易接受為價值取向。由于全民健身涉獵對象的廣泛性無法與競技體育更高、更快、更強的思想特征相匹配,體育項目“輕”化轉型似乎成了推廣全民健身的主旋律。進一步來說,所謂“輕”化首先應理解為“輕松化”,以促使全民參與、增進全民健康為主色調,然后才能進一步分岔衍義到對各體育項目運動強度、動作構成、對抗程度等“輕”化的直觀性解釋。全民健身沒有具體的運動項目的指定,徒步、慢跑、跳交誼舞等都處于范疇之內,與傳統“運動方式”的認識相比,它更像是人們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利用碎片化的時間維系健康、舒緩身心壓力的一種新型生活理念。體育項目的“輕”化轉型特別適合當今工作的上班族、學業繁重的學生以及老年人群。因此,相對于傳統體育項目,廣大民眾更加樂意于選擇休閑健美操、有氧自行車、慢跑等舒緩、少汗、“輕”化轉型后的運動方式。與這些轉型后的體育項目相比,珍珠球運動的卓絕性逐漸失卻,其對抗性更強,運動強度更大,體能消耗更高,技術要求更細,因而在推廣“復興”道路上失去了部分民心,他們更喜歡在“輕”化轉型后的體育項目中獲得最大化的舒緩身心。
6 積極轉型:滿族珍珠球運動的民俗復興良方
當下社會環境中,滿族珍珠球運動良好的復興態勢得益于社會各界因素的共同助力,其中,不同民族間民俗文化的相互融合與認同,民眾的積極參與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珍珠球運動賽制規則的編制和完善,民族傳統體育正式項目的確立,各地區珍珠球館的興起,預示著它已具備了與大眾體育、全民健身和合共生的社會土壤,也演繹出復興為新民俗的社會跡象。但是,任何事象的發展過程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泛民俗”形勢下,珍珠球運動復興成社會新民俗事象的行進步伐因一些不符合全民健身體育價值訴求的因素而受阻,只有在保持其本源屬性的基礎上適時轉型,才可消除壁壘融入全民體育生活,進而上升為一種“新民俗”。具體而言,珍珠球運動在秉持健身、文化、競技、觀賞等多元價值基礎上向著民眾雅俗共賞的“輕體育”方向進行簡化規則、降低得分難度、減輕運動強度等多層面適時“轉型”,滿足全民健身背景下我國大眾對珍珠球運動的實際需求,進而推動其“新民俗”進程,使之在傳統體育推廣與民俗文化復興、群眾體育普及與體育強國建設中獲得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