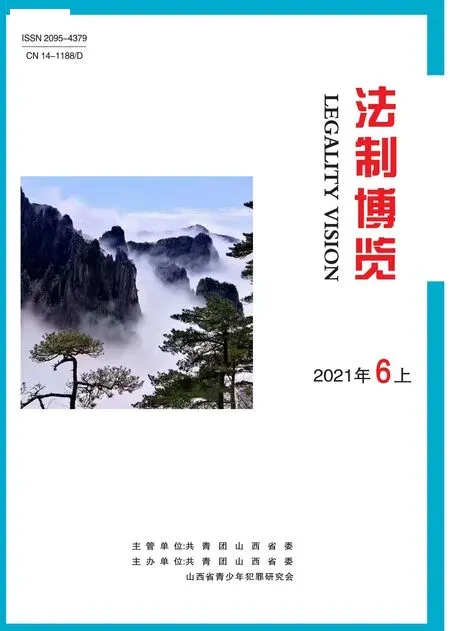設立家族信托監察人的必要性
王佳彬
(沈陽師范大學,遼寧 沈陽 110034)
一、家族信托監察人制度概述
家族信托即以家族財產的所有人委托而確認的,以家族成員為受益人的,以家族財富為基礎設立的意定信托。通過信托合同約定和法律規定的安排,使信托財產由信托公司持有和管理,并將其受益和信托財產本身分配給受益人。無信任則無信托,信任關系是信托設立的基本條件。委托人基于信任將信托財產交由信托機構占有并管理具有一定風險。如何降低信托的風險并維系委托人對受托人的信任關系是家族信托乃至整個信托制度發展的根本。監管的重點是信托財產的獨立性,建立家族信托監察人制度對信托機構進行有效的管控[1]。
二、當前信托監察人的制度現狀
(一)信托監察人制度的國外現狀
信托監察人制度主要在部分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存在,但各個國家關于信托監察人制度的具體規定不盡相同。日本《信托法》中關于“信托管理人”的規定以及英美法系國家所使用的“信托保護人(Protector)”其本質上與信托監察人制度相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八十七條第一款規定:“信托的管理應當受到委托人的監督,如委托人已死亡,應受其繼承人、受益人甚至將來受益人的監督。”同時,中國香港特區2013年出臺的《信托法律》對1934年就已經生效的《受托人條例》和《財產恒繼及收益累計條例》的規定進行了全面的改革,主要包括:賦予受托人更大的法定權利,對受托人的權力進行適當的制衡和引入反強制繼承權規則[2]。
(二)信托監察人制度的國內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下稱《信托法》)僅對公益信托監察人制度中信托監察人的產生、可訴性和認可進行了規定即確立了公益信托監察人制度。具體在《信托法》第六十四條規定:“公益信托應當設置信托監察人。信托監察人由信托文件加以規定。信托文件未規定的,由公益事業管理機構指定。”第六十五條規定:“信托監察人有權以自己的名義,為維護受益人的利益,提起訴訟或者實施其他法律行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中政府相關部門僅僅在必要時才進行必要的審計監督,這是一種缺乏力度的被動監管模式[3]。在信托監察人的選任或設立、職責的行使、責任的負擔、權利的必要限制和監察人權出現沖突時如何解決等方面均有所缺失。
目前中國大陸區域內具有針對性、安全性和保密性的家族信托數量很少。在實務中家族信托存在譬如信托稅務負擔、信托財產的實際登記問題甚至包括信托本身登記存在的問題,而信托監察人制度的缺失使得這些矛盾深化。《信托法》對于除公益信托之外的其他信托監察人方面未進行確認或限制,這成為家族信托業務在中國大陸地區難以順利開展業務的主要原因。
三、構建家族信托監察人制度的必要性
(一)家族信托受益人的非特定性需要信托監察人
我國《信托法》有且僅有對公益信托監察人的規定,從立法原意上來說這主要是由于立法者認為公益信托在設立和運作時,不像私益信托那樣對受益權和受益人明確。基于公益信托中受益人的非確定性,我國更加傾向對受益人不明確的公益信托設置信托監察人,以此對受托人在選定受益人及確定其權益的過程中進行協助和監督。
家族信托同樣面臨上述相似的問題,家族信托的受益人范圍和權益大小,會依據信托文件的內容進行判定,但在家族信托的長期存續期間內總會呈現向不確定性發展的趨勢[4]。例如,新生的對象在設立后和運行中其家族成員總是存在必然的不確定性[5]。家族信托監察人制度的設立可以有效對受托人進行約束,保證受益人身份的確認及其受益權的實現。其實在公益信托中還存在廣泛的社會監督,但家族信托具有濃厚的私益色彩導致信托受益人保護處于相對劣勢的狀態。雖然家族信托具有私益信托的性質,但不可否認家族資產是社會財產的組成部分應當予以保障。
(二)家族信托事務管理的復雜性需要信托監察人
銀保監會在2018年發布的《信托部關于加強管產管理業務過渡期內信托監管工作的通知》中強調信托在財產規劃、風險隔離、資產配置、子女教育、家族治理、公益(慈善)事業等事務中的管理功能[6]。家族信托的財產往往種類繁多,數額巨大,同時利益分配復雜,長期存續的家族信托需要具有更多的機能以容納結構日趨復雜的信托利益。家族信托當事人的主體設置上可以達到監督信托實施的功能,如委托人可以對信托事務進行變更、而受托人出于自己的利益也會對信托事務進行監督。當信托事務管理中委托人或受益人的民事行為能力單獨或同時呈現瑕疵狀態時,會使受托人權利缺乏制衡而導致違背信托目的而侵害受益人權益的行為。
當委托人的行為能力出現瑕疵而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呈現出多元未知的情況下,家族信托將由三方監督變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雙方監督。作為受托人的信托機構在現實中掌握更多的專業經驗所以其處于相對的優勢地位。當進一步出現信托受益人為無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極端情況時,這種結構性的失衡很大程度上可能導致信托合同不能實現[7]。針對上述情況,構建家族信托監察人制度讓獨立、公正的第三方介入,讓其承擔監督信托運行具有其必要性。
(三)家族信托受益人權益保護完善需要信托監察人
家族信托最主要目的是財產傳承,這對信托財產的安全保障和信托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厘清提出了要求,與此同時更要注重信托財產效益的實現和最大化。信托財產在管理運用的增值過程中導致信托事務的復雜性和專業性。此時當信托當事人出現紛爭并訴諸法院時,法院在認定相關的信托人的違法或違約行為時存在專業性上的短板[8]。司法資源稀缺以及爭議性質的多樣性和專業性決定了司法機關對信托的監督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家族信托的長期性決定了必然會出現信托委托人缺失的狀態,而我國《信托法》第二十二條對受托人違規或違約不當處理信托財產的情形下,僅委托人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該處分行為并有權主張賠償損失。同時第二十三條還規定了上述情況發生時委托人可以依照信托文件的規定或者向法院申請解任受托人。法律規定的委托人對受托人進行監督并自行救濟的規定與委托人有限額的存續期間導致在家族信托場景下出現法律空白。在公益信托方面,我國《信托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委托人、受托人或者受益人三方在公益事業管理機構違反信托法規定時都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9]。這體現了我國信托法對公益信托監督的重視,但對于家族信托的監督缺位以及對設立信托監察人的缺失將不利于中國家族信托的發展。
四、結語
信托制度經過英美國家幾個世紀的發展,在中國大陸發展的時間也有幾十載。在家族信托中對受托人行為的有效管控和受托人利益的切實保護過程中存在多元化的監督機制,但信托監察人的職能不容忽視。設立家族信托監察人制度,可以促進家族信托業務的穩定運行,保證家族信托核心財產的傳承和長遠利益的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