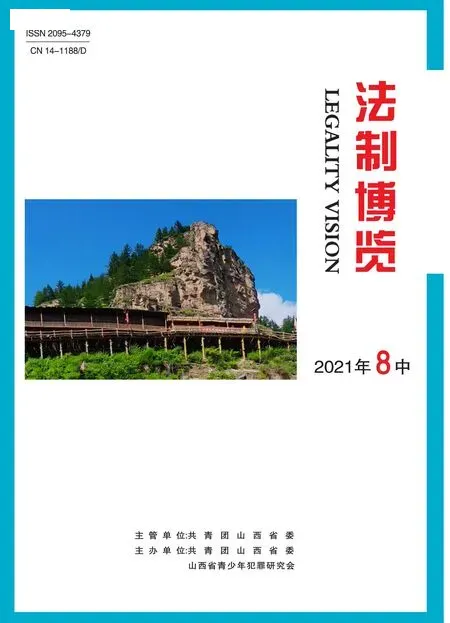從《刑案匯覽》探究清代存留養親制度
趙金磊
(黑龍江大學法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一、清代存留養親制度形成的歷史淵源
中國古代存留養親制度自北魏出現,歷經數朝數代,至清代發展完善。《魏書·?刑法志》載,北魏孝文帝將存留養制度著以令格,死刑犯如若全部滿足祖父母和父母年老、無其他成年子孫、無可期之親三個條件,核實后奏報孝文帝準予,該犯可免死留養侍親盡孝,自此便出現古代存留養親制度的雛形。唐代在《北魏律》的基礎上據以國情略作調整,諸如適當放寬案犯申請犯罪存留養親制度的條件,直系親屬祖父母、父母“篤疾”難以維系生活亦成為理由,但相對而言,只有非十惡的死罪方可適用,竊盜等極度危及社會秩序的犯罪亦不可,即便符合條件的死刑犯亦難逃相應杖刑懲罰等。宋朝完全承襲《唐律》中關于存留養親制度的法律規定。金代金世宗創制出官與養濟制度與存留養親制度并行,意欲通過以國家政權為表率,分擔社會老而無養的壓力,打破困頓局面,實為仁善之政。元代的存留養親制度更顯寬松,不僅將適用死罪的罪名限制取消,還將年齡放寬至七十歲以上,對竊盜犯更為寬容,元代承受刺斷黥墨的竊盜犯可以適用存留養制度,對其再犯亦稍顯寬容。明朝伴隨著封建專制中央集權制度的極端發展,“禮法并用”的治國方略得以維系,更是通過《大明律·?名例律》規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以次成丁者。開具所犯罪名奏聞,取自上裁。若犯徒流非常赦所不原,止杖一百,余罪收贖,存留養親”。[1]雖然存留養親制度以專條方式規定在《大明律》中,但其適用條件極為嚴苛,難以正常施行。清代存留養親制度在沿襲明代的基礎上,大量進行補充、完善,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較之前代更為廣泛,并且增加了孀婦獨子以及留養承嗣等新的適用條件。
二、對《刑案匯覽》中清代存留養親制度案例的分類辨析
《刑案匯覽》中記載93篇從乾隆年間到光緒年間關于犯罪存留養親制度的判例,其中詳細記載了存留養親制度的適用情況,接下來從是否準予留養、留養承祀等角度探析清代存留養親制度。
(一)準予留養的案例
乾隆五十四年關于山東省軍犯王大友案的說帖[2]中記載,雖然王大友的母親已經年滿七十歲,但其父親王燦才62歲,不滿七十。山東省督撫援引乾隆四十二年湖廣省絞犯王述盛案和乾隆五十二年山東省免死減流犯張起子案兩案說理,以上兩宗案例中“犯父均年未及七十,尚可謀生,而其母或老或疾”。因此,清代存留養親制度的適用不需要同時滿足老疾,父母有一方已“老”至七十,即可符合,應當將案犯準予留養。
(二)不予留養的案例
道光八年說帖:“死者雖有兄弟出繼不能歸宗北撫咨:李允寬系毆傷葉應憚身死之犯,例準留養,惟死者之親尚在,雖有兄弟出繼,不能歸宗,即與獨子無異。應比照兇犯有兄弟出繼,不能歸宗,以獨子論之例,將李允寬不準留養。”[3]清代存留養親制度中被害死者如果同是獨子,案犯之親自然不能由于死者之親獨享子嗣侍奉,而關于獨子的認定清代亦通過案例來釋明,出繼子不能歸宗等同于被害死者的獨子身份,揆之情理,以顯公平。還有諸如犯強盜或者多次盜竊等嚴重危及社會秩序的常赦所不原之罪,亦不予留養。
(三)查明再行取結核辦的案例
道光十三年有直隸鄒培林等共毆安亮身死一案,正犯在逃未獲,案情仍有待商榷,倘若僅據一人之言就此斷案留養,難免有失公允,唯有監候待質,待正犯歸案,查詢明確再行辦理。清代對于適用存留養親制度仍較為慎重,唯有核實情節后再行決定是否適用存留養親制度,以便追求更為公允的結果。
(四)留養承嗣的案例
清代存留養親制度在協調家庭、宗族、國家的關系中產生了留養承嗣制度,注重法律對家族的影響。嘉慶十八年減等流犯鄭發毆妻致死準其承祀一案,鄭發砍傷致其妻子丁氏死亡,擬判處絞刑,秋審時查其情節較為輕微,總共經歷三次緩決,上奏皇帝準許減等為流刑,又因其母已故,其子尚未成丁準其留養承嗣。雖然對于秋審時入緩刑名冊的減等犯沒有相關規定,但依據服制,夫毆妻死情節較輕,三次緩決未定留一線生機,刑部回復仍然發配未免過于拘泥于法律條文,應該準其承嗣。可以了解到,清代案例已經被提及至與《清律》條例同等高度,二者都可以作為判案參考依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此時,在具體適用條件下,援引成案判例更為推崇,甚至可以稱之為以例改律。另一方面服制對于清代律文影響頗深,妻為夫服斬衰,夫為其服齊衰,尊卑有序,以尊犯卑,關系越近,處罰越輕,這也正是鄭發被認為情輕能得以繼而留養承嗣的原因之一。
三、清代存留養親制度適用中存在的問題
(一)地方關于存留養親的捏結
《刑案匯覽》中還有諸多關于清代存留養親制度的案例,可以了解到其在清代適用范圍的放寬,伴隨司法實踐中的諸多適用,其弊端亦隨之而來。曾有道光四年江西省絞犯劉德興案,直至當年秋審后尾,尸弟馮忠街上呈控告,劉德興非家中獨子,實不符孀婦獨子之特殊規定,復將劉德興改歸秋審緩決,后亦將扶同捏結之人審擬治罪。但捏結謊報之案并非始自道光年間,乾隆年間、嘉慶年間就已經出現捏結謊報之案,諸如乾隆五十四年河南絞犯聶添一等案,只不過道光年間更甚,鑒于清代存留養親適用制度的程序以及府衙內腐敗積弊已久,縱然清代存留養親制度的審判核查程序規定嚴密、繁瑣,亦不可避免此類情況的出現。為此清代統治者發現此種現象并非個例,隨即采取相應措施用以解決問題,但從案例中可知,雖然嘉慶、道光試圖從法律上對案涉相關人員進行規制,但仍收效甚微。
(二)取結、供節和提訊存在難題
清代存留養親制度的程序流轉本就繁瑣,層層上報核實,為減少上述捏結謊報之弊,清代統治者加大過程中對案情的復核,諸如道光八年廣西頻出捏報留養之案,乃至于廣西全省暫行按下,上下聯動、一一核覆本省其余留養案件,響應道光帝“各督擾,督同泉司,于秋審時遇有呈請留養者,務當親提犯屬尸親鄒族人等,逄加嚴訊”的詔令,案件流轉過程中極大增加相關司法官員的工作壓力,同時亦對案涉供結、取供的人員是一份負擔,長途奔赴難免悖于恤民之心。為了矜恤存留養親案件的無辜之人,直隸督撫于道光九年建議以民為本,為百姓提供便利適用就近原則,甚至符合條件亦可派人上門取供,不僅提高了州府縣臺的工作效率,以能彰顯清代統治之仁義,與清代存留養親制度的內核甚相符合。
四、清代存留養親制度的價值評析
(一)清代存留養親制度的正面價值
清代存留養親制度矜恤親老,彰顯“盡人之情”。清代作為封建王朝的巔峰,亦深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清代存留養親制度是國法、天理、人情交織融合的結晶,它滿足廣大百姓“老有所養”的心理以及生活需求,揆之法、理、情,詮釋了法的“隨人情、通人性、合人道、應人心,而不應逆人情、悖人性、反人道、違人心。”這體現了清代存留養親制度的價值追求,亦在國法、天理、人情的和諧統一中,提高家庭、宗族在法律中的地位,反之亦加強百姓對法律的認同感、歸屬感,切實增強法的可實行性。
(二)清代存留養親制度的負面價值
存留養親制度違背了樸素的公平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助長犯罪囂張氣焰,也容易引發更為激烈的社會矛盾沖突。存留養親制度最終仍在一定程度上受皇權專制的影響,受制于封建社會階級屬性,統治者具有最終決定權,而最終結果的不確定并不能因為程序法律的完善而得以足夠穩定,以至于清代統治者自身的素質的高低都足以影響存留養親制度的正常運作。此外,從刑罰的目的角度來看,鑒于清代存留養親制度對案犯正常結果的干涉,并未強化刑罰的一般預防目的,而且清代存留養親制度的“法外施仁”,讓案犯得以避重就輕,亦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刑罰的威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