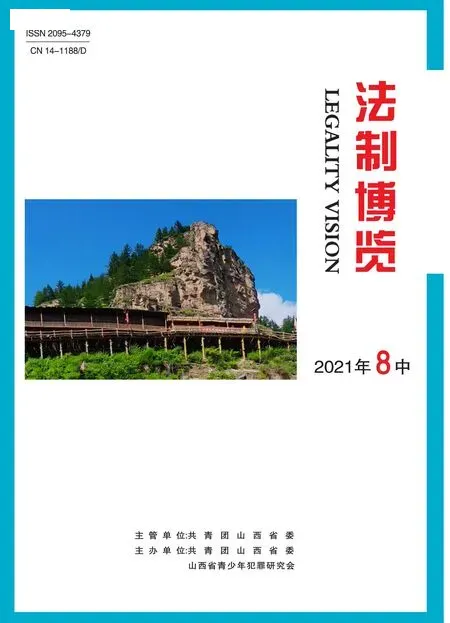《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之合同僵局下的解除權行使
王 茜 李 意
(1.重慶市酉陽縣人民檢察院,重慶 409800;2.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重慶 409000)
一、“合同僵局”與履行不能、法定解除權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第二款賦予了違約方申請解除合同的權利,而該條文的產生背景在于司法實踐中存在大量合同僵局問題,如不賦予一方解除權,合同無法繼續履行且對合同雙方均不利,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又缺乏請求權基礎。合同僵局不是嚴格的法律術語,而是來自《公司法》中“公司僵局”的比較,合同僵局現象在民事和商事活動中并不單獨存在。對此,王立明教授認為,合同僵局主要是指在某些長期合同(如十年房屋租賃合同)中,由于經濟形勢的變化,一方無法履行長期合同,并降低了使用性能,導致合同需要提前終止,而另一方拒絕終止合同。根據上述定義,大多數合同僵局是由合同的無法履行引起的,不管是法律上抑或是事實上不可能實際履行。不能忽略的是,在該種場合下,債務人雖已構成違約,但是,債權人不會盲目地為自己的利益行使撤銷權,因為這不可避免地背離了公平交易和禁止濫用權利的原則,導致合同的繼續存在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嚴格遵守合同的原則貫穿于整個合同中,并且合同應得到充分執行,這是毋庸置疑的法律常識。但是,合同僵局既致合同雙方利益失衡,又致效率低下、資源浪費,故破解合同僵局是必需。[1]
(一)法定解除權的潛在沖突與“合同僵局”
合同終止的先決條件是有效合同的存在。撤銷是解除合同的方法之一,根據撤銷的不同原因和情況,《民法典》規定了三種行使撤銷權的方式:法定撤銷權,約定的撤銷權或同意撤銷。就法定撤銷權而言,《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條的第一款繼承了原《合同法》第九十四條中關于法定撤銷權的理由的列舉規定,這可以從前四項實質性規則中看出。但是,每個違反合同義務的狀態都可能導致合同目的的失敗,這將成為法定終止合同的最多的原因。根據《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條的規定,終止合同將不會更改原義務。
由于終止合同的權利是民法中的一項形成權,因此提起訴訟或仲裁僅是法院確認當事方有權行使終止合同的權利,當事人終止合同的權利是合同終止的先決條件。《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條沒有明確區分違約方和守約方對“當事人”的使用。一些學者認為,第一款中規定的不可抗力情況可以包括違約方和守約方,第五項作為兜底規定應視具體情形而定。但是,司法實務中當合同已經不可能履行,而僅有守約方享有法定解除權,若守約方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拒絕行使解除權,即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構成權利的濫用,此時對于整個合同而言顯失公平,《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第二款支持違約方亦可解除合同,正是對上述合同顯失公正之困境的正視。
(二)基于違約方解除權的解除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規定了一方當事人違約時可以拒絕守約方履行請求的情形,在司法實踐中,法官為解決合同僵局問題直接依據該條規定或精神作出裁判。然而,該條規定在適用范圍上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從字面表述的含義上看,適用前提僅是非貨幣債務,同時,不能將對方的履行請求的辯護直接從“不履行”推論為“可以終止”。據認為,從利益計量的角度來看,當違約方繼續履行合同時,超出合同方所需要的財務和物質資源,如果從履行合同中獲得利益,則應允許違約方終止合同并賠償損失,而不是繼續履行。在最高法判例“新宇案”中,違約方新宇公司無法為馮玉梅的建筑面積超過60000平方米的商店提供服務,合同的終止符合經濟合理性和交易效率。理論與實務界對“新宇案”判決的原因和結果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其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判決形式明確申明,在排除履行權的特殊情況下,違約方可以要求終止合同。在2019年11月發布全國法院民事和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之后,法院可以裁定在更嚴格的條件下終止合同。也就是說,違約方終止合同的權利不是單方面終止。這里強調,對違約方申請終止合同的權利有嚴格的法律要求,顯然不公平。實際上,違反合同會對不同級別的合同目的產生不同的影響,當一方違反合同時,可能會導致無法履行,并且由于無法達到合同目的而導致違約。其中,履行不能不僅包括法律上與事實上的不能,還包括人身關系與經濟因素的不能。同時,違約方申請合同解除權與英美法系中的“效率違約”理論存在根本性差別,效率違約是一方基于追求更大利益考慮的故意違約,僅以效率價值為依歸。而在違約方申請合同解除的場合中,更多的是違約方被動止損的“無奈之舉”,倘若守約方一味死守已經“死亡”的合同拒絕解除,繼續維持合同效力,無疑會造成社會財富的無端浪費。
二、《民法典》應對“合同僵局”之解析
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反對者質疑違約方解除權在道德上的正當性,有違合同嚴守原則,最終因爭議過大,三審稿將刪去的第五百六十三條第三款放在了違約責任章節第五百八十條第二款,并將“解除”這一敏感詞匯代之以“終止”。
其一,第五百八十條第二款規定包括,由于主要原因終止連續性合同,違約方的解散和司法解散。打破合同僵局的規則應支持違約方要求終止合同,這與行使撤銷權的領域類似。如果沒有這樣的要求,司法就很難介入爭端,因為,違約方享有終止權,和審判法院或仲裁庭作出的終止(或終止合同權利和義務)的判決與結果是一致的。其二,合同解除制度同樣是終止合同權利義務關系的手段之一,作為合同嚴守的例外,最終服務于合同目的。若認為合同解除權只能由守約方享有,在雙方權利嚴重失衡情況下,不利于當事人從中解放出來。當然,為避免合同雙方利益均衡關系因合同解除而遭受破壞,法律對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應作出明確規定。其三,守約方的法定解除權的行使與合同一方當事人申請解除合同看似效果上一致,但存在明顯的區分,后者僅是一項程序性權利,即有權向法院提出終止合同權利義務關系的請求,因尚未進入實體審理,客觀上合同雙方均可以行使,而不局限于違約方,至于能否實現解除合同的目的,應由法院或仲裁機構依據具體情況進行審查判斷。[2]
三、《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第二款規定未盡問題
從法律漏洞填補路徑出發,該條文的主要立法目的是彌補《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條的適用范圍缺陷。在合同領域,合同解除權的行使是對違約行為的一種補救措施,基于誠實信用原則,有效保護守約方,并防止違約方從解約中獲利。在《民法典》中,合同解除使當事人從合同僵局中脫身,提高交易效率,也有效地維護了誠信原則,其客觀功能逐漸受到重視。但從法律解釋路徑探求解決合同僵局的法律規范基礎,《民法典》提供的應對規則仍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
其一,它不能適用于付款義務。換句話說,《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規定,第一款的排除,即以非貨幣債務為基礎,規定了付款的規則。違約方申請解除合同,適用范圍將不完整。在民法傳統中,金錢的債務屬于實物債務,不存在無法履行的問題。例如在租賃合同中若出現明顯不公平、違背誠信、權利濫用等限制性條件時,就不能以租金不能給付為由而申請解除合同。其二,在違約方申請解除合同時,為防止惡意違約及虛假訴訟,有必要對違約方的主觀心態進行考量。那么,對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采用客觀標準,即以一個一般的、理性的、善意的第三人視角去審查行為人的違約行為是否具有正當合理性。但實踐中多為模糊認知的合同目的不能實現,往往成為合同僵局破解的主觀基礎障礙。其三,在合同法體系建構中,不論是“終止”的措辭還是賦予“解除”的含義,《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第二款規定置于違約責任章節,難免出現性質界定不明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