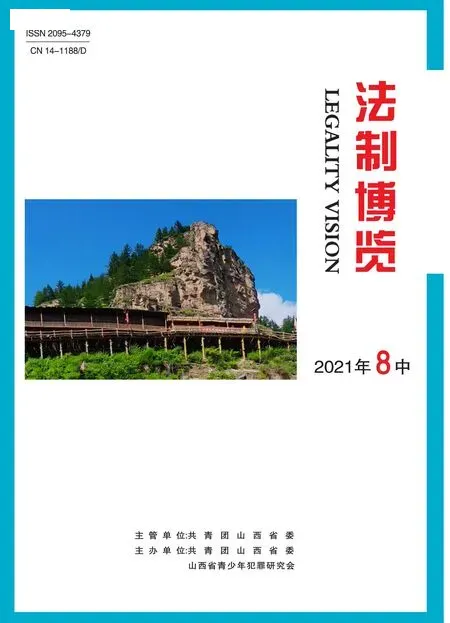互聯網小貸公司法律現狀以及監管問題研究
曹 瑜
(青島科技大學,山東 青島 266061)
最近十幾年里,小額貸款公司依托著普惠金融的大背景在全國迅猛發展,百姓貸款不再是一件難事兒。至此,網絡小貸公司的發展日益繁榮。通過網絡大數據征信、風險管控技術,互聯網小貸公司借助強大的互聯網技術,再利用網絡運營平臺等多方面互聯網技術的服務,互聯網小貸公司相較于傳統的小貸公司,具有安全性更高、效力更快、突破地域限制等多方面的優勢,為我國互聯網金融行業創造出非常可觀的利潤,也拓寬了互聯網金融經濟行業的經營模式。
2015年10月,《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銀發(2015)221號)由中國人民銀行聯合其他10個部門發布。[1]此后,全國各省各地紛紛出臺了關于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文件,例如,重慶、上海、江西等地,其中阿里小貸公司作為互聯網小貸公司的代表進入了公眾的視野。但是在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之下,存在著監管混亂、法律規范的缺失以及政策風險等問題。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本著“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的規則,任意拓展業務,甚至公司資質等方面的問題頻發,造成了互聯網小貸行業的無序與風險。
在這樣的發展與監管需求并進的環境之下,本文通過分析關于互聯網小貸公司的法律現狀以及監管現狀,探尋網絡小貸公司法律規制中留存的漏洞,并提供一些管理問題的方法和出路。
一、互聯網小貸公司法律性質的界定
(一)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的概述
“電商網絡小貸”是網絡小貸公司的前身,目前我國對其尚沒有一個準確的法律界定,只是在一些地方的規范性文件中,為了適應本地區發展的需要以及監管的便利對其做了規定。本文在總結各地方對網絡小貸公司的定義后認為,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即依法取得小額貸款業務執照,并主要通過互聯網的渠道提供小額貸款業務的非存款類互聯網金融公司。
(二)互聯網小貸公司與傳統小貸公司的區別
傳統的小貸公司與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相比有很多的區別,體現在地域限制的差異以及借貸業務的成本等方面,但是二者之間最關鍵的區別是監管機構的不同。傳統的小貸公司的規制主體級別較低、靈活較大,且各地政府對傳統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模式大體相同,各省級政府可以授權該小貸公司所在地的市(縣)級金融辦或相關機構進行具體監管;而網絡小貸公司的法律規制主體級別更高,由銀監會以及各省級政府進行監管。
另外在注冊資金以及發起人的資格要求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總體要求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要比傳統的小額貸款公司嚴格很多。例如,江西省要求互聯網小貸公司注冊資本不低于5億元,且必須一次性繳納,而對傳統小貸公司的要求僅為不低于5000萬元人民幣;上海市要求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的發起人應為穩健經營指標在國內排名靠前的互聯網企業或有互聯網平臺資源支撐的全國性大中型企業。[2]
二、我國網絡小貸公司的立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的立法現狀
網絡小貸公司作為我國企業法人的一種,公司的設立、運營以及注銷等問題首先要遵守的必然是《公司法》與《破產法》,在日常的業務活動中,涉及合同、借貸等問題應遵循《民法典》的相關規定。但由于網絡借貸業務與形式的特殊性,僅僅遵循以上法律是遠遠不夠的;2008年5月,我國關于小額借貸的第一個正式性法律依據由中國銀監會與中國人民銀行頒布(《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銀監發〔2008〕23號))。該文件主要對小額貸款公司的準入行為、發起人要求、經營行為等方面的內容進行了進一步規定并且賦予了小貸公司的合法經營地位。但該文件法律效力較低,文本結構上仍有缺乏法律嚴謹的地方。2015年7月,由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財政部、工商總局、法制辦、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10個部門聯合發布的《互聯網金融指導意見》在某些篇章節中提到了互聯網小貸公司,規定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主體為銀監會[3]。該文件作為政府的部門規章,規定的內容較為原則性,沒有落實到具體的實施措施。同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又在《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征求意見稿)》中提到互聯網小貸公司的監管主體除銀監會之外還應包括各省級政府。一直到2019年9月,銀保監會與央行陸續發出多次相關文件對互聯網金融行業進行規制,其中關于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相較于之前的文件更為詳盡,但其在法律位階上作為部門規章,效力仍未提升。
(二)我國網絡小貸公司法律規制中存在的問題
1.針對網絡小貸公司的基本立法規范缺失
第一,從政策層面上來看,政策的不穩定性是造成互聯網小額貸款行業亂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法律的滯后,一部分互聯網小貸公司在自認為存在法律漏洞的法律背景下開展了并不合規合法的業務模式;另一部分小貸公司則對政策的不穩定因素畏首畏尾,紛紛夭折。政策與法律的結合不應該讓膽大、冒險的企業有機可乘。
第二,從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及內容方面來看,我國關于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監管方面的法律文件只是作為互聯網金融監管大背景下的一小部分,穿插于各個大背景文件中,并且法律效力較低、內部存在較多的矛盾與沖突。
2.網絡小貸公司法律定位模糊
我國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的法律性質,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官方的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定義,僅僅是一些部門規章或者地方性文件根據本地方的需要有針對性地界定其性質,這其中存在著很多的矛盾與沖突。例如,在《小貸公司指導意見》中互聯網小貸公司被界定為企業法人,并不認為其是金融機構;而在央行印發的《金融機構編碼規范》又將其作為金融機構來監管。[4]但是,銀監會與央行這樣的規定是因為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的主營業務為借貸,業務涉及金融,方便監管,故此規定。
由于網絡小貸公司身份的不明確,其有時被界定是一般企業法人,有時又被當作是非銀行類的金融機構,在公司的設立與發展等各個方面又是要受到雙重的限制與監管。這種不明確的法律定位也會造成監管漏洞,在雙重監管都認為超出自己范圍的情況下,違法亂紀的問題就會滋生。因此,法律的空白雖然有利于其業務模式的開拓創新,但多變的政策風險、內部治理風險以及無序競爭的風險等因素,對其發展都是巨大的阻礙。
3.法律監管機構權責不清
雖然與傳統小貸公司相比網絡小貸公司的監管主體由地方集中到中央,監管級別更高且采取中央與地方相結合的方式,[5]但由于缺乏明確的分工,就會存在監管漏洞與行政資源的浪費,因此究竟該如何為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確定監管主體仍需要進一步明確。
通過本文的論述,對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法律性質仍不明確的認識以及對目前法律監管立法現狀的梳理,分析出目前我國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在監管方面主要存在法律定位模糊、基本立法規范缺失以及監管主體權責不明的問題。針對上述問題,結合我國互聯網金融日益繁榮的大趨勢,如何有效監管又不打擊互聯網小貸公司發展的積極性,是我國法律與政府政策需要不懈努力的方向。望本文為互聯網小貸公司的法律監管秩序的發展能提供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