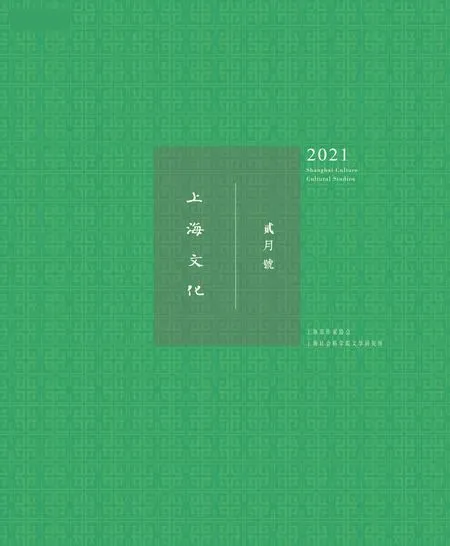踵事增華:滬上梨園竹枝詞與風土詩歌的都市化轉型
李 碧
竹枝詞自盛唐文人聽歌記聞或采歌入詩至今已有千年歷史,與地域文化的傳播有著不解之緣。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竹枝詞已經跳脫了“棹歌”“舫歌”“漁唱”等鄉土地域的定位,陌生化為描摹山川風物、百業民情、風流韻事等多方面社會內容的“竹枝體”,常被冠以“百詠”“雜詠”等稱,其內容和表現手法均與傳統竹枝詞相同,但在詩境上已經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開拓。滬上梨園竹枝詞的生成便是傳統竹枝詞邁向都市書寫的典范,報刊等新媒體的推動、租界文化的包容、商業消費模式的構建,在帶給戲曲更多可塑性空間的同時,也推動了以竹枝詞為代表的風土詩歌的都市化轉型。
一、新媒體的推動與梨園竹枝詞的創作空間
清代中前期著意以竹枝詞刻畫戲曲的詩作并不多,筆者據顧炳權《上海歷代竹枝詞》統計,其所收4000余首竹枝詞中,直接以戲曲演出為主題創作的不足1%,另有散見于清人詩文集中的零星之作。這一時期竹枝詞的創作涉及宮廷演劇,如康熙萬壽有“千秋令節艷陽天,歌舞分班行殿前。此日球場開牧馬,更無臺閣立飛仙”。①陳金浩:《松江衢歌》,顧炳權編:《上海歷代竹枝詞》上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12、13頁。民間則流行“三里一臺”的說法,如觀玉仙演《葛衣記》有:“三里歌臺未足奇,梨園只惜玉仙稀。垂簾擇得乘龍婿,院本當場笑葛衣。”②陳金浩:《松江衢歌》,顧炳權編:《上海歷代竹枝詞》上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12、13頁。更多的民間演劇涉及節慶與祭祀,如春日搭臺演戲(即春臺戲)有:“春臺好戲各爭強,忽聽新音韻繞梁。多少名班齊壓倒,讓他串客暫逢場。”①陳祁:《清風涇竹枝詞》,顧炳權編:《上海歷代竹枝詞》上冊,第102頁。樓船戲有:“學士文佳碑石刻,院傳仁濟住黃冠。藥王誕日樓船戲,即在高王廟畔看。”②沈蓉城:《楓溪竹枝詞》,顧炳權編:《上海歷代竹枝詞》上冊,第116頁。還有文人雅集的演劇,如施紹萃工詞曲,曾自制一舟,取名“隨庵”,并邀好友與伶人共同載酒為樂,竹枝詞有:“一天花影尋毿毿,峰泖云霞次第探。郎譜新詞儂按拍,興來攜客上隨庵。”③丁宜福:《申江棹歌》,顧炳權編:《上海歷代竹枝詞》上冊,第185頁。如此等等。梨園竹枝詞的創作仍處于散點視角,既無戲曲發展的宏觀把握,對演劇細節的關注也不夠深入。隨著晚清戲曲發展迎來又一高峰,在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下,以上海為代表的都市文化為竹枝詞的創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申報》在創辦時便刊登了《申報館條例》,其中明確了收稿標準:“如有騷人韻士有愿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區‘竹枝詞’及長歌紀事之類,概不取值。”④《申報》1872年3月23日。因報紙面向的讀者層面較廣,傳統文人詩只能與部分讀者產生共鳴,竹枝詞和長篇敘事詩在內容上更容易理解,創作要求也相對簡單,展現的風物民俗還可開拓讀者的視野,在創辦之初便納入了刊載視野。報紙上刊登文章往往要收取一定費用,而竹枝詞類作品“概不取值”,即免費刊登,吸引了更多創作者紛紛投稿。幾十年間,《申報》刊登的竹枝詞作品涉及民俗民風的方方面面,成為此類研究的重要史料。其中以戲曲類竹枝詞的創作為最盛,最早在《申報》見刊的有關戲曲的竹枝詞為《滬北竹枝詞》和《續滬北竹枝詞》,以后者為例:
自有京班百不如,昆徽雜劇概刪除。
街頭招貼人爭看,十本新排《五彩輿》。
金桂何如丹桂優,佳人個個懶勾留。
一般京調非偏愛,只為貪看楊月樓。
酒館方闌戲館招,才生弦索又笙簫。
無端忙煞閑身漢,禮拜剛逢第六宵。
案目朝朝送戲單,邀朋且盡一宵歡。
倌人請客微分別,兩桌琉璃高腳盤。
戲園請客易調停,酒席包來滿正廳。
座上何多征戰士,紛紛五品戴花翎。⑤懺情生:《續滬北竹枝詞》,《申報》1872年5月18日。
這組詩記載了海派京劇生成之前,京師梨園南下初期對上海梨園文化產生的沖擊,以及觀者對京劇的追捧和喜愛。《五彩輿》本屬徽班傳統劇目,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由春臺班搬演,歷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道咸年間曾于宮廷演出此劇,《故宮珍本叢刊》收其腳本,光緒間由四喜班發揚光大,名角王九齡、孫菊仙、梅巧玲、王瑤卿、馬連良均演過此劇,后福壽班、富連成班亦排演此劇。《五彩輿》是最早傳入上海的京劇連臺本戲之一,組詩第一首可推知此劇傳入上海的時間約為同治十一年(1872年)前后。其所演海瑞到嚴嵩府上拜壽,因忤逆嚴世藩而被貶淳安事,是為大眾所熟知的歷史題材,涉及人物眾多,非大型戲班不能承演,因而此劇制作相對精良,在上海掀起一陣熱潮。據張紅考證,傳世的《五彩輿》版本有腳本兩種、馬連良藏十本戲版本及車王府藏十六本戲版本,①參見張紅:《〈五彩輿〉連臺本戲研究》,《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詩中提及的十本戲版本內容或與馬連良藏本相近,但應不同于北京曾上演的徽腔版本,而是皮黃版本。組詩第二首中直言“一般京調非偏愛”,可知京劇在上海受到歡迎并非皆因聲腔,除了如《五彩輿》般豐富多彩的連臺大戲能夠大開眼界之外,還有名伶的個人魅力。如隸屬丹桂園的武生名角楊月樓,曾于上海梨園風靡一時,唱念講究,儀表堂堂,有“天官”之譽。京劇的演出吸引了大量觀眾,有些伶人或戲班紛紛效仿,“好是吳中窈窕娘,春風一曲斷人腸。只因聽慣京班戲,近日兼能唱二黃”。②袁翔甫:《續上海竹枝詞》,《申報》1872年4月12日。就連昆腔名劇《玉堂春》也可以京腔唱之,且愈加得以弘揚,正所謂“花樣翻來局局新,京腔同唱《玉堂春》”。③浙西惜紅生:《滬上竹枝詞》,《申報》1872年5月7日。組詩后三首可見京劇在上海流行初期觀者甚眾,且觀者身份上至達官貴族、下至無業游民,皆以看戲為日常休閑娛樂活動,竹枝詞中亦有“第一開心逢禮拜,家家車馬候臨門。姨娘尋客司空慣,不向書場向戲園”。④黃燮青:《洋涇竹枝詞》,《申報》1874年10月17日。而戲園吸引觀眾的方法之一就是早早送上戲單,竹枝詞還有“清早紛紛送戲單,新來角色大奎官。恰逢禮拜無閑事,好把京班仔細看”⑤夢蘭仙史:《洋場雜詠》,《申報》1874年6月7日。等句,戲單可謂戲曲廣告的雛形,其中受邀最勤的為妓館,竹枝詞云:“日日頻將戲目分,偏于妓館最殷勤。聲聲小姐來相請,今夜新燈好戲文。”⑥張春華:《洋場竹枝詞》,《申報》1872年7月12日。以丹桂茶園為代表的京班演劇獲得了巨大成功,加之常邀三慶、四喜等京班名角至滬上演劇,京班對上海的昆班、徽班皆形成了沖擊。大眾審美趣味皆向京劇轉變,“俏眼斜脧不自禁,先生也許訂知音。為郎愛聽京腔調,不弄琵琶換月琴”。⑦鋤月軒居士:《申江竹枝詞》,《申報》1872年11月11日。在此過程中昆腔式微,一度難以在梨園生存,“共說京徽色藝優,昆山舊部倩誰收。一枝冷落宮墻笛,白盡梨園弟子頭”。⑧葛其龍:《前后洋涇竹枝詞》,《申報》1881年5月8日。
《滬北竹枝詞》和《續滬北竹枝詞》中勾勒描繪了形形色色的都市文化生活,戲曲被視作其中一隅,僅僅經過兩年時間,1874年2月5日《申報》便刊登了署名“松江養廉館主”所作的《上海茶園竹枝詞》,凡29首,再現了梨園演藝的繁盛景象,涉及戲曲文化的諸多面向。此后,竹枝詞創作多以主題進行劃分,如煙館竹枝詞、女彈詞新詠、滬上青樓詞、香國流民乞食詞等,梨園竹枝詞也走上了專題創作道路,甚至單獨結集出版。以朱文炳的創作為例:
菊仙名角信非虛,聲調悠揚氣展舒。
一樣內廷老供奉,叫天相較果何如。
靈芝草木有三人,昔日京華賞鑒真。
海上僅來崔氏子,擅場第一《玉堂春》。
大觀名角紫金仙,小鳥依人亦可憐。
還有三花李百歲,戲迷傳亦各完全。
當日春仙邱鳳翔,戲中常供夜來香。
書生酸態描摹透,女子神情亦會裝。
伶隱爭夸汪笑儂,悔從宦海卜遭逢。
做官做戲何分別,下得場來孰改容。①朱文炳:《海上竹枝詞》,顧炳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228、281頁。
(1)重視手段忽視內在教學內容的改革。近年城鄉規劃相關學科的課程設置與教學模式上更多的是強調教學手段的信息化,如微博信息平臺互動教學的利用、微課教學形式的增加等,而對信息化時代大數據對本學科發展的積極作用以及對今后城鄉規劃職業的影響探討較少。
除前文提及的楊月樓外,滬上梨園的名角名家如百花齊放,這組詩中勾勒出的梨園名家群像,每首詩均圍繞一位伶人的技藝、樣貌或擅長的劇作展開,兼及生與旦、文與武,未見創作者自身的審美趣味和觀劇傾向,較為客觀地展現了大眾審美風尚。正是詩人將主體性抽離于作品,才使得竹枝詞實現了詩史功能,將戲曲藝術的發展狀態客觀直接地記錄和保存下來。
二、租界文化與戲曲藝術的可塑性
正如霍塞所言:“(上海)這個城市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靠它的商業力量逐漸發展起來。”②霍塞:《出賣的上海灘》,紀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4頁。在紛紛涌現的娛樂行業中,戲曲也爭相擠占市場。租界設立以后,因其有別于傳統的城市管理方式,在戰亂中為文化傳播營造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空間,成為西學東漸的重要媒介。19世紀60年代后,租界內的娛樂場所數量激增,茶館、酒館、煙館、妓館、戲館、賭館等大量開設,“昔諺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今則曰:下有申江”。此時的戲曲演出也呈現出“書場唱晚,響聞寶善之街。京戲偷看,擠斷百花之里”的繁盛景象,竹枝詞中對此時戲曲演出的盛況有大量的描繪,正所謂“洋場處處是逍遙,漫把情形筆墨描。大小戲園開滿路,笙歌處處似元宵”。③養浩主人:《戲園竹枝詞》,《申報》1872年7月9日。
租界中開放的社會風氣,改變了“男外女內”的傳統社會觀念,推動了女伶演劇及男女合臺演出。盡管女伶演劇在戲曲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都有零星記載,但多出現在家班或被視作“官妓”,并未面向廣大觀眾進行商業性演出,而真正的商業女戲班最先興起于上海的租界之中。同光年間,租界出現了女伶演唱京戲,起初被稱為“髦兒戲”。髦兒戲多為十二三歲女童登臺表演,既方便女眷觀劇,又不要求一定搭有較高的戲臺,多盛行于堂會演出,后由滿庭芳戲園名角桂芳將其帶入商業演出的視野,竹枝詞有載:“月中丹桂舞衣涼,坤角登臺滿庭芳。大戲亦教題桂字,取名應啖木犀香。”④朱文炳:《海上竹枝詞》,顧炳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228、281頁。坤角登臺給觀眾帶來了新鮮感,一時間形成了新的觀劇熱潮,“其時人心寂寞已久,忽然耳目一新,故開演之后,無日不車馬駢闐,士女云集”。⑤佚名:《女伶將盛行于滬上說》,《申報》1899年12月9日。髦兒戲的演出內容豐富,演員風貌佳音,都成為吸引觀眾的看點,“髦兒戲俏聽人多,一陣笙簫一曲歌。風貌又佳音又脆,幾疑月窟降仙娥”⑥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卷二,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156-157頁。“髦兒新戲更風流,也用刀槍與戟矛。女扮男裝渾莫辨,人人盡說杏花樓”。⑦養浩主人:《戲園竹枝詞》,《申報》1872年7月9日。可知髦兒戲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已在杏花樓進行比較成熟的商業演出,其中男性角色亦由女伶反串,且有武戲。“鴻福班頭吳月琴,虧她色藝本雙清。當場演出《天門雪》,試問梨園有幾人。”⑧蒲郎:《上海竹枝詞》,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517頁。吳月琴的《天門雪》演出一度問鼎梨園,達到髦兒戲演出的巔峰。繼杏花樓之后,不同的髦兒戲館之間競爭激烈,“髦兒戲館各知名,丹鳳群仙各競爭。漫道曉峰音調好,少娥亦是女中英”,①朱文炳:《海上竹枝詞》,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229、229、194頁。其中較為知名的為丹鳳樓和群仙樓,各具特色,不相上下,觀者趨之若鶩,一時風靡滬上。
作為典型的男女合臺演出的花鼓戲,在民間演出過程中屢次遭禁,“花鼓戲傳未三十年,而變者屢矣。始以男,繼以女,始以日,繼以夜,始于鄉野,繼于鎮市,始盛于村俗農氓,繼沿于紈绔子弟”。②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志·上海卷》,中國ISBN中心,1996年,第10頁。早期秦榮光《上海縣竹枝詞》曾有“花鼓淫詞蠱少孀,村臺淫戲誘鄉郎。安排種種迷魂陣,壞盡人心決大防”③顧炳權:《上海歷代竹枝詞》,第253-254頁。之句,當花鼓戲由鄉野走向都市,依然屢禁不止,租界也曾在清政府的照會下查禁花鼓戲,但始終網開一面,花鼓戲一度改稱為“灘簧”以求存,竹枝詞中對“花鼓戲”和“灘簧”均有記載,前者有“暢月樓中集女仙,嬌官唱出小珠天。聽來最是銷魂處,笑喚冤家合枕眠”,④云間逸士:《洋場竹枝詞》,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458頁。后者有“灘簧曲子自成腔,五鳳樓中竟少雙。編得淫詞供俗賞,一班游女興難降”。⑤朱文炳:《海上竹枝詞》,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229、229、194頁。由兩首詩中的描述可知,花鼓戲不僅在都市文化中受到廣泛認同,且在上海的禁戲力度并不大,給予了花鼓戲發展的空間,暢月樓和五鳳樓更為花鼓戲的演出搭建了平臺。隨著越來越多的坤伶登臺,演技精湛的名角也受到追捧,竹枝詞“女伶封王”有云:“尋常一輩少年郎,喜為坤伶去捧場。金字寫來如斗大,崇銜喚作某親王。”⑥葉仲鈞:《上海鱗爪竹枝詞》,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332頁。而在清政府的嚴格禁令之下,北平梨園直至民國初年才開始有坤伶演戲,“民國初元,平市始有坤伶之發現……老俞之子俞五見有機可乘,遂爾招致坤伶,借以標新立異。當時遞呈警廳,請解坤伶入京之禁。批準后,即在香廟建一戲棚,仿外埠男女合演之例”。⑦醒石:《坤伶開始至平之略歷》,《戲劇月刊》1928年第1期。
滬上登臺演出的另一新興群體是串客和票友。所謂票友,即“不以優伶為職業,以道樂而學戲劇者,成為票友。南方名:清客串”。⑧波多野乾一:《京劇二百年之歷史》,鹿原學人編譯,上海:啟智印務公司,1927年,第123頁。“票房之創,肪于北直,風尚所趨,爰及上海。”⑨義華:《上海票房二十年記》,周劍云編:《菊部叢刊·歌臺新史》,上海交通圖書館,1918年,第16頁。光緒間,上海成立了專業的票房“盛世元音”,由蓋叫天、趙小廉等名伶指導,成員皆為戲曲愛好者。此后還有市隱軒、雅歌集、遏云集等知名票房,玩票成為上海劇壇的另一片陣地。竹枝詞諸如“殘蠟人多串戲來,皖南野鶴亦登臺。當場一出《胭脂虎》,喝彩聲聲震似雷”“逢場作劇便忘形,海上名流學老伶。優孟衣冠梁夢影,先生女生總明星”,⑩朱文炳:《海上竹枝詞》,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229、229、194頁。不論是富紳堂會還是專門的票房演出,每每有某先生或某女生之類的名流登臺。民國時,雅歌集票房還成立了專刊《雅歌集特刊》,串客和玩票成為職業演出之外的演劇新風尚。
西風東漸的過程中,先進科技傳入中國,上海的都市文化以其獨有的包容性推進了現代文明的進程。中國傳統的戲曲演出中曾以真馬、真虎等大型動物登臺,以增強戲劇的真實性,當西方的馬戲傳入中國,為中國的表演藝術開拓了視野。1882年,號稱“天下第一馬師”的意大利馬戲表演家車利尼到上海演出時,《點石齋畫報》刊載竹枝詞有:“絕技天然出化工,雖云戲術亦神通。可知事到隨心欲,猛獸也將拜下風。”“海外名班車利尼,象獅熊虎舞翩躚。座中五等分層次,信是胡兒只愛錢。”①辰橋:《申江百詠》,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92頁。其中將馬戲也歸為“戲術”,如“化工”“翩躚”等評點之語皆挪用中國傳統藝術的評點語言。1908年,意大利人又在上海拍攝了第一部電影《上海第一輛電車行駛》,繼而美國人在上海創辦亞細亞影片公司,電影以“影戲”的稱呼定位,成為又一種流行“戲術”:“東西影戲到春申,活動非常宛似真。各式傳奇堪扮演,一經入目盡稱神。”②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卷二,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134、156頁。影視文化的涌入給傳統戲曲帶來了巨大沖擊,不僅吸引了大量觀眾的眼球,也有一些伶人投入到戲曲題材的電影拍攝中。但畢竟電影的制作成本比較高,一些名伶為擴大自身的影響力,也有選擇轉向灌制唱片,為近代戲曲藝術留下了珍貴的有聲資料。竹枝詞“留聲機器行”條便對此進行了記述:“伶人歌唱可留聲,轉動機關萬籟生。社會宴賓堪代戲,笙簫鑼鼓一齊鳴。”“買得傳聲器具來,良宵無事快爭開。邀朋共聽笙歌奏,一曲終時換一回。”③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卷二,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134、156頁。留聲機在給受眾帶來新鮮感的同時,也滿足了足不出戶即可聽曲的需求。從演劇群體的擴大到全民參與,再到中西合璧,短短數十年間,戲曲以其極強的可塑性在租界文化的滋養下迅速發展。
三、商業驅動與梨園消費文化的建構
京師梨園南下之前,上海的演劇場地多為茶樓或戲棚,比較簡陋,有的甚至為露天舞臺,北京戲班將京城戲園的氣派帶到上海。紅桂茶園為上海第一家較為氣派的戲園,將“茶園”代指戲園亦源于北京,“據聞清代乾隆盛時,前門一帶戲園林立,極歌舞升平之勝,而皇室貴胄八旗子弟征歌選舞毫無顧忌,致為純廟所聞,赫然震怒。有旨八旗都統約束各旗并招五城察院勒停戲園……嗣以皇太后萬壽御制戲曲,傳集名伶進宮演唱,藉伸慶祝。由是禁令漸弛。前門一帶昔時歌舞之場遂得重振旗鼓,開臺再演。惟不敢顯違功令,乃改頭換面,避舊日戲園之名,易其市招為茶園。并稱戲價曰茶資,世世相沿,即上海戲園亦援京師成例”。④《戲雜志》1923年第9期。此后名稱各異的茶園在上海灘上紛紛建立,據統計,從同治初年到宣統年間,上海的職業戲園約120家,其中最著名的丹桂、金桂、天仙、大觀合稱為“清末四大京班戲園”。
飛座:青鳥何曾一柬通,酒壇驀地集飛鴻。深心不肯多留戀,恐有新人在意中。
留條:人來不速靜無嘩,莫道瘋狂錯認衙。拼卻十千沽美醉,樽前添得一枝花。⑦藝蘭生:《宣南雜俎》,張次溪編纂:《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年,第514、514、514-515頁。
酒席間如有伶人為他人所召,客人便隔座相問,名曰“飛座”;為避免伶人錯認座席,便在官座上留有便條,便于辨認,由此生成“留條”之規;此外還有“挑眼”,即指客人別有所屬,伶人間相互妒忌的情狀,等等,此類行話中充斥著濃重的商業色彩。伶人侑酒的商業利潤豐厚,導致一時間童伶之風興起,年僅12至16歲間的伶人紛紛站臺,流連于商賈豪客之間,成為商人階層炫耀財富的一道獨特風景。但雛伶正處于學藝的起步階段,便淪為戲班老板謀求戲外之財的工具,極大地影響其演藝水平,聲音細弱,不識音律,舞臺功底遜色,臺上功夫的欠缺都靠臺下侑酒來彌補。
大型戲園一般單獨設置“官廳”“包廂”,若普通觀眾多付戲價,想得到更舒適的待遇,戲園又有“樓廳”“邊廳”,可以“包定房間兩側廂,倚花傍柳大猖狂。有時點出風流戲,不惜囊中幾個洋”。⑧養浩主人:《戲園竹枝詞》,《申報》1872年7月9日。可見觀者為得歡愉,包廂觀劇是比較普遍的。觀劇往往攜妓侑酒,謂之“叫局”,“一陣花香香撲鼻,回頭行過麗人來。吳娘喚到淡妝同,醉臉霏微淺露紅。隔座忽傳鴛牒下,花香釵影去匆匆”。①花川悔多情生:《滬北竹枝詞》,《申報》1872年9月9日。從竹枝詞的描繪可知,邀妓觀劇的場景頻繁出現,即便同時同地觀演同一部劇,同一位妓女也可能收到不同的邀請,于是在演劇時奔波于不同包廂之間,如臺上伶人換場一般,儼然已經成為戲園的另一道風景,人們爭先光顧觀演的熱鬧場面被概括為:“丹桂園兼一美園,笙歌從不問朝昏。燈紅酒綠花枝艷,任是無情也斷魂。”②海上逐臭夫:《滬北竹枝詞》,《申報》1872年5月18日。也有攜妓觀劇避人耳目選擇包廂就座的,“茶園丹桂滿庭芳,到底京班戲更強。出局叫來終不雅,避人最好是包廂”。并注:“包廂,在臺之兩旁,有門可避人,伴妓共肩者,都掩飾于此。”③洛如花館主人:《春申浦竹枝詞》,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64-65、65頁。妓女伴座時還提供水煙,“偶聞新戲便傷哉,怕向園中看一回。只恐尊親人在座,娘姨裝過水煙來”④洛如花館主人:《春申浦竹枝詞》,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64-65、65頁。“鑼鼓聲喧戲上場,阿儂最喜坐包廂。裝煙大姐直忙煞,才罷張郎又李郎”。⑤苕溪醉墨生:《青樓竹枝詞》,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491頁。在陪同看戲的過程中,如果客人不熟悉戲情,妓女還為其詳細講解劇情,竹枝詞有:“邀同看劇包廂樓,促膝殷殷體態柔。節拍新掐渾未識,嬌聲為我說從頭。”⑥辰橋:《申江百詠》,顧柄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第105頁。此時的戲曲演出作為商業運營的一部分,其利潤來源不僅是一張戲票的價格,更多來自于叫局、侑酒等,用豐厚的盈利再對戲曲演出進行反哺和包裝,臺上之戲得以不斷精進,使得戲曲文化產業走向良性循環。
四、風土詩歌在都市文化傳播中的價值張力
《文選·序》有云:“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⑦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頁。竹枝詞本由巴蜀民歌發展而來,以吟詠風土為主要特色,常在描摹世態民情中呈現出鮮活的文化個性和濃厚的鄉土氣息。自《申報》公開征求竹枝詞與長篇紀事詩相關稿件以來,大量描繪上海都市生活的竹枝詞創作涌現出來,客觀上促使竹枝詞脫離了鄉土氣息,轉向都市書寫,在都市文化傳播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首先,竹枝詞中大量記載了近代上海戲曲的變革,包括京師梨園南下、伶人技藝與舞臺生涯、戲曲評論等,客觀反映出滬上梨園的發展變化狀況,以及都市社會文化對戲曲發展進程的影響。在海派京劇誕生之前,京師梨園南下為海派京戲的生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是傳統戲曲近代化的先聲,但在戲曲史研究中因其處于過渡性階段而較少受到關注。《申報》創刊之初便有多首竹枝詞圍繞京戲南下而撰寫,其中涉及最早由北京傳入上海的京戲連臺本戲、京戲名角到上海演出情況,以及觀眾的喜愛和追捧,等等,這些都為海派京戲的生成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竹枝詞的書寫還伴隨了海派京戲的發展、昆曲徽班的衰落等,種種戲曲變革盡收眼底,連綴起來可形成一部小型的晚清民國上海戲曲史。
其次,竹枝詞中描繪勾勒出梨園都市化、商業化的共享文化空間。清代中前期的觀劇活動多為家班演出,后逐漸演變為堂會演出,甚至是私寓性質的演出,觀者數量均控制在較小規模,幾乎未見大規模的商業性演出。上海的滿庭芳、丹桂茶園等大型娛樂場所的開設,以及租界對大眾娛樂的跨文化包容,開創了觀看戲曲演出的新范式。戲園設計宏大奢華,觀眾席的設置可滿足不同階層的需要,劇場中相應提供各種服務,觀眾和演員亦可近距離接觸,戲園逐漸成為綜合性娛樂消費的場所,既可滿足觀劇聽曲的審美需要,還成為商人、仕宦炫耀財富和提升社會地位的新平臺。竹枝詞中記錄了這一共享文化空間生成的細節過程,生動再現了滬上梨園的繁華景象。
最后,戲曲文化空間的嬗變彰顯了近代都市社會觀念的變遷。上海素有“梨園之盛,甲于天下”的美譽,伴隨戲曲文化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其每一次變革不僅是審美層面的創新,更蘊含著觀念的變化。女伶登臺演出極大地挑戰了“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自同光年間始,上海梨園不僅出現了以女性為主體的演出班底,還支持男女同臺的演出形式,打破了傳統戲曲舞臺上演員性別結構單一化的格局。舞臺上的坤伶演出不僅實現了女性自身的解放,還起到了啟迪民智的作用。眾多女性觀眾步入戲園,舞臺上的戲曲故事豐富了她們的視野,舞臺上的伶人也使她們意識到女性的社會作用不只是局限于家庭角色,甚至許多閨閣小姐與貴婦都曾以串客或票友的身份親身登臺,內心的解放意識以此得到宣揚。買辦和富商對公眾娛樂產業的經濟支持也體現了近代工商觀念和商賈階層社會地位的變遷。當西方近代工商觀念傳入中國,最先受到影響的都市便是上海,事實上,商人是推動晚清上海戲曲變革的最主要消費者和核心力量,其推進方式不僅在于投資興建大型戲園,還效仿明清時期的貴族、文士與伶人過從甚密,進行一系列捧角活動,在產生大量經濟效益的同時,也一度成為其躋身上層社會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