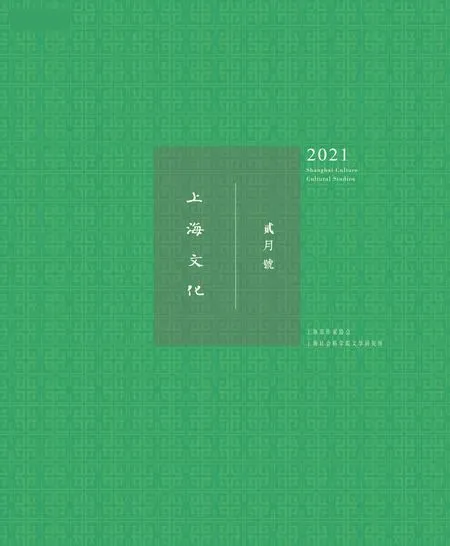卷首語
在21世紀的第21年,很多人都期待著“牛”轉乾坤。
這當然是一個美好的愿望。然而,我們肯定還將面對一個復雜的環境:疫情還會反復,全球生態和氣候問題無人可以躲避,國際之間還會有各種矛盾沖突,社會階層且分化且固化,大眾文化撕裂……重重疊疊的問題之中蓄積著突破和創新的能量,只等時機成熟。誰也無法預料,明天早上起來,人類又會在能源、生物、人工智能等領域開辟出一個什么樣的新天地。
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人文精神和現代文明的領域,除了應對不同層面上的新問題之外,還是始終要面對千百年來的老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人應該如何生活,或者說,什么樣的生活才是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雖然理想不是用來實現的(可以實現的只能是“小目標”而已),但是也不能放在遙遠的未來,而是要用它來照亮現實,在當下的現實中發生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段話是對文藝工作者說的,也同樣適用于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研究者。
學術研究不能沒有理想,也不能沒有現實關懷,為此,需要有思想、立場、方法,需要利用全人類歷史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它們并不因時隔久遠就變成靜止的,而是如同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一刻不停地在我們身邊流動著,它們一直都是現在進行時。不斷重讀經典,乃是走向理論前沿的正道,而唯有正道,才是捷徑,所謂“彎道超車”,只是實踐中的權宜之計。
1921年1月1日,在上海編印的文化雜志《新青年》第8卷第9號刊出蔡元培先生的《文學研究會宣言》,其中寫到:“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一百年過去了,這樣一種信念和工作態度,是不是依然值得倡導和秉持呢?文學和文藝,是不是依然“于人生很切要”,構成基本的人文教養呢?
當然,文學和文藝的本質、形態、效用,以及我們對它們的理解,已經大為不同,而且還在變化之中。邊界擴展,界限消融;人文與科技的結合,經過三五百年(從盧梭或達·芬奇的時代算起)的摸索,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開始起步。五年前,Alpha Go橫空出世,宣告“未來已來”。現如今,我們難以想象五年之后的A I時代將會是怎樣一幅景象。可以確定無疑的是,文化成為生活本身,將會在城市文化中表現得更為顯著。文學、文藝和文化研究者的眼光,早就不得不從文本的字里行間,延伸到城市的大街小巷,乃至于圖像、裝置、屏幕和虛擬空間。在日新月異的時代里,“學者”作為“學習者”的自我認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在新的起點上,本刊再一次調整提高,奔赴偉大的新時代新征程。在此,我們感念過去30多年里曾經為本刊付出心血的前輩們,感謝為我們出謀劃策的各位師友。期待學界同仁的鼎力支持,做好我們共同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