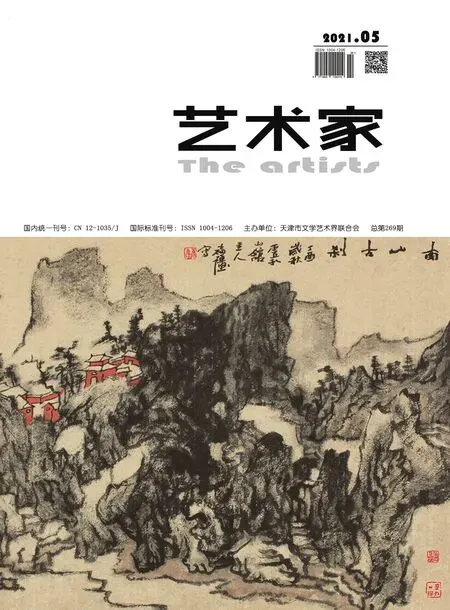小號藝術中民族化特征研究
□年 昊 沈陽音樂學院(音樂教育學院)
小號在西方音樂及相關樂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首先被應用于軍樂隊的演奏中,在長時間的使用和拓展過程中逐漸具備了與我國民族文化息息相關的文化特征,尤其是當代中國小號音樂的創作過程中經常會用于表達一種陽剛性的音樂力量[1]。本文將針對我國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進行探討,同時對小號的發展歷史與文化特征進行分析,最終對當代小號藝術在發展進程中表露出的民族化特征進行總結。
一、中國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
民族文化的形成受到當前民族的歷史發展、民俗文化、政治經濟、人文地理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是一種客觀存在、深入影響且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變化、容納、發展的文化類型[2]。也正因如此,當代民族文化的特征相較于歷史其他階段民族文化的特征必然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深入分析后,我們也能發現雙方存在深入和緊密的聯系。結合當前中國的實際發展情況來看,中國民族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在長期的封建社會歷史中逐漸形成一定的規則,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革開放、文化思潮等多個階段的變化以后,民族文化特征發生了極大的改變[3]。筆者認為,當前階段,我國民族文化特征更強調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充分發展社會經濟,同時在此基礎上積極吸收以往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優秀民族文化特征,最簡單的文化特征,如尊老愛幼、保家愛國、報效國家等,這些都是潛藏在中國民族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特征[4]。
二、小號的發展歷史與文化特征
小號經由西方傳入中國已有百余年的歷史,在發展過程中涌現出諸多適合小號演奏的音樂作品,對推動小號藝術在中國的發展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由于一百年前中國處于特殊的歷史階段,在小號傳入中國的過程中,相關創作者、演奏者受到特殊歷史條件的影響,不由自主地賦予了小號與中國文化相關的歷史特征[5]。雖然,當前我國社會發展條件與100 年前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但在小號本身特點的基礎上,小號在流入中國的最初階段被賦予的歷史文化特征被發揚光大,開始廣泛應用于我國音樂潮流的發展中,潛移默化地對小號的民族化特征產生了相應的影響。也正因如此,當前階段,我國范圍內的小號作品仍是在西方音樂的調試基礎上進行再創作,但中國音樂創作人在本身審美思想、文化思潮的引導下也逐漸賦予小號在創作和演奏過程中不同的民族化特征。
三、小號藝術發展過程中的民族化特征
(一)小號藝術發展過程中創作的民族化特征
首先,對小號藝術發展過程中創作題材的民族化特征進行分析。題材既是小號音樂作品創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內容,又是賦予小號音樂藝術民族化特征的前提。在小號藝術發展過程中以創作題材角度賦予小號藝術民族化特征,其最初階段是由創作人員將中國的經典民歌、民間樂曲等題材轉換為小號藝術作品的形式[6]。例如,我國著名的音樂教育家、小號演奏家朱啟東先生,在小號藝術創作過程中,根據新疆民歌編制了小號獨奏曲《阿拉木汗》,根據陜北民歌編制了小號作品《秋收》,根據民間樂曲中的笛子獨奏曲編制了小號作品《喜相逢》,這種直接從中國民族文化歷史產品中獲取題材并進行小號再創作的行為,對賦予小號藝術民族化特征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基礎作用。在小號藝術的后續發展中,也有創作者使用中國音樂元素編制小號樂曲,在小號藝術創作中融入中國特有的民族韻味。例如,我國著名的小號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許林先生,他曾經創作的小號獨奏曲《秧歌》《花燈》《溜冰》《兩個小伙伴》等均是在小號藝術創作過程中融入中國民族文化內容,從而有效凸顯中國民族文化的特征。又如,我國著名的小號演奏家羅平先生曾經創作了《牧羊姑娘》《帕米爾的春天》等歌曲,這兩首歌曲都是根據我國內蒙古傳統民歌改編而成的,對豐富小號藝術作品的形式內容、文化特征發揮著非常積極的作用。此外,黃日照先生創作的《山歌》《嘎達梅林》,以及陶嘉舟先生創作的《趕車》、李誕生先生創作的《帕米爾在歡唱》等都是從我國諸多民族文化中提取的創作題材,富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有效豐富了小號藝術作品的民族化特征。
其次,對小號藝術發展過程中創作風格的民族化特征進行分析。藝術風格是體現藝術作品特色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反映當前藝術已經發展至成熟階段的重要標志。小號藝術的民族化創作想要充分表現其已經具備的民族化特征,就要結合我國的地理環境、社會歷史、文化傳承、風俗習慣、經濟發展等多項因素,充分體現中華民族特有的審美趣味與美學追求,鮮明反映中華民族共有的文化傳承和文化力量[7]。以許林先生創作的《降B 大調小號協奏曲劉三姐》為例,該作品充分汲取了廣西地方戲曲《劉三姐》與廣西民間歌舞《劉三姐》等題材的內容,同時將上述內容與宜山民歌中的“柳柳羅”、柳州山歌中的“棒冬棒”有效結合,在充分發揮小號作為銅管樂器演奏特點與演奏技巧的基礎上,將作品的演奏形式與上述題材內容的音樂語言、審美需求有效結合。在具體的調式調性層面上,雖然該作品為降B 大調,但不拘泥于降B 大調,以樂曲內容中的情節表現、民族風格為基礎,大量使用了我國傳統文化特色中的商、徵、角、羽調式,對小號藝術的民族化特征容納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也正因如此,小號藝術作品本身的演奏個性與演奏技巧,雖然與我國民族傳統文化作品的演奏形式、文化審美等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只要不斷磨合、不斷創新、不斷改編,也能達到兩者兼顧的創作目的,從而真正在小號藝術創作過程中實現小號藝術與民族文化之間的緊密聯合。
(二)小號藝術發展過程中演奏的民族化特征
需要明確的是,任何一種樂器在實際演奏過程中所具備的演奏技術技巧、音樂表現能力均具有相應的局限性。在小號藝術發展過程中,想要實現其演奏技巧的民族化,演奏者必須充分熟悉小號本身的性能特點、音色音區、運指規律、華彩技巧等,要充分貼合小號作為樂器所具備的個性魅力與演奏規律,才能將小號的演奏藝術與我國的民族文化情感、民族音樂影響、意境技術技巧等有效結合,逐步探索出適合表現我國民族音樂頻率的技巧系統[8]。以朱起東先生創作的《喜相逢》為例,該作品的創作題材源于內蒙古、山西區域的民間笛子小曲。演奏者在樂曲開始階段要盡量模仿笛子的“滑音”演奏技巧,充分表現離別時的傷感情緒;在第一變奏時要運用小號的“短吐音”演奏技巧,表達久別重逢的迫切心情;在第二變奏時要運用小號的“連續音程大跳”演奏技巧,凸顯喜相逢的主題情緒;在樂曲結尾時則要運用小號的“滾奏”技巧,再次模仿笛子演奏時的花舌技巧并以此凸顯相聚的喜悅情緒。總體來說,小號在演奏過程中想要與中國民族文化特征緊密融合,演奏者必須在充分保留和發揮當前小號藝術演奏性能特點、演奏技巧的基礎上,對傳統小號藝術演奏技巧進行拓展、改編、容納,達到凸顯我國傳統文化思想內涵、民族風格的目的。
結 語
綜上所述,小號作為一種西方傳統樂器類型,雖然其演奏方法與演奏技巧均以西方音樂內容為基礎,但小號在藝術作品創作及當前階段的演奏過程中仍然能夠與我國民族文化有效結合。小號藝術作品與民族傳統音樂、審美品位、文化特征的有效結合,是探索小號藝術作品民族化特征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豐富我國文化內涵的重要措施。在小號藝術作品的后續發展中,小號民族化的推進也必須以民族文化的審美價值觀念為基礎,在作品創作與藝術表演的過程中既要體現民族風格的審美特征,又要展現中國文化的深刻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