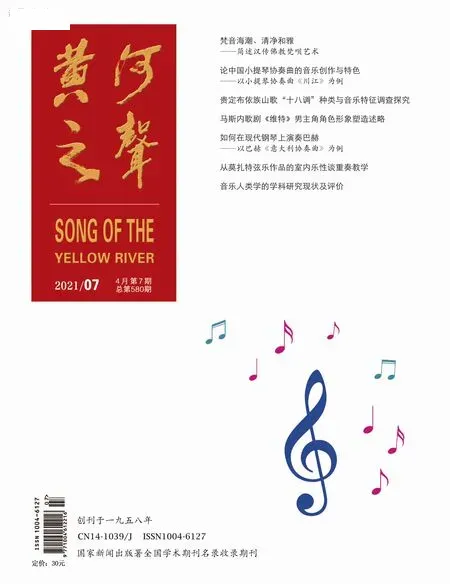音樂哲學的價值取向
張 竹
近些年,伴隨社會需求的變化,音樂在我國社會活動中的作用也逐步凸顯,與音樂相關的哲學研究也層出不窮。但是,出于各種條件的制約,難免會產生研究成果良莠不齊的現象。產生這種成果泡沫化的原因,主要是一些研究者望文生義,錯誤地理解國外的音樂哲學意義。哲學概念本身就晦澀難懂,其詞性的本意以及派生出來的引申意義與比喻意義支脈復雜。往往一個單詞的理解偏差就會出現會意上的南轅北轍。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以及翻譯水平參差不齊,致使這樣的錯誤屢見不鮮,以這樣的翻譯文本為開展研究,出現適得其反的結果也就不足為奇。此外,一些研究者生搬硬套,大量截取中文二手文獻,對外文原著棄之敝履,這也是虛假的、偏頗的研究成果產生的原因。本研究試圖從音樂相關哲學思想的理論內核入手,一步步剖析中國音樂理論的哲學取向,解讀音樂相關哲學與后現代語境結合狀況,從而在一定程度促進音樂哲學思想研究正本清源。
一、音樂哲學思想的產生與理論內核
(一)音樂哲學思想辯證思維的產生背景
上世紀末期,多元化思潮在美國興起,在這種思潮的沖擊下,原本被奉為圭璧的審美核心論、西方核心論的音樂觀念與哲學思想幾乎被質疑的聲音淹沒。其中聲勢最大的,是來自被稱為審美音樂之父的雷默的擁躉與學生大衛?艾瑞特。從實踐的角度看,大衛?艾瑞特的質疑并不突兀,他主修爵士小號,演奏中多是即興發揮和靈感觸動,與雷默提倡的通過審美經驗堆砌構架的審美音樂哲學思想體系大相徑庭。1988年,大衛?艾瑞特發表文章,對雷默的哲學理論進行反思,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擴充了音樂相關哲學的實踐意義。1995年,大衛?艾瑞特再次撰文,確立了音樂哲學思想的實踐主體。這篇文章也促成了美國音樂哲學中審美與實踐兩種思潮的對立。這種非黑即白的對立哲學思維,曾經長久占據音樂哲學思想的陣地。2001年,愛思特?喬根森連續撰文,將辯證的音樂哲學思想展現在世人面前。在文章中,喬根森剖析了以往音樂哲學思想的局限之處,認為辯證的思維方式才會得到客觀的結果。喬根森的音樂哲學辯證論所以產生,并非一蹴而就,在她之前霍奇斯就認為在音樂哲學思想研究中,應該持有包容對立面的胸襟。隋默也在其研究中做出過類似推斷,并以融合論來作為音樂哲學思想的核心,將審美與實踐兩個對立的思想派別融合于音樂哲學中。
綜合來看,喬根森的辯證思維體系,更偏重于音樂這一主體本身,認為音樂相關哲學既包含整體音樂框架,又涉及具體音樂細節的反思,而非簡單的美學延伸與音樂實踐。喬根森以宏觀的、多元化的哲學視角,打破了音樂哲學研究的桎梏,指出了音樂哲學辯證的認知本質,是從音樂實踐中歸納相關哲學認知,再由這些認知來指導音樂實踐。喬根森還從本體論、政治論和價值論的角度進一步闡述辯證的音樂哲學思想,指出音樂活動與體驗的人文價值、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喬根森肯定了音樂哲學的藝術與審美因素,同時還強調其道德屬性和倫理屬性。
(二)音樂哲學思想的辯證理論內核
基于黑格爾的辯證哲學理論,審美與實踐兩種音樂哲學思想,就彷如白天與黑夜,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是獨立與聯系的結合體。縱觀世界音樂的發展歷史,每一種理論模式、每一種實踐方法既存在于獨立的時空象限中,又相互依存,彼此促進。音樂哲學中的辯證思維,是辯證法在音樂活動實踐中的具體體現,而非武斷的評判和片面的否定。喬根森在其《理論與實踐的辯證觀》中,點明音樂的哲學研究往往從不同的路途出發,得到殊途同歸的結果,或者因為一瞬間的靈感爆發,讓研究結論與初衷南轅北轍。因此,面對本來就容易產生爭議的哲學研究,往往會因為固執己見而脫離全局的視野,產生研究上的軌道偏差。在具體的音樂活動實踐中,審美與實踐兩種范式是可以靈活地運用的,要遵循其中的關聯層面,還要正確評判二者本身固有的爭議,這樣才能避免實際音樂哲學研究中的錯誤趨勢。所以,只有從辯證的角度正確認識到音樂哲學思想的獨立性與同一性,才能從廣度上拓展音樂哲學的研究維度。具體來說,最能體現理論結合實踐的辯證統一思維的,就是音樂的實踐活動,具體操作中要體現思辨的角度、靈活的手段和突破的勇氣。其實,翻開國內外的音樂發展史冊,在實際音樂活動中往往是審美與實踐并重,并沒有明顯的界限劃分。針對專業與非專業兩種類型的音樂活動,應該選擇不同的側重點來進行分析和考量。對于專業類的音樂活動,要以音樂實踐方面的理論為主,豐富音樂理論,強化音樂技能,為從事專業的音樂活動夯實基礎;對于非專業類,則要立足音樂文化角度,提升鑒賞與品評音樂的能力。此外,音樂活動不能脫離音樂環境與背景,要充分考慮音樂文化的國家特色和民族特色,在音樂哲學研究過程中要體現相關傳統與傳承的針對性。音樂實踐不是片面的繼承和武斷的灌輸,要從多角度、多層面進行思辨性探索。只有這樣,從實踐中認知的哲學思想才能通過實踐的驗證。音樂活動的參與者,要保持與時俱進的探索作風,不斷從實踐音樂與前沿音樂中汲取新的養分,而不是權威崇拜和僵化照搬。
音樂經驗與音樂現象,都是音樂實踐核心哲學觀的發生源頭。從目前的音樂哲學研究現狀看,多數研究只停留在經驗的總結階段,缺乏思辨性推演和前瞻性評估。哲學在音樂中的作用,是培養音樂人的思辨能力,讓他們的日常音樂活動更具目的性、操作性和預測性,避免機械式的、復印式的僵化音樂演繹。在實際音樂活動中,應該充分認識到哲學所具備的統籌作用,在哲學的框架中找尋最合理最科學的方向與方法,要兼顧審美與實踐,忽略了審美的實踐,只不過是單純的技能競賽,而忽略了實踐的審美,也不過是脫離環境的孤芳自賞。這兩種片面的音樂實踐方式,都背離音樂的本質。音樂是一種內涵豐富的資源,兼具著品鑒欣賞功能和社會人文功能,更是文化傳播的一條主要路徑,音樂正是為此才能夠源遠流長。總之,音樂以及其理論與實踐,是否合理,是否科學,都要靠辯證的思維來檢驗。
二、音樂理論的哲學取向
國外音樂哲學居于審美與實踐的論戰,也引發了中國音樂理論在哲學取向上的爭論。
(一)音樂的審美核心哲學取向
審美核心的音樂哲學取向脫胎于上世紀官方主流理論——美育論。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外審美核心的音樂哲學思想就影響著我國的音樂哲學取向。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我國的音樂活動多是關注音樂社會功效,而忽略了其審美與專業的本質。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借鑒國外的審美理論,我國對音樂的哲學觀進行了審美化修正。這種審美哲學觀,是美育論的一種繼承,具有階段意義的合理性。然而隨著時代進步,單純的“審美”已經不能順應文化觀念的變革,明顯不能適應時代需求,學界進行了深入的反思與討論。曾任《中國音樂》副主編的管建華通過后現代音樂理論對純粹美學的音樂理念進行反思;周憲也以審美現代性批判理論來探究審美核心哲學取向的思想禁錮性。
(二)音樂的文化核心取向
相對于審美核心觀,文化核心觀則更加重視音樂的文化屬性,認為音樂的人文性賦予其文化傳承與文化認同等使命。作為我國音樂文化核心哲學觀的先驅,管建華歸納了眾多音樂領域的哲學研究成果,并依此為基礎點明哲學審美核心觀的片面之處,試圖以多元化的思想來完善音樂哲學體系。綜合來看,審美哲學觀基于二元論哲學,從審美的角度出發,解析主客體間的客觀反射,更注重音樂作品的審美功能。而文化核心觀更突出音樂的廣度,以一元論的哲學視角,強調音樂的人文本質。
(三)音樂的創造核心哲學取向
2007年,在充分考慮國情需要和時代需求,并對我國音樂的創造力匱乏現象進行反思基礎上,王耀華提出創造核心的音樂哲學觀。這種哲學觀將創造當作整個音樂體系的中軸線,涉及音樂在審美、文化和功能上的創造屬性。音樂的創造,具有強烈的時代意義,具有廣沃的包容性,提倡音樂實踐的創新。王耀華認為創造的潛能是每個人都有的,這賦予了兒童音樂天賦開發的哲學基礎。創造核心觀兼顧了音樂美學中審美與立美的雙重屬性,突出了音樂哲學思想的實踐意義,同時指出單純的音樂實踐核心哲學思想,容易孤立音樂的外延,產生為實踐而實踐的偏執狀態,限制音樂的創造性功能。王耀華肯定了音樂創造要以音樂文化為基礎,同時還指出了音樂文化核心哲學觀的維度局限,認為文化核心觀不利于音樂的延伸進步,音樂應該用傳承激發創造,用創造促進傳承。對于創造核心觀,一些研究者也提出質疑,認為片面強調創新的音樂活動,將弱化音樂的審美功能。
(四)音樂的多元化哲學取向
針對音樂哲學取向的爭論,很多國內研究者依據雷默的兼容理論,提出包容審美、文化與創造的音樂多元化哲學觀,試圖打破各種哲學觀的片面性。劉沛東在2004年依托音樂的價值取向,總結了以往各種音樂哲學觀的利弊,提出兼容且多元化的音樂哲學觀。劉沛東認為,音樂的各種價值維度,包括文化、實踐與功能,正在進行融合,而多元化的哲學觀因其多維度的兼容性,更利于音樂邏輯體系的形成。崔學榮分析了各種哲學觀的兼容可能,指出兼容的、多元的音樂哲學取向對音樂的實踐指導意義。此外,吳悅悅、資利萍和朱詠北等研究者從三維的角度進行了音樂哲學思想的研究。
三、音樂哲學與后現代語境的結合
以往審美與實踐兩方面音樂哲學取向的劃分,存在很明顯的人為痕跡,缺乏對二者內部關聯的充分探討。而辯證主義的哲學論點,往往會從整體的高度、以多側面的分析方式論證融合的可能。喬根森的研究肯定了審美與實踐的共存性,認為音樂的辯證哲學思維與后現代語境具有高度的契合趨向。藝術符號學理論指出,表象化世界的思想與行為,都具有整體特征,喬根森以此理論來論證音樂中的辯證思維所蘊含的整體意義。她分析了后現代主義哲學觀點的矛盾之處,從而明確了辯證思維是解決音樂哲學問題的合理路徑。
結 語
從哲學的高度來研究音樂相關問題,就是音樂哲學,研究角度的差異、基礎哲學背景的不同,都會令音樂的哲學取向產生分歧。中國的音樂哲學研究方興未艾,集合了大量的專家學者,使這一門新興的學科有了飛躍式的進步。從發展的眼光來看,我國的音樂哲學研究正逐步由個體研究轉化為群體研究,其中如五月天等研究陣營正闊步登上國際舞臺,獲得了很高的國際聲譽。國內的音樂哲學研究組織正朝著正規化的方向邁進,學術研討會已經成為常規化的學術活動。隨著國內音樂哲學研究維度的擴張,更深層次的思想撞擊與更合理的研究成果必將大量涌現,這對中國音樂事業的長遠發展無疑是一件幸事。在中國,專家學者們已經開始反思音樂哲學中存在的具體問題,但目前仍存在一些偏差,比如在學術上的崇洋媚外,照搬照抄國外在音樂哲學領域的研究成果,而忽略了中國的國情與音樂傳承;不能知行合一,只在理論上下功夫,卻不去顧及音樂的具體活動和實踐。眾所周知,理論研究的目的,最終展示的是在實踐中的指導能力。音樂是一種頗具特色和影響力的實踐活動,具有極大的研究潛力。音樂哲學的研究,更需要從實踐出發,用實踐這一標準來評判自身的哲學觀,通過實踐的修正,進而指導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