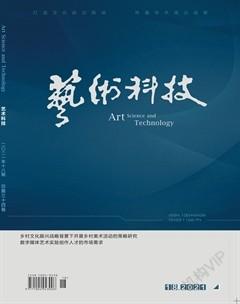美術作品署名權糾紛研究
摘要:作者享有的精神權利中,署名權至關重要。作者行使權利署名作品,不僅能帶給作者適宜的精神利益,還有利于作品本身價值的提升。一般情況下,作品有署名,尤其是有名家署名,與未署名作品相比會存在顯著的價格差異。而面對這一現象,部分逐利者難免會出現偽造他人簽名等違法行為,導致藝術品交易市場更為混亂,藝術品消費者也因此面臨巨大的交易安全風險。基于此,文章從署名權的法律意義出發,在分析美術作品署名權法律特征的基礎上,以案例的形式深入具體地研究美術作品的署名權糾紛,以供參考與借鑒。
關鍵詞:美術作品;署名權;糾紛
中圖分類號:D923.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18-0-03
美術作品指具有審美意義的立體或平面造型藝術作品,如書法、版畫、雕塑、水彩畫、中國畫、油畫及工藝美術等一系列作品。具備獨立法律意義的美術作品與其他藝術、文學及科學作品相同,皆屬于著作權法律關系客體,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的保護。在著作權法保護中,美術作品作者署名權是一項重要的內容,是雕塑家、書法家、畫家及工藝美術家享有的在自己的美術作品上署名的權利,用于表明自身美術作品作者身份,屬于著作人身權范疇。
1 署名權法律意義
首先,作者享有署名的權利。作為著作權主體之一的作者,享有署名美術作品的權利,所以署名權屬于排他性權利之一。作者享有署名權的同時,既有禁止他人署名自身美術作品的權利,也享有禁止他人在仿造自己的美術作品上署作者之名的權利,且享有使用自己美術作品的人對自身為作品作者明確的權利[1]。其次,作者享有不署名的權利。作者是否署名美術作品,也是其享有的一項權利,常見于版畫、壁畫、雕塑、工藝美術及宣傳畫等作品中。即便不署名,作者依舊享有作品的著作權,而非否認其為作品作者。當出現著作權糾紛時,作者依舊可借助各種途徑對作品著作權歸屬進行確認,如采取出版、獲獎、發表、公證、展覽或著作權登記等途徑。當有爭議發生時,也可從美術作品構圖、色彩、創作時間和地點、線條、流派、風格及師承等方面考證。短時間無法完成美術作品作者的確認時,其署名權依舊享有著作權法律保護。針對作品作者身份不明的情況,除署名權以外的著作權由作品原件擁有人行使,而在確定了作者身份后,著作權的行使則轉交給作者或其繼承人。最后,作者享有署真名或假名的權利,且享有屬別名、字、號等權利。我國文人墨客擁有遠比一般人更為復雜的名字,如字、號、別號等,其作品上的署名款也會有一定差別。同時,我國書畫署名中也有印章這一形式,署名款的組成也包含名號章、閑章等。閑章是除姓名、室名、字號及別號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是本人心跡意趣的表現,如鄭燮的“七品官耳”等,此類題款、鈐印個性特征突出,打造了我國書法作品特色鮮明的署名。
2 美術作品署名權法律特征
一方面,不得繼承或向他人轉交署名權,作者需要全權承擔作品傳播中形成的名利得失、藝術褒貶。另一方面,他人使用作品或是贈與、繼承、轉讓作品時,署名權不會發生變更,署名權不會因作品進入公有領域等而消亡。電視臺、錄音錄像制作者、出版者、表演者等在使用他人作品的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循相關的法律法規,禁止侵犯作者的修改權、署名權,要注重作品完整權保護這一權利的行使[2]。依法對作者作品合理使用的,有關報酬支付方面,即便沒有取得著作權人許可也可自行選擇取消,但必須明確作品名稱及作者姓名,同時要保護著作人相應權利。
針對美術作品原件和作品著作權的轉移,由于兩者有一定區別,因此不會被認定為轉移作者署名權。作者在世時,由作者本人負責對署名權進行保護;作者去世后,由其繼承人或受遺贈人負責保護署名權,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則是在作者無繼承人或沒有受遺贈人的情況下保護署名權。
對于美術作品而言,若是有侵權糾紛產生于署名權方面,當事人可向相應行政管理部門提交訴訟申請,或是前往人民法院進行民事訴訟。在訴訟中可供使用的證據包括著作權原件、底稿、著作權登記證書、取得權利的合同、合法出版物、公證機關出具的取證公證書、認證機構出具的證明、購買的侵權復制品實物等一系列物品。人民法院受理此類案件時,需以著作權法相關規定為根據,在不存在相反證據證明的情況下,視美術作品署名的法人或自然人等為享有著作權相關權益的人員[3]。若是因順序引起的美術作品署名糾紛,人民法院審理中遵循的是“有約定的依約定,否則以作品創作中付出的勞動、作者姓氏筆畫或作品排列等為依據進行署名順序的確定”這一原則。
3 美術作品署名權糾紛
3.1 合作作品署名權糾紛
以2008年李子成與葛懷圣侵害著作權糾紛案為例,盡管雙方當事人并非以美術作品為爭議標,然而討論該情形時仍然有參考價值。首先,原告、被告在民國版《壽光縣志》中共同參與了點校,并就此書達成合意,但雙方的合作因后續有分歧點被終止。被告在對共同點校之書再次反復點校后出版,出版時選擇的名義為個人[4]。但原告認為被告出版的一書中有95%與自己出版的校注本《壽光縣志》是相同的,僅有5%不同;在被告看來僅有85%是相同的,不同之處則達到15%。法院后續以被告當庭承認的85%相同、15%不同的事實為根據,給出了共同點校民國版《壽光縣志》屬于合作作品的判定,即該書部分著作權由當事人雙方享有。這樣看來,原告署名權也就受到了被告的侵害。
盡管被告在創作作品時是獨立進行的,原告未參與,但最終法院給出的認定結果依然是合作作品,由此可知,面對特殊的情形即“二次”創作時,有關合作作品的判斷方面,要結合原合作作者是否參與新作品創作、比較“二次”創作作品與原作品間的相似性等一系列因素,若僅選擇其中一項進行判定必然不妥[5]。倘若兩者有著相似的構成實質性,此時應以合作作品來認定“二次”創作的作品,不論新作品創作中原合作作者參與與否,“二次”創作者都需要將原合作作者姓名署在作品上,否則可判定為侵犯署名權。
3.2 復制品署名權糾紛
在分析復制品署名權侵權時,引入了喻繼高(原告)與厲建華(被告)一案。在該案中,原告發現有八幅假冒其署名的贗品畫掛在兩漢畫廊網站中銷售宣傳,甚至有的作品根本不是自己的。法院受理此案后,判定被告移除涉案畫作圖片,且在判決生效日起3日內執行,這也表明了法院對被告侵犯原告作者署名權的肯定。但是,審理法院針對侵犯署名權的具體作品卻沒有明確。被告將原告姓名署在原告從未畫過的五幅作品中,這一行為是典型的“冒名”行為。筆者認為,從性質上來看,該行為應確定為侵犯姓名權行為,但也不會對以《著作權法》相關規定為根據對被告提出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請求造成阻礙。
同時,若被告對原告既有作品進行了偽造,則需要明確此類作品是否對署名權構成了侵犯。此處引入劉世江訴豪獅畫廊侵犯其作品署名權、復制權的案件,原告認為被告在沒有獲取自身許可的情況下,復制作品《追風》,署名“趙雯”并銷售。法院判定被告在銷售涉案畫作時,在復制原告作品的同時署名案外人,將原告與其作品間的聯系割裂,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權[6]。該案中雖然被告沒有假冒原告姓名,但卻將案外人名字署在涉案作品中。我國《民法典》中明確規定,他人偽造原作者未繪畫的作品并署名作者名字的行為是在假冒、盜用原作者名字;他人偽造原作者作品并附上原作者姓名的簽署時,因原作者沒有參與復制品的創作,所以同樣可判定為假冒、盜用,對原作者姓名構成了侵犯的行為。
3.3 法人意志解讀署名權糾紛
在分析該糾紛時,引入張曉寧(原告)與三色鳥公司(被告,武漢三色鳥創意設計有限公司)一案。原告擔任被告內部設計總監一職務,雙方就勞動事宜簽訂了相應的合同。被告接受了某個包含IP人物形象的外部委托設計,該項目隸屬藝術甚至是美術作品范疇,該項目交由原告及其所在的團隊負責。在完成項目的設計后,項目中沒有原告的署名,被告以公司名義參與了外部設計大賽且最終獲取了銀獎。法院認為,因是被告與案外第三方簽訂合同承接的訴爭作品,包含原告在內的設計團隊雖然參與了設計工作,但其是為被告工作的,以被告及案外第三方要求為根據開展設計,被告享有決定或否決設計團隊個人創作作品內容的權利,當公司最終決定作出后,員工個人意識會向代表單位意志轉變,同時需承擔的有關訴爭作品的責任也轉移至單位。所以該案例中的訴爭作品判定為法人作品,被告享有作品的著作權[7]。換言之,法院認為該案例原告是以被告要求為根據開展的一系列工作,原告是否創作了滿足要求的作品,其最終決定權是由被告負責行使的,當被告作出最終決定后,即向單位意志的代表轉變,體現了法人意志。另有一案,被告為原告提供了照片、物質方面的幫助,原告則負責塑造第十世班禪大師泥頭像。在作品創作過程中,被告前后6次要求修改五官特征,原告也酌情進行了修改。在塑造完成后,雙方簽訂了銀質頭像鑄造合同。一審、二審判定,原告以被告意志進行創作構思,由于被告意志在作品的觀點、思想及內容方面得到體現,因此作品所有責任承擔人為被告。同時,因該作品關聯宗教領袖,具備特定人身性質,所以將其判定為被告享有著作權的法人作品。雖然在委托創作方面雙方簽訂了契約,被告在物質條件及修改建議方面也提供了幫助,但這是否就證明是被告意志(法人意志)的反映,能否判定該作品為法人作品呢?
上述兩個案例中,法院在判斷有無法人意志的體現時沒有采用統一的標準,基本可采取兩種意見進行歸納:一是法人是否提出主題或原則性要求,且錄用的最終決定權是否由法人行使,這是對法人作品進行區分的一個關鍵因素;二是在具體判斷中,除了沿用法人主題或原則性要求及最終決定權等標準外,也需要將法人為創作者預留的自由思維空間、創作表達方式等因素納入考慮范疇。筆者認為,在判定涉案作品是否為法人作品時,需要統籌考慮最終決定權、原則性要求等因素,不得僅選擇其中一項或多項因素進行判定。
3.4 法人作品創作者署名糾紛
分析該糾紛時,引入李慧卿(原告)與陳文燦(被告)的案例。原告向法院提起訴訟,稱其是《武夷之春》(吳景希)法定繼承人,但被告擅自將該作品著作權登記在個人名下,侵害了作品署名權。一審法院給出法人作品的判定,認為以法人作品認定訴爭作品不代表參與實際創作的人員不能將自己的身份表明在作品上。反之,法人允許參與實際創作的人員在表明身份時采取署名的方式,這在公民參與創作的積極性方面發揮了一定的鼓勵和保護作用,同時在實現立法著作權的目的方面也產生了相應的作用。出版物方面,法人將相關參與人員(如創作者等)名字主動署在作品上,可認定是公開認可作品中上述參與創作及署名的人員,該行為從某個角度來看即認可了上述人員署名權,參與人員雖然獲取了署名權方面的認可,但是法人享有的著作權卻不會受到絲毫影響[8]。然而,根據當時的著作權法制度來看,該判斷無疑對其構成了沖擊。在給出認可法人作品的判定后,法人享有著作權相關的完整權利,那么享有署名權的人員中為什么會包括參與人員?在有關該問題的研究方面,筆者認為關鍵在于考察“署名權”的法律性質。法律制度中認定作者為法人或非法人組織且享有一定的著作權權利,旨在為法人合法利益提供有效保護,否則必然不會判定為法人作品,這也表明了不可能出現創作者、非法人組織或法人等一同具備作品著作權權利的情形。同時,著作權轉讓人身權并未受我國《著作權法》的認可,獲取署名權的非法人組織或法人,向他人轉讓的行為是不被認可的,因此《武夷之春》一案中,從性質方面來看,不得選擇承認或轉讓署名權來認定法人署名其他參與人員的行為。
4 結語
署名權是表明作者自身身份的重要權利之一,該權利密切關系作者的身份利益和財產利益,同時還會影響作者作為自然人享有的人格利益。作者在署名權的行使下,能將其作者身份公示給世人,同時享有作為作者的相關權利,這也從法律方面賦予了作者真正的意義。我國目前有關美術作品署名權的相關研究及司法雖存在一系列不足,但在愈加頻繁的藝術品交易及不斷擴大的相關市場這一背景下,必然會逐步形成更為完善的法律規定,為美術作品的作者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障,避免其利益受損。
參考文獻:
[1] 江武建,范大平.淺談學生臨摹美術作品侵權的法律問題[J].全國商情(理論研究),2011(4):93-94.
[2] 唐艷.論特定美術作品原件所有權與著作權的沖突與協調[J].電子知識產權,2020(8):76-88.
[3] 王遷.論平面美術作品著作權的保護范圍:從“形象”與“圖形”的區分視角[J].法學,2020(4):154-165.
[4] 趙書波.以交易促保護:對民間美術作品版權問題的思考[J].美術觀察,2018(2):27-28.
[5] 柏洪.如何認定美術作品的“抄襲”?[J].藝術市場,2018(11):63-65.
[6] 袁博.拆毀公共場所美術作品侵犯著作權嗎[J].法人,2018(1):92.
[7] 陶鑫良.論“署名權”應改為“保護作者身份權”[J].知識產權,2020(5):15-21.
[8] 張鴻霞.法人作品中參加人署名權保護研究[J].學術界,2016(3):76-83.
作者簡介:黃慶聰(1996—),男,江蘇南京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經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