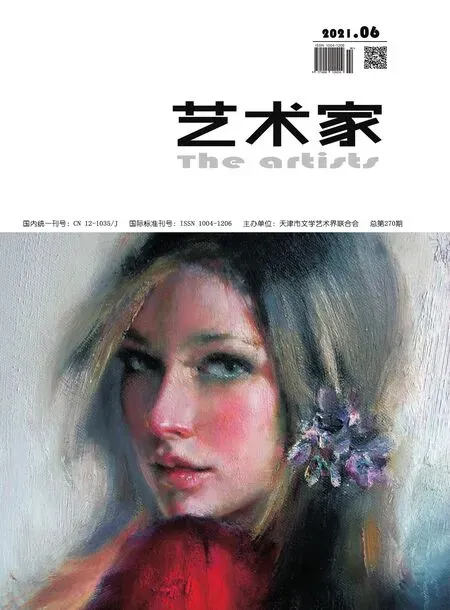秦安小曲戲《梁山伯與祝英臺》的藝術特點
□王 芳 甘肅省秦安縣文化館
一、秦安小曲戲《梁祝》簡介
(一)秦安小曲
秦安小曲為國家級非遺項目,起源于唐代,興盛于明清,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它吸收了民歌的精華,如《割韭菜》等曲牌;也經過了官宦、文人的加工,他們見多識廣,欣賞過其他地方的曲藝,所以秦安小曲又有江南韻味、昆腔之美。明代嘉靖時期的翰林、山東巡撫胡纘宗、清代乾隆時期的翰林張位、張位之子翰林張思誠都參與過秦安小曲的創(chuàng)作,極大地提升了秦安小曲的文化品位。在民間藝人與文人的共同參與下,這種曲調悠揚婉轉的小曲不斷發(fā)展,流傳至今。目前秦安縣形成了以秦安縣文化館秦安小曲研究所為中心,以16家位于鄉(xiāng)鎮(zhèn)的秦安小曲傳習所為節(jié)點,點、線面相結合的非遺傳承傳播體系[1]。
(二)移植改編
《梁山伯與祝英臺》是中國古代四大傳說之一。越劇《梁祝》通過電影的呈現(xiàn)而為廣大觀眾所熟知。后來,何占豪、陳鋼創(chuàng)作的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祝》充分參考和借鑒了原有的戲曲音樂的曲調,保留精髓,推陳出新,成為獨具東方韻味的一部曲子。
將一部戲曲改編為本是曲藝的劇目本身就有一定的難度。曲藝主要以說唱為主,演奏者、演唱者站立或者端坐,秦安小曲也不例外,也有帶著秧歌舞步進行曲伴舞的,如郭嘉鎮(zhèn)胥堡村一帶流行的小曲社火。另外,省級非遺秦安蠟花舞的伴奏音樂也是秦安小曲。戲曲是一門綜合藝術,靠演員用“唱、念、做、打”和“手、眼、神、法、步”最基本的“四功”“五法”來塑造人物形象,再通過表演來感染觀眾。而觀眾則通過視覺和聽覺來直接感受那“三五人便千軍萬馬,一席地乃萬水千山”的舞臺效果[2]。
甘肅各地流行著“曲子戲”,表演時不拘場合,較為自由,是曲子在演出中的一種延展,是曲藝和戲曲之間的一種過渡形式。傳統(tǒng)的秦安小曲中也有曲子戲,但數(shù)量不多。在《梁祝》之前,秦安縣尚未編排過全本的秦安小曲大戲。
要想將一部家喻戶曉的劇目移植改編為本地獨有的劇種,既是挑戰(zhàn)又是機遇。1979——1980年,經過秦安縣秦劇團王鵬舉等老師的努力,越劇《梁祝》最終被改編為秦安小曲戲,成功搬上了舞臺。當時,主要演員每人都抄寫了一本道白和唱詞,而樂隊則用油印的曲譜。到現(xiàn)在,手抄戲本、曲譜仍保存完好,有錄音、錄像資料,是珍貴的非遺檔案[3]。
(三)秦安小曲戲《梁祝》的演出
本劇初演時的主要演職人員包括,劇本整理:劉國柱,作曲:王鵬舉,演員扮演者:(祝英臺)王芳、曹漪;(梁山伯)王鳳玲、張玉梅。
此劇在當年得到了甘肅省文化廳、天水市文化局各級文化主管部門的肯定,其作為國慶三十周年獻禮劇目,參加了天水地區(qū)調演,在天水市中心廣場的紅旗劇院(已拆)演出時,盛況空前,獲得了廣大觀眾的一致好評和專家的認可,還上了《甘肅日報》頭版頭條。甘肅省電視臺、甘肅人民廣播電臺多次錄像錄音,遠播海內外,1985年以后,演出逐漸減少。近年來,由于原有的人員陸續(xù)調離、退休,該劇已不再演出,急需搶救式記錄、整理,并重新搬上舞臺。
二、唱詞及曲牌的藝術特點
(一)唱詞的文學性
全劇共有18幕,結構緊密。作為移植劇,改編者保留了部分越劇的戲詞,又增添了一些秦腔常用的戲曲詞匯及韻腳;在唱詞中基本上除去了秦安的方言詞匯;念白則采用秦腔的念白。在唱詞中,該劇還采用了駢散結合、復沓、比興等多種句式和修辭手法。這樣就使本劇打破了地域局限性,能讓更多的外地觀眾欣賞。
(二)曲牌的應用
創(chuàng)作者在移植改編的過程中選取了秦安小曲已有的曲牌,唱詞內容與音調恰當貼切,使整部戲能夠呈現(xiàn)出秦安的地方特色和秦安小曲的獨特魅力。如第一場祝英臺用的調式是《馬頭調》,馬頭調比較抒情、緩慢,主人翁在慢慢訴說著她的心事。
第三場祝英臺女扮男妝后,幕后一句高亢響亮的,“從此不是籠中鳥”,用的調式叫《珍珠倒卷簾》。這個調子比較輕盈、歡快。此刻用這個調子反映了祝英臺離開閨房,出外求學,脫離牢籠后的歡欣雀躍。
在《樓臺會》一場中,當梁山伯興沖沖來到祝英臺家,要與朝思暮想的人相會。祝英臺上場唱道:“聽說山伯來到家下,好姻緣竟成了水月鏡花,無奈何上前去含淚問話。”這個曲牌為《進蘭方》,此曲調比較抒情、緩慢,它在高興的情節(jié)可以表達歡快,在憂愁的情節(jié)中可以唱苦音,兩種情節(jié)都能淋漓盡致地表達人物的內心世界。接下來的段唱,使用的曲牌叫《混江龍》。這個曲調一般是表現(xiàn)主人翁在對話或者生氣時吵架的情形,有時候表現(xiàn)比較激昂、熱烈的一種情節(jié)。“梁兄一旁喜欲狂,哪知我愁苦心內藏,欲將實言對他講,只恐愁煞少年郎。”接下來,祝英臺又唱了一個《瓊竹調》。《瓊竹調》和《馬頭調》有點類似,都比較抒情、緩慢,給人一種娓娓道來的感覺。
(三)音樂的特點
秦安小曲的音樂曲調悠揚婉轉、溫和細雅,含有元曲的音樂元素和風格,在表現(xiàn)愛情戲方面有獨特的韻味。主創(chuàng)者遵循地方語言的特點,選取了秦安小曲已有的曲牌,采用了拉伸、緊縮、音色變化、潤腔、歸韻等手法,使整體節(jié)奏連貫、緊湊、回環(huán),結構閉合,既保留了基本調式和韻味,又跳出了已有的窠臼,從而賦予曲牌新的生命。
三、人物塑造
《梁祝》的主角有兩位,即梁山伯與祝英臺,其中祝英臺的戲份更多些。在《送別》中,梁山伯的形象是憨厚、木訥的,盡管祝英臺多次暗示,可是他自始至終沒有識破祝英臺是女孩子這個秘密。
本劇表演者對祝英臺人物性格的把握恰到好處,感人至深,令人難忘。中國古代戲曲塑造了許多女子形象,諸如歸漢的蔡文姬、帶枷的玉堂春、驚夢的杜十娘、葬花的林黛玉、掛帥的穆桂英、替父從軍的花木蘭。在文學作品及民間傳說中,祝英臺是個大家閨秀,她知書達理,忠于愛情,為人稱道;而展現(xiàn)在舞臺上的祝英臺形象栩栩如生,她粉面含春、光彩照人,她的美貌、忠貞、聰慧一次次感染了觀眾。
在第三場女扮男裝的表演中,先是幕后一句高亢嘹亮的“從此不是籠中鳥”,只見演員背身上場后以扇半遮面而亮相,眼睛左右一看,意思是我像少年嗎?這時,觀眾也會意地看到了一位俊秀儒雅的少年書生。接下來唱“展開雙翅沖云霄”時,只見演員一提袍襟跑了個小圓場,手中的扇子上下舞動,眉飛色舞,使觀眾看到和感受到了一個英俊灑脫的少年,在脫離牢籠后,投身大自然懷抱的情不自禁和喜悅之情。
《樓臺會》表現(xiàn)的是祝英臺那柔腸寸斷的復雜情感,如泣如訴的哀婉唱腔,讓人覺得凄涼、悲痛。梁祝同窗三載,情深意長。臨別時,英臺私下將家中“小九妹”許給山伯,并拜托師母做媒。她想,山伯知情后定會來她家赴約,他們也將永結同心。然而,回到家后,父親卻強逼她與紈绔子弟馬文才成婚,祝英臺真是萬般無奈。恰恰這時,山伯得到師母告知后萬分喜悅,興沖沖來到了英臺家相會。這時,祝英臺上場,一身淡雅女裝打扮,唱道:“聽說山伯來到家下,好姻緣竟成了水月鏡花,無奈何上前去含淚問話。”此時此刻,日夜思念的心上人來赴約,祝英臺將如何面對?真是想見又怕見啊!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先生說:“戲劇身段是造型化,是經過藝術家提煉,再經過美學家過濾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時,只見演員用似乎是散架的身段、沉重的腳步、下拖的水袖、欲進又退的行動、凄楚繾綣的面部表情,來刻畫滿腹愁思的祝英臺的形象。隨著劇情漸入高潮,矛盾明朗化,演員表演更加張弛自如,恰到好處地表現(xiàn)了此時此刻的人物性格。
就《樓臺會》這場戲開始的劇情而言,女方清醒,明知自己已許配他人;而男方則不知實情,還一腔熱情,滿心歡喜。正是這樣一明一暗的戲劇沖突才造就了全場的吸引力與推動力。這時,女方則早知將勞燕分飛、一離永別。她此刻既與梁兄難以割舍,然而,面對殘酷的現(xiàn)實,又無能為力。她雖然內心傷痛,明知此事說破對梁兄是晴天霹靂,而又不得不說,這種矛盾重重的心理,使她欲罷不能,欲說不忍。她唱道:“梁兄一旁喜欲狂,哪知我愁苦心內藏,欲將實言對他講,只恐愁煞少年郎。”兒女情深,萬般無奈之下,英臺只能表白心跡,唱道:“請兄原諒休見罪,保重身體莫傷悲,小妹我心如鐵石情不背,夢魂之中也相隨。”
當一對淚人互訴衷腸,絕望地表明心跡后,山伯悲傷離去。這時,英臺的父親叫丫鬟替小姐更衣,英臺仿佛如夢初醒。當聽到父親再次催促女兒趕快梳妝,馬家花轎將到時,只見演員沒有說話,只用了一個水袖動作,將水袖拋出,隨后雙手又將水袖纏繞回來,再猛地打出去,打向她的父親,轉身離去。這一拋、一繞、一打、一轉,詮釋了一個弱女子對封建禮教的控訴與反抗。
結語
魯迅先生說過:“悲劇是把人間最美好的東西撕破了給人看。”只有這樣,才能更進一步渲染悲涼的氣氛,同時,也與結尾化蝶相得益彰,升華了主題。本文從移植改編、唱詞、曲牌、人物塑造等多個方面剖析、總結了秦安小曲戲《梁祝》的藝術特點。筆者相信,秦安小曲這一在久遠文明和豐厚文化積淀下形成的民間藝術將會一代代傳承下去,在教化民眾、構建和諧社會方面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