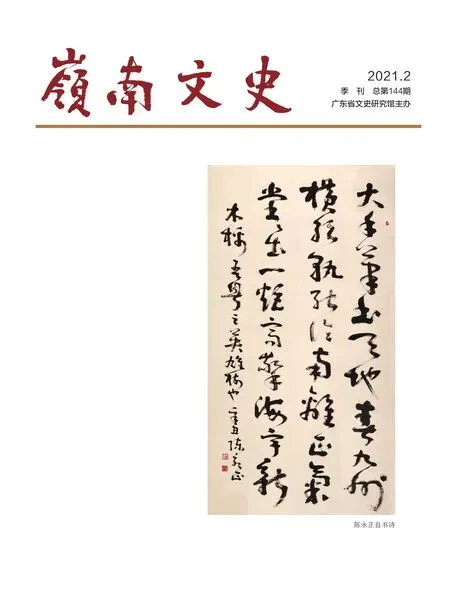湛若水已佚《修復古易經傳訓測》的體系復原與遺文分析
張金蘭 程 潮
湛若水是明代的經學大家,在中國古代經學史上開辟了“以測解經”的新經學。但因他帶“測”的經學著作與正統經學相沖突,故得不到朝廷授命刊行,甚至受到官方打壓,以致除《二禮經傳測》外,其余都在近代之前失傳了。經過對現存明清資料的爬梳剔抉,找回了已佚的《古易訓測》《四書訓測》的遺文。本文擬對湛氏《修復古易經傳訓測》的體系結構進行復原,并對現存遺文進行整合和說明。
一、《修復古易經傳訓測》的著述動因
《修復古易經傳訓測》,又有《古易訓測》《古易經傳》《古易經傳測》《周易訓測》等簡稱。從書名上看,湛若水是帶著崇尚“古易”、憂心“古易”的心態和修復“古易”的使命寫這部書的。他所理解的“古易”是由“一經十傳”構成的。“一經”是指由伏羲之“卦畫”、周文王之“彖辭”和周公之“爻辭”所構成的“全經”。[1]所謂“十傳”,是指孔子所作的《十翼》,合稱《易傳》。
湛氏認為,孔子為“經”作“傳”之時,必取“經自為經”,故不將自為的“十篇”之“傳”分附于“經”中。[2]他既反對將孔子之“傳”當作“經”,主張“古易只伏羲、文王卦畫、彖爻辭為經,孔子十翼為傳”;[3]也反對“分傳附經”,經傳相混,主張“經自為經,傳自為傳”,經傳相分,故將“分傳附經”視為“漢儒支離附會之陋”。[4]到底誰是“分傳附經”的始作俑者呢?楊時喬言“自費氏分傳附經”,[5]黃居中言“至鄭康成分傳附經”,[6]胡培翚言“分傳附經始于輔嗣”。[7]而湛氏稱“自孔子之后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焉”,[8]顯然是視鄭玄為始作俑者,而把費氏當作“以傳解經”的代表。
其實,湛氏作《古易訓測》,主要不是針對漢儒易學,而是針對宋明主流易學的弊端而發的。他說:“夫十傳所以解經者也,后之儒者乃于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乎?”[9]這里指出后儒解《易》的三個弊端:一是分傳附經。王弼承鄭玄,程頤又承王弼,故后世有“王弼乃以傳附經,而程子從之”[10]之說。二是繁疏博釋。無論是程頤的《伊川易傳》,還是朱熹的《周易本義》,都對“經”中的“畫”“彖辭”“象辭”“爻辭”作繁博的疏解。三是傳外立傳。湛氏弟子黃省曾認為,孔子的《易傳》已將“經”闡釋得“至矣盡矣”,但“后之儒,復于經而有傳,是與仲尼爭衡也;且后儒之傳,外仲尼之旨為之說者謂之誣,竊仲尼之旨為之說者謂之綴”。[11]這里雖未明指程頤,但《伊川易傳》正好可以“對號入座”。至明代,以程頤為代表的易學模式得到官方的提倡而甚為顯盛。明洪武初,頒《五經》于天下,《易》兼用程《傳》、朱《義》;永樂中,胡廣等撰《周易大全》,“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傳》之后”。[12]成化時,成矩依程《傳》模式將朱熹的《周易本義》由經傳相分的十二卷原本改成經傳相混的四卷本。[13]故黃氏說:“今之為《易》,次附汨紊,又非朱氏之舊矣。(湛)先生恐《古易》之軌躅終泯也,乃因門人葛澗氏之請,起而正之。”[14]這就道出了湛氏著《古易訓測》的直接動因。
二、《修復古易經傳訓測》的體系復原
在宋明時期曾誕生以呂大防、呂祖謙、朱熹、吳澄為代表的“古易”派。呂大防《周易古經》的結構是: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系辭上第七、系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15]此說后為呂祖謙、朱熹所沿襲,只是呂的《古周易》首為“上經”“下經”,朱的《周易本義》首為“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二書其后篇次均為“彖上傳第一”至“雜卦傳第十”。吳澄的《易纂言》以“卷”替“第”并在《十傳》各篇尾加“傳”字,構成“卷一上經第一”“卷二下經第二”“卷三彖上傳”……“卷十二雜卦傳”的結構。湛氏又沿用朱、吳的古易學模式,“出羲、文、周公之《易》,復為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為后人所分附者,復合而為《十傳》”。[16]而在宋咸淳元年(1265)吳革所刋的十二卷本《原本周易本義》中,加上“卷末”的《五贊》和《筮儀》二篇;湛書受此書的啟發,卷末也有《二十三贊》。[17]吳氏《易纂言》的《卷首》闡釋了《連山》和《歸藏》,湛氏也有“夏之《連山》”[18]之說,可能取法吳氏而為“卷首”語的一部分。吳氏將《系辭傳》中說上、下經的“十六卦十八爻之文”定為“錯簡”,移置于《文言傳》中。[19]湛氏也將《系辭》“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重予厘正,復歸《文言傳》之后。[20]清康熙年間,姜丹書在《學易筌蹄》書中“從明湛若水說”,而將原《文言》“元者善之長”以下八節及原《系辭》中“鳴鶴在陰”七節(即“鳴鶴……慎乎”“同人……如蘭”“初六……失矣”“勞謙……者也”“亢龍……悔也”“不出……出也”和“子曰……招也”)、“易曰自天佑之”一節(即“易曰……利也”)、“憧憧往來”十一節(即“易曰……盛也”“易曰……見耶”“易曰……者也”“子曰……謂也”“善不……耳兇”“子曰……苞桑”“子曰……任也”“子曰……之望”“子曰……元吉”“天地……一也”和“子曰……恒兇”)編為《文言外傳》。[21]翟均廉(約1736-1805)在《周易章句證異》卷七和卷八中引《系辭》上、下傳原文時,就有18處標注“湛若水作文言”“湛若水曰(或云)是文言”等語。若將湛氏從《系辭》中移至《文言傳》的“十九篇”與吳澄的《文言傳》文相對照,與姜丹書、翟均廉的說法相印證,就可斷定湛氏《文言傳》的內容直接取自吳氏《文言傳》,只是節序有所不同。
綜上所述,可以推斷《古易訓測》十卷的體系結構及篇次大致如下:吏部尚書湛公古易經傳訓測序(黃省曾);修復古易經傳訓測序(湛若水);卷首(包括釋“連山”“歸藏”);上經;下經;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系辭上傳;系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二十三贊。
三、《修復古易經傳訓測》的遺文整合
《古易訓測》的遺文,除“自序”來自湛氏的《文集》外,其他都是我們在明清其他易學著作中搜尋出來的。本文所收集的遺文,除湛氏自序和黃省曾序不錄入外,其余按照該書的體系結構整合為八個部分,20條(用帶圈數字編序)。每條先引《周易》原文(因通行本都可找到,故長原文中間省略),后引湛氏的“訓”文(有原文,有間接引文)和“測”文,并都打上標點。
(一)《卷首》
(1)連山易。湛若水曰:“夏之連山,知止者,始終之要,程子所以取艮卦也。”(引自朱彝尊:《經義考》卷二;參閱湛氏弟子蔡汝楠之說:“夏之連山,知止者,始終之要,程子之所以取艮卦。商之歸藏,翕聚者,開泰之本,孔子之所以取坤乾。”[22])
(二)《彖下傳》
(2)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止而巽,動不窮也。(下經,《漸》)
湛子謂“二以柔順居中,以上承陽”。(引自熊過:《周易象旨決錄》卷四)
(三)《象上傳》
(3)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上經,《蒙》)
湛甘泉曰:“治蒙之初,非用教刑,則無以儆其惰、破其愚,所以然者,使蒙不至于終蒙,終蒙則過惡之甚,至受桎梏之刑矣。故初之用刑,用以脫其桎梏之罪也。兩‘用’字有著落。”(引自查慎行:《周易玩辭集解》卷二)
(4)初六:……象曰:乾父之蠱,意承考也。……象曰:乾母之蠱,得中道也。……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上經,《蠱》)
諸爻取父母之象,李(鼎祚)、吳(幼清)、湛子(若水)嘗有說矣,有未暢者……”(引自熊過:《周易象旨決錄》卷二)
(5)六二:窺觀利女貞。象曰:窺觀女貞,亦可丑也。(上經,《觀》)
湛源(原)明曰:“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以君子之人,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九五陽剛中正之道,但覘視朝美一班于形似之粗,如女子之窺觀也。丈夫而效女子之見,不亦丑乎!”(引自程汝繼:《周易宗義》卷三;參閱潘士藻:《讀易述》卷四)
(6)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上經,《無妄》)
湛原明曰:“天為純陽,雷者陽之動,陽動而萬物發生。勾者萌,甲者拆,蟄者驚,蔵者發。洪纖高下,物各付物,而天不與焉。不與焉者,動以天也。動以天者,無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圣人體無妄之道也。茂,盛也。動以天,故盛也。因其時而施,因其物而付,圣人無與于時與物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圣人所以體天而無妄者也。”(引自潘士藻:《讀易述》卷五;參閱錢澄之《田間易學》卷三)
(7)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經,《大畜》)
湛原明曰:“治己治人,其道一也。”(引自潘士藻:《讀易述》卷五)
(四)《象下傳》
(8)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下經,《恒》)
湛原明曰:“君子何以立不易方也?所以體恒也。知雷風相隨,亙古不變之象,而自立于大中至正之矩,為可久不變之道也。何以為易也?變也。何以為方也?所恒也。時變而所恒不變也,何也?剛柔之上下,陰陽之升降,日月之代明,寒暑之往來,極古今之變,而不能易其常也。不知者以經權常變二之以為對,豈知道者也。”(引自潘士藻:《讀易述》卷六)
(9)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下經,《遁》)
湛原明曰:“天下有山,主天而言也。主天而言之者,主陽而言之也。陽止陰于下,而脫然高上,不為所凌之義,遁之象也。不惡也者,無大聲厲色,以絕彼之跡也。嚴也者,莊敬自持,以消彼之邪也。無有作惡,而嚴以自守,乃君子之常,非以遠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彼雖上凌而迫之,而邈其不相及矣。此之為君子之遁也。夫遁者,早見而先機也。二陰方長,未至于盛,故可遠,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引自潘士藻:《讀易述》卷六;參閱程汝繼:《周易宗義》卷五,汪邦柱:《周易會通》卷五)。
(10)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下經,《家人》)
湛氏作嗃嗃,嚴厲之聲。(引自章潢:《周易象義》卷三)
(11)上六:無號,終有兇。象曰:無號之兇,終不可長也。(下經,《夬》)
湛原明曰:“何以為終?不可長也。當夬之終,不可使一陰之復長也。陽盛而陰將盡,豈能有復長之理?圣人于夬終,為之戒慎,終保治之道也。”(引自潘士藻:《讀易述》卷七)
(12)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無禽,時舍也。(下經,《井》)
湛甘泉以禽為井欄。(引自黃正憲:《易象管窺》卷九,參閱趙振芳:《易原》卷六)
(13)六四:井甃,無咎。象曰:井甃無咎,修井也。(下經,《井》)
湛甘泉曰:“甃者,砌之也。四柔順得正,以順承九五剛中之君。交修其德,如修井然。井修則水之用不窮,德修則澤之流不竭,此大臣輔弼之道也。茍不務此,而汲汲焉思以勺水濟天下,惠而不知為政,人人而濟之,日亦不足矣。”(引自黃正憲:《易象管窺》卷九)
(14)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下經,《渙》)
原明曰:“六質柔而履初剛,履剛者,乘壯馬也。又,馬少則壯,老則弱。初,所以為壯馬也。又,初為渙之始,始渙而拯之則有力,亦壯馬也。救之不早,不力也,救之早,則為力也易,此初六柔順從陽之道也。若以二有剛中之徳為壯馬,然人乘馬上,而二反在前,非象旨矣。”(引自潘士藻:《讀易述》卷十;參閱張次仲:《周易玩辭困學記》巻十二,汪璲:《讀易質疑》卷十六)
(五)《系辭上傳》
(15)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湛子曰:“理一而已,易簡非二體,久大非二功,德業非二事,蘇氏所謂隱顯之別也。此乾坤之辨也,不可不知也。”(引自潘士藻:《讀易述》卷十一;參閱程汝繼:《周易宗義》卷九,熊過:《周易象旨決錄》卷五)
(16)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徳。
湛子因曰:“陰陽交迭升降,合日月往來代明。”(引自潘士藻:《讀易述》卷十一;參閱熊過:《周易象旨決錄》卷五)
(六)《系辭下傳》
(17)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湛原明曰:“天地日月無不一,故止言乎貞。有不一而侈言一,故以一言乎人也。天地日月人,其理一也。”(引自潘士藻:《讀易述》卷十三)
(18)天地之大徳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財,古與材通,湛原明指為卦材。(引自潘士藻:《讀易述》卷十三;參閱方孔照:《周易時論合編》卷十一,熊過:《周易象旨決錄》卷六)
(七)《文言傳》
(19)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湛元明謂:“陰陽剛柔,器也,得其中正者,道也。”(引自查慎行:《周易玩辭集解》卷一)
(八)《序卦傳》
(20)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通篇)
甘泉湛子曰:“《序卦》者,君子之讀《易》至此而有感焉,《易》既成而象之者也。是故其言序者,順其指,達其辭,枝而牽,其圣人之疑乎!”(引自熊過:《周易象旨決錄》卷七)
四、《修復古易經傳訓測》的遺文說明
(一)判斷是否湛氏遺文的根據
其一,確認在湛氏現存論著中沒有與別人所引原文完全相同的文字。湛氏的易學思想,并非僅存于《修復古易經傳訓測》中,現存的《文集》(包括32卷本、35卷本、40卷本、85卷本、33卷續編本)和《圣學格物通》等論著也有所闡發。若在湛氏現存論著中沒有出現與別人所引原文完全相同的文字,就可推斷所引遺文可能出自《古易訓測》。若湛氏現存論著中也出現與別人所引原文完全相同的文字,就要看這段文字的上文是否有相應的《周易》原文。如第19條遺文雖然也出現在湛氏的《樵語》(《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一,黃楷刻本)中,但在查慎行的《周易玩辭集解》中是用來解讀《文言》“大哉乾乎!……天下平也”這段話的,符合湛氏的“原文—訓測”格式,故應為《古易訓測》的原文。
其二,確認引用湛氏原文的著作中哪些文字屬于湛氏遺文。現存的湛氏遺文,多是引用者在解讀《周易》的同一原文時,將它與多家解文作比較之用的。如取自熊過《周易象旨決錄》的第20條遺文,是根據熊氏將它與“文中子贊:‘易至序卦……可與幾矣’”“張文饒云:‘序卦上經……末牽繞也’”和“俞氏曰:‘序卦者……故在下’”三家之說相對照而推知的。因為王通、張文饒、俞琰解讀《序卦傳》的文字都是三人著作的原文,則湛氏所“曰”也應是《古易訓測》的原文。但有些引用者在引他人的解文時又作點評,只有找出所引解文的出處,才能區分出解文與評文。如取自潘士藻《讀易述》的第16條遺文,是依據潘氏引荀爽和蘇軾的訓文時,其后都各有一段文字不見于《荀爽易言》和《東坡易傳》而推知的。故將潘氏之文標點為:“荀爽曰:‘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深居,馮氏止以復臨明之。湛子因曰:‘陰陽交迭升降,合日月往來代明’,恐與變通義復也。蘇氏曰:‘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陰陽之義,至徳得其易簡之善。’明乾坤非專以為天地也。”又如取自熊過《周易象旨決錄》的第2條遺文,是根據“若……,則……”的語法規則推知的,即將熊氏之文標點為:“若湛子謂‘二以柔順居中,以上承陽’,則于‘進’義不明”。
(二)遺文可以佐證各卷有無“訓測”
“訓”是對字詞句的意義的字面解釋;“測”是對段篇章的意旨的深度推測。根據黃氏的分析,湛氏對《古易經傳》的“訓測”,僅指“訓說仲尼之翼言而彰測其蘊”,而不敢對“經”及其“彖、象”作訓測。[23]湛氏本人說:“于孔子十傳則稍出愚見,因言求象而各為之測;于之經,則全本文,第令葛生等采測義作旁釋,而不為之說,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經。”[24]黃氏也說:“(湛)不敢訓測夫經,……在《翼》下,暢而發之,又為大測,二十三贊以畢。”[25]即是說,“訓測”的范圍僅限于孔子之“十翼”,而對《周易》之“經”(包括“彖”“象”)只能作“旁釋”。從現存遺文看,也很少有《上經》《下經》的經文訓測,只有《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系辭上傳》《系辭下傳》《文言傳》《序卦傳》的傳文訓測。而“訓”與“測”的形式在湛氏現存的《二禮經傳測》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也給人們如何理解《古易訓測》中的“訓測”提供了指引。
(三)遺文反映出湛氏易學獨特的學術價值
從上面20條遺文看,其中對“禽”“甃”“財”“嗃嗃”“陰陽之義配日月”等字、詞、句義的解釋屬于“訓”;而其他段落文字基本屬于“測”。這些引自別人著作中的“訓測”,多是以與他人對《周易》原文的解讀觀點相對照的形式出現的,只有少數是單獨介紹湛氏的訓測觀點,反映了引用者或介紹者對湛氏訓測觀點的重視,也反映了湛氏訓測觀點的獨特性或獨創性,能夠成一家之言。
其一,“訓”的學術價值。如第12條中“舊井無禽”的“禽”字,多作“禽鳥”解,而湛氏訓“禽”為“井欄”。第18條中“何以聚人曰財”的“財”字,多作“資財”解,而湛氏訓“財”為“卦材”,熊過認此解為“是”。而這兩個概念的解釋,可謂別出心裁,且使文意的邏輯更為順暢。
其二,“測”的學術價值。遺文之“測”,一是對篇名總義之測。如第1條對《連山》(還應有《歸藏》)總義之測,第20條對《序卦》總義之測。二是對《十翼》文義之測。湛氏通過對“十翼”的文義作測,表達他的本體論、道德論、政治論等觀點。如第2條反映女性順從男性的道理;第3條揭示“教”與“刑”在“治蒙”中的不同功能;第5條以女子“窺觀”之狹喻君子應明見“陽剛中正之道”;第6條以“陽動而萬物生”喻示圣人應體天道以應人事;第7條以“豮豕之牙”說明君主如何自治治人的道理;第8條以雷風之“恒”說明君子如何在“變”中立“不易”之方;第9條以“遁”之象喻君子應通過“嚴以自守”以應對小人;第11條以“陽盛而陰將盡”說明“戒慎”為“保治之道”;第13條以修井儲水說明為政“修德”的重要性;第14條以乘壯馬拯初渙之群說明“柔順從陽之道”;第15條通過“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說明“理一而已”;第17條揭示天地、日月和人,“其理一也”;第19條說明“道器”關系。在湛氏之“測”文中,多含有對正統易學觀點的挑戰性。如程頤釋“初六:用拯馬壯,吉”時,稱“馬,人之所托也。托于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26]而湛氏則說;“若以二有剛中之徳為壯馬,然人乘馬上,而二反在前,非象旨矣”,認為程子的解釋不合邏輯。
注釋:
[1][2]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約言》。清康熙二十年(1755)黃楷刻本,第2、2頁(卷頁)。
[3]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七十二,《新泉問辨續錄》。
[4] 屈大均輯:《廣東文選(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第109頁,2008。
[5] 楊時喬:《周易古今文全書》,《周易古今文全書總序》。四庫全書本,第2頁(序頁)。
[6] 黃居中:《千頃齋初集》卷十三,《重刻周易全書序》。明刻本,第10-11頁(卷頁)。
[7] 胡培翚:《研六室文鈔》卷二,《周易分傳附經考》。清道光十七年(1837)涇川書院刻本,第2頁(卷頁)。
[8][9][16][20][24]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七,第2、2、2、2、3頁(卷頁)。
[10]李光地等:《周易折中》,《御纂周易折中凡例》。四庫全書本,第1頁(“卷首”頁)。
[11][14][17][23][25] 黃省曾:《五岳山人集》卷第二十六,《吏部尚書湛公古易經傳訓測序一首》。明嘉靖間刻本,第12、14、14、14、11頁(卷頁)。
[12][19] 吳伯雄編:《四庫全書總目選》。南京:鳳凰出版社,第12、18頁,2015。
[13] 牛鈕等:《日講易經解義》卷十五,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內府刻本,第1-2頁(卷頁)。
[15] 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中篇》四庫全書本,第9頁(篇頁)。
[18]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四庫全書本,第11頁(卷頁)。
[21] 陳鐘英等主修,王詠霓總纂:《黃巖縣志》卷二十五。清光緒三年(1877)刊本,第10頁(卷頁)。
[22] 蔡汝楠:《說經札記》,《易經總記卷一》。明天啟三年(1623)蔡武刻本,第2頁(卷頁)。
[26] 程頤:《伊川易傳》卷八。元刻本,第12頁(卷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