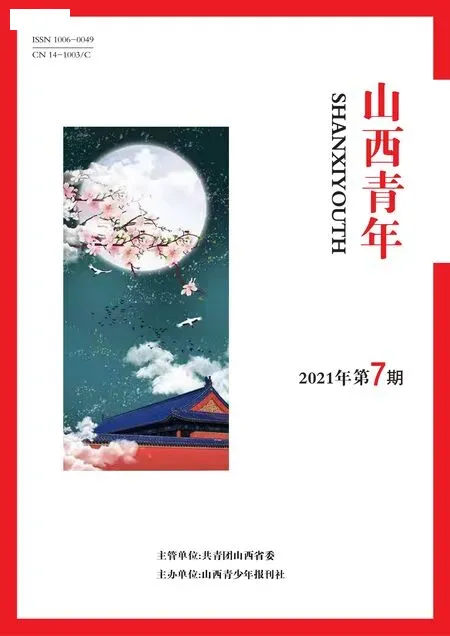民生檔案利用策略
姜海平
(大慶市大同區(qū)民政局社會救助服務(wù)中心,黑龍江 大慶 163515)
民生檔案是黨和政府各部門、各單位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中形成的真實(shí)記錄,涉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是維護(hù)人民群眾各項(xiàng)權(quán)益的原始憑證。有效利用民生檔案將對當(dāng)?shù)氐拿裆纳铺峁椭=陙恚浴懊裆鷻n案利用”為議題的研究性文獻(xiàn)大量涌現(xiàn),研究者基于自身的職業(yè)立場,對上述議題展開了多方位、立體式的闡述。2020年在我國是不平凡的一年,該年不僅是精準(zhǔn)扶貧工作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同時,在2020年年初爆發(fā)了眾所周知的公共衛(wèi)生事件,這就為地區(qū)民生工作的開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立足于“十三五”向“十四五”邁進(jìn)的關(guān)鍵時期,筆者重提民生檔案的利用議題,更凸顯它在社會保障工作中的重要價值。
一、本文研究的理論背景
本文研究主要基于以下理論背景而展開,并在區(qū)域植根性要求下提出了新的論點(diǎn)。
(一)民生檔案整合與利用在新時期區(qū)域發(fā)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在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民生檔案整合與利用面臨著新契機(jī),需要檔案管理人員注重構(gòu)建更加人性化及便捷化的檔案管理機(jī)制。
(二)民生檔案是服務(wù)民生的真實(shí)歷史記錄,是社會公共服務(wù)體系的有機(jī)組成部分。應(yīng)從民生政治、民生策略和民生價值等角度,對民生檔案服務(wù)民生的戰(zhàn)略高度、整體建設(shè)和創(chuàng)新利用體系進(jìn)行認(rèn)識。
(三)應(yīng)在分析民生檔案基本特征及服務(wù)現(xiàn)狀的基礎(chǔ)上,對民生檔案聯(lián)動共享的發(fā)展歷程、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及面臨的問題進(jìn)行認(rèn)識,并從服務(wù)模式、管理監(jiān)督機(jī)制、運(yùn)行機(jī)制、協(xié)同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民生檔案聯(lián)動共享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策略。
(四)要保護(hù)好公民個人信息權(quán)利,必須完善國家法律法規(guī)、建立科學(xué)的檔案管理規(guī)范、強(qiáng)化保護(hù)個人信息權(quán)利的行業(yè)自律意識。共享精準(zhǔn)扶貧檔案,有利于扶貧工作的順利開展,為黨和政府制定幫扶決策提供依據(jù),促進(jìn)社會和諧。但是,這種共享應(yīng)限制在一定的地域和指定的網(wǎng)域中,堅(jiān)持適時、適地、適當(dāng)?shù)脑瓌t,使精準(zhǔn)扶貧檔案真正為精準(zhǔn)扶貧服務(wù)。
以上所給出的理論背景,都在不同角度對民生檔案議題展開了討論。而且,都基于當(dāng)前的網(wǎng)絡(luò)化環(huán)境,對民生檔案中的信息共享提出了要求。與此同時,當(dāng)前研究仍存有宏觀視野、原則性導(dǎo)向的特點(diǎn),這或許對我國民生檔案的長期發(fā)展具有啟示性作用,但就解決眼下的實(shí)際問題尚需繼續(xù)提高其指導(dǎo)價值。鑒于此,筆者試圖在本職工作的經(jīng)驗(yàn)累積中,為短期民生檔案急需解決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思考。
二、民生檔案利用所存在的不足
立足于民政局社會救助中心的工作職能,在民生檔案利用中主要面臨以下三個方面的不足:
(一)線上線下檔案信息的閉合存在不足
當(dāng)前在民生檔案中需契合網(wǎng)絡(luò)化時代的技術(shù)特點(diǎn),即在線上實(shí)現(xiàn)信息共享[1]。然而,若要發(fā)揮網(wǎng)絡(luò)化時代的技術(shù)特點(diǎn)(優(yōu)勢),首先需保證在線民生檔案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實(shí)性。在工作實(shí)踐中發(fā)現(xiàn),個別當(dāng)事人的民生檔案信息,存在著線上與線下之間的閉合問題。問題的形成固然與檔案錄入人員的工作質(zhì)量有關(guān),但主要原因還需從民生檔案信息補(bǔ)充環(huán)節(jié)來考察。如,根據(jù)A某的填報(bào)信息已經(jīng)形成了線下原始檔案信息,線上檔案信息也根據(jù)線下信息進(jìn)行了錄入。但又因各種緣由A某向救助中心提交了補(bǔ)充材料,但此時的補(bǔ)充材料可能并未及時錄入在線系統(tǒng),這樣所共享的在線信息便存在著不完整性,并可能削弱對A某最終的救助力度。
(二)民生原始檔案信息的歸類存在不足
實(shí)現(xiàn)民生檔案的有效利用,需依照標(biāo)準(zhǔn)化流程來展開,這樣才能確保檔案信息在采集、比對中的及時性和便捷性。筆者在工作實(shí)踐中發(fā)現(xiàn),盡管民生檔案在歸集中遵循著一定的標(biāo)準(zhǔn),但這種標(biāo)準(zhǔn)存在廣泛性、剛性的特征,從而使得在采集和比對民生檔案信息時存在爭議。產(chǎn)生爭議的原因是基層救助中心的民生檔案歸類標(biāo)準(zhǔn)缺乏區(qū)域植根性,即隨著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環(huán)境的不斷變化,當(dāng)事人的“社會關(guān)系”也會隨之發(fā)生變化,變化后的社會關(guān)系將影響當(dāng)事人的經(jīng)濟(jì)地位、致困緣由、主觀訴求等因素。這就意味著,基層救助中心若不根據(jù)本地實(shí)際情況優(yōu)化或重建檔案歸類標(biāo)準(zhǔn),那么在民生檔案利用中可能會出現(xiàn)“苦樂不均”的現(xiàn)象。
(三)民生原始檔案信息的開發(fā)存在不足
此時的不足可以界定為:民生原始檔案信息的開發(fā)問題。需要指出的是,救助中心在開展民生救助工作時需具有前瞻性和預(yù)見性,這就需要對現(xiàn)有的民生檔案信息進(jìn)行大數(shù)據(jù)分析,從中發(fā)掘出本土救助人群的需求偏好和主觀訴求。這里暫且不論民生檔案歸類問題對大數(shù)據(jù)分析所帶來的困擾,當(dāng)前對民生檔案原始信息的大數(shù)據(jù)分析工作仍較為滯后。事實(shí)上,隨著民生檔案信息向線上遷移,這便為利用各種分析手段提供了便利。然而,當(dāng)前在對民生檔案信息所做的分析中,實(shí)證分析力度遠(yuǎn)大于規(guī)范分析的力度,即工作人員通常習(xí)慣于回答“是什么”,而較少去思考“應(yīng)該是什么”。對于提升民生檔案利用績效而言,或許在民生檔案管理中引入價值判斷,更能契合救助人群的實(shí)際需要。
三、增強(qiáng)民生檔案利用績效的策略
(一)側(cè)重民生檔案信息的網(wǎng)絡(luò)化搜集
目前,再去討論“如何實(shí)現(xiàn)線上與線下民生檔案信息的閉合問題”已缺少實(shí)用價值,畢竟在網(wǎng)絡(luò)時代,當(dāng)事人已經(jīng)逐步習(xí)慣于借助手機(jī)端來發(fā)布各類信息。因此,基層救助中心應(yīng)側(cè)重于民生檔案信息的網(wǎng)絡(luò)化搜集。具體的實(shí)施策略為:(1)在賬號、密碼后臺管理的基礎(chǔ)上,對當(dāng)事人的私人信息進(jìn)行嚴(yán)格識別,對于具備救助資格的個人賦予專屬在線賬號。(2)盡可能在智能手機(jī)端開展在線檔案信息搜集工作,并以基本信息模塊、個性化信息模塊作為信息錄入平臺,并根據(jù)區(qū)域民生工作的實(shí)際情況,重點(diǎn)細(xì)化個性化信息模塊所包容的民生信息內(nèi)容。(3)加強(qiáng)民生檔案信息數(shù)據(jù)庫管理,并匹配基本信息模塊、個性化信息模塊分類進(jìn)行數(shù)據(jù)儲存。
(二)建立植根性的民生檔案歸集標(biāo)準(zhǔn)
在痕跡管理的要求下,在線下民生檔案信息開發(fā)利用前,需建立植根性的民生檔案歸集標(biāo)準(zhǔn)。民生檔案歸集標(biāo)準(zhǔn)應(yīng)根據(jù)當(dāng)?shù)厣鐣?jīng)濟(jì)環(huán)境的變化而進(jìn)行優(yōu)化或重建。具體的實(shí)施策略為:(1)加強(qiáng)對本地民生案例的調(diào)研工作,在區(qū)分城鄉(xiāng)救助對象的基礎(chǔ)上,分類開展民生案例的調(diào)研。(2)根據(jù)分類開展調(diào)研工作所得到的信息,通過提煉出信息中的一般性因素,以此作為優(yōu)化和重建民生檔案歸集的標(biāo)準(zhǔn)。(3)結(jié)合筆者的工作體會,應(yīng)重點(diǎn)設(shè)置民生檔案中個性化信息的歸集標(biāo)準(zhǔn),如可以將被救助者的意愿、聯(lián)代性救助需求、被救助者的資產(chǎn)結(jié)構(gòu)等作為一級指標(biāo),并以此繼續(xù)開發(fā)出可供操作的二級指標(biāo)。為了便于之后的大數(shù)據(jù)分析,救助中心應(yīng)對指標(biāo)內(nèi)容賦予“標(biāo)準(zhǔn)化表述”,并可以用數(shù)字給予替代。
(三)應(yīng)用大數(shù)據(jù)分析實(shí)現(xiàn)參數(shù)化管理
對民生檔案信息實(shí)施參數(shù)化管理能夠契合網(wǎng)絡(luò)化時代下的技術(shù)要求,也能根據(jù)國家、地區(qū)的相關(guān)救助政策、標(biāo)準(zhǔn),快速精準(zhǔn)鎖定救助人群,并有助于大數(shù)據(jù)分析的需要。具體的實(shí)施策略為:(1)救助中心在對指標(biāo)內(nèi)容賦予“標(biāo)準(zhǔn)化表述”的基礎(chǔ)上,應(yīng)開發(fā)出適應(yīng)本地救助特點(diǎn)的數(shù)值編碼標(biāo)準(zhǔn)。如,可以由一組數(shù)字區(qū)分救助對象的來源(城市或農(nóng)村),然后依據(jù)救助對象檔案信息的重要程度,依次開發(fā)出可以比對的數(shù)字代碼,這樣就能為民生檔案的利用,提供數(shù)字信息化管理的條件。(2)將已開發(fā)出的數(shù)字代碼標(biāo)準(zhǔn)轉(zhuǎn)化為條形碼,并將條形碼粘貼在紙質(zhì)民生檔案的紙袋上,便能在利用時快速識別需要救助的對象,而避免了再次查閱檔案的繁瑣。(3)在對線上民生檔案數(shù)字化信息進(jìn)行大數(shù)據(jù)分析后,便能發(fā)掘出本地民生救助的主要方向,為救助中心工作提供路徑指向。
(四)以檔案開發(fā)驅(qū)動崗位能力的提升
基層救助中心民生檔案管理人員,是有效利用檔案資源的中堅(jiān)力量,但似乎在諸多研究者的視角下,并未關(guān)注這類工作人員的崗位能力提升議題。筆者認(rèn)為,應(yīng)以檔案開發(fā)來驅(qū)動崗位能力的提升。具體的實(shí)施策略:(1)應(yīng)對檔案管理工作人員進(jìn)行組織動員,使他們能夠認(rèn)識到有效利用民生檔案的現(xiàn)實(shí)意義。(2)組建專門的民生檔案開發(fā)團(tuán)隊(duì),團(tuán)隊(duì)成員主要包括檔案管理人員、計(jì)算機(jī)操作人員、數(shù)據(jù)庫開發(fā)人員,在缺乏條件的情況下可以與計(jì)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供應(yīng)商合作,但需要對民生檔案信息做好保密措施。(3)在檔案開發(fā)的過程中加強(qiáng)人員之間的業(yè)務(wù)交流,使他們能夠在“干中學(xué)”獲得相應(yīng)的業(yè)務(wù)能力。
四、工作展望
(一)增強(qiáng)與各類社會組織的信息聯(lián)系
在我國社會網(wǎng)格化管理模式有待完善的今天,以及社會養(yǎng)老體系有待強(qiáng)化的當(dāng)下,需要增強(qiáng)與各類社會組織的信息聯(lián)系。這里的各類組織除了社區(qū)、養(yǎng)老保障中心外,還應(yīng)包括基層黨委、單位離退休辦等組織。通過與他們的聯(lián)系多途徑收集檔案信息資源,并根據(jù)多方信息來源進(jìn)行比對,從而提升民生檔案建設(shè)的質(zhì)量。
(二)與社保部門建立起信息共享機(jī)制
在彌補(bǔ)民生檔案建設(shè)短板的要求下,可以與社保部門建立起指定信息的共享平臺。這里指定信息主要指向:該老年人是否健在。若建立共享平臺存在著技術(shù)和制度障礙,則可以通過定向查詢的方式來解決。
(三)調(diào)整崗位工作機(jī)制實(shí)現(xiàn)人員往來
社區(qū)管理已成為我國人口管理的基本單位,為了更好的與社區(qū)工作人員進(jìn)行合作,以及通過合作來核實(shí)相關(guān)老年人的檔案信息,則需要通過調(diào)整崗位工作機(jī)制實(shí)現(xiàn)人員往來[2]。可以采取片區(qū)蹲點(diǎn)制度來固定與社區(qū)往來的工作人員,使他們能夠跟蹤特定區(qū)域老齡人群的動態(tài)信息。最終,反饋到民生檔案建設(shè)中來。
綜上所述,基層救助中心應(yīng)側(cè)重于民生檔案信息的網(wǎng)絡(luò)化搜集。在痕跡管理的要求下,在線下民生檔案信息開發(fā)利用前,需建立植根性的民生檔案歸集標(biāo)準(zhǔn)。對民生檔案信息實(shí)施參數(shù)化管理能夠契合網(wǎng)絡(luò)化時代下的技術(shù)要求,也能根據(jù)國家、地區(qū)的相關(guān)救助政策、標(biāo)準(zhǔn),快速精準(zhǔn)鎖定救助人群,有助于大數(shù)據(jù)分析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