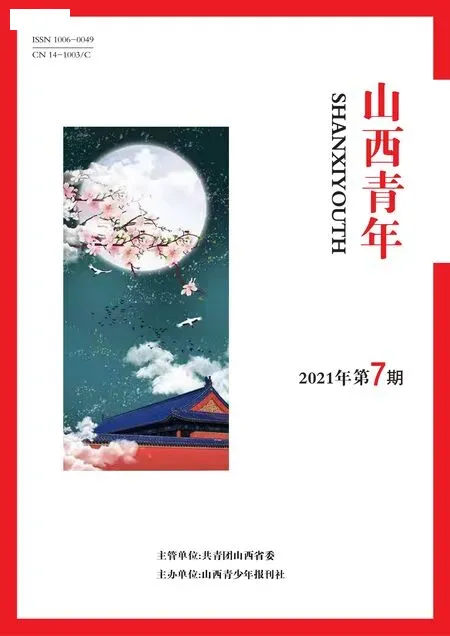社會工作介入社區養老的現狀以及優化路徑
鄭若霞 朱冬茹 王佩芬 洪采儀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知識產權與法學院,廣東 佛山 528000)
據統計,2015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2.22億,占總人口的16.15%。預計到2020年,老年人口達到2.48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7.17%,其中8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3067萬人。面對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峻,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全面建成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很多社區養老機構也慢慢引入社工,運用社工“助人自助”的服務理念以及同理心、接納、保密、不批判的專業技巧,為老人提多樣化的服務,提高服務效果,為老年生活提供質量保障。但由于我國社會工作及社工介入老年社區養老服務的發展還處于早期階段,服務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困境和阻礙。
一、社會工作介入社區養老的現狀及困難分析
(一)專業的社會工作人才需求
其一,社工人才存在流失現象。一方面是專業認同感、成就感低導致的人才流失,社會工作在我國知名度低,社會工作者在入駐社區開展養老服務的過程中,給社會工作者的介入和服務的開展帶來一些阻礙;另一方面社會工作者面臨著養老服務開展與服務對象實際需求存在心理壓力,作為服務購買方的基層政府對社工專業不甚熟悉,社會工作者在具體實務中往往面臨著完成政府指標與滿足服務對象需求之間的矛盾,由此對專業價值理念產生疑惑,因此社會工作領域難以留住人才。此外,由于我國社會工作發展水平尚待提高,目前我國社工專業最高學位為專碩,相對于其他領域,社會工作薪酬待遇、晉升空間較低,社工人才在遇到發展瓶頸后往往會轉向其他行業。
其二,社會工作者專業化水平低。社工人才流失率較高導致大部分社會工作機構處于社工崗位空缺狀態,一些社會工作機構為了填充空缺的崗位被迫降低社工崗位專業門檻,導致社會工作者專業素質良莠不齊。根據“中國社會工作動態調查”(CSWLS2019),在全國樣本中,53.57%的機構總干事沒有接受過社會工作專業學歷教育,59.98%的理事長和53.57%的總干事未接受過專業學歷教育。[1]非社會工作專業出身的社會工作者缺乏系統的專業理論、技能的支撐,其所提供社區養老服務缺乏專業保障。
(二)養老服務無法適應老年人多層次的需求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不同的人群有不同層次的需求,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的需求也會相應發生改變。生活在同一社區的老年人,由于面臨的實際情況不同,群體間也會呈現出同質性相對較弱的特點。一般情況下,社區里的老人可以分為以下幾類:高齡老人、中高齡老人、低齡老人、獨居老人和不能自理的老人等等。以上這些不同特征類型的老人,面臨的問題和需求都會有所不同。在社區養老服務中,社會工作基本可以根據不同類型的群體提供相對應的服務,但是介入的層次還有待提升。在實際的社會工作養老服務中,我們可以發現當前的社區養老服務主要集中在日間照料和文娛活動方面,這對于老年人養老質量的提高是有幫助的。但是在老人養老過程中更深層次需求的挖掘和服務方面,例如對老年人進行心理輔導和教授一些知識和技能等,社會工作的思考和介入服務還有所欠缺。
(三)各主體之間缺乏交流溝通,聯動性較弱
由于社區、社工、志愿者之間缺乏交流與合作,聯動性較弱,對社區養老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首先,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受到政府和人民的關注,社會上也更是倡導年輕人要為老人群體服務,但過度的照料和關心也給老年人帶來不便。例如,在同一天就有幾批志愿者分別來到老年人家里,幫助老年人清潔打掃房間、與老人聊天,影響老人群體的正常生活。由于這些志愿者沒有進行專門的培訓,對老年人的情況沒有進行詳細的了解,會影響老年人的情緒。其次,老年人不了解社工這個職業,在日常接觸中對社工難免有些抵觸心理,因此社工很難進行老年人的需求評估,同時社區工作人員沒有搭建好連接社工和老年人的橋梁,難以讓社工更好地了解老年人多元化需求。
(四)養老服務資金支持薄弱
政府資金投入是社區養老資金的主要來源,大型的養老項目、非營利服務組織、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均要靠政府資金支持,僅有少部分來自民間資本。首先政府資金投入總額的不確定性會直接影響社工機構的正常運轉,比如社工人員配備的人數、服務活動的次數、服務活動的質量等,經費的不足導致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標準降低和服務受眾群體范圍變窄,很多需要幫助的老人不能享受到服務,從而使居家養老的福利性嚴重不足,極大影響著社區養老的服務質量。其次政府資金投入與老年人多樣化需求之間難以保持平衡,老年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既有生活照料層面、醫療健康層面的需求,也有精神層面的需求,然而政府投入的資金有限,難以顧及老年人多方面的需求,往往只能集中于某一類的養老服務投入或者盲目投入,對于老年人需求量大、需求急迫的養老資金投入力度遠遠不夠,最大程度上只能滿足經濟困難老人的需求,而對需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的老人就難以提供專業化服務。
二、社會工作介入社區養老服務的優化路徑
(一)完善社工人才引進、培養、激勵機制
在社區養老領域中,針對社工專業化、職業化水平低和人才流動性大的問題,應依托政策引導、社會工作機構內部人力資源管理改革吸引人才、培養人才、留住人才。首先,政府應出臺相關社會工作機構評估硬性指標,提高社會工作機構內持有職業資格證書的專業社工人員人數、比例要求,促使社會工作機構嚴格執行“持證上崗”制度,保障在崗社工的質量和服務水平。其次,在社工人才培養方面,一是鏈接高校資源對社工人才進行定期培訓,鞏固社工理論知識;二是定期與其他機構合作,帶領社工外出交流學習,增加社工人才實務經驗;三是機構內部定期進行專業能力考核,檢驗社工人才培訓成效。此外,社會工作機構內部應建立明確清晰的晉升機制,形成良性競爭機制,提高社工人才的工作積極性。
(二)多層次關注老年人需求,協同老年人良性發展
立足于老人的實際情況,對其問題和需求進行合理的評估,才能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在社區中,應該根據不同的老人群體,對高齡老人、中高齡老人、低齡老人、獨居老人和不能自理的老人的需求進行分析,提供深層次高質量的養老服務。比如高齡老人和生活難以自理的老人群體,由于身體健康問題需要更多的照料,但是如果與人缺乏精神上的交流,會感到孤獨寂寞,所以對于這類老人,社會工作在提供日間照料的同時,也要注意老人的精神狀態和心理需求,提供精神支持和個案咨詢。再比如對于低齡老人,這類群體一般身體狀態良好,行動自如,生活上基本可以依靠自己。在低齡老人自愿的前提下,社區可以支持、鼓勵和提倡低齡老人參與社會發展和公益事業,體現“獨立、參與、照料、自我實現和尊嚴”的老年人基本原則。[2]或者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開設技能性課程,教授老人新的技能,提升生活的本領,使其“老有所為”。同樣,社會工作者也需要關注這類老人的心理需求,提供個案咨詢,改善老年人的心理狀態,提升社區養老服務的質量。
(三)整合社會資源,多元主體參與社區養老
隨著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和政府職能的轉移,養老服務更多地被交付給社會,多元主體掌握更多主動權的同時,也需要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一方面是對養老服務的供給模式進行創新。首先,推動“社工+義工”聯動模式的建立,社會工作者通過對志愿者進行專門的培訓并引導、帶動他們參與社區養老服務活動,緩解養老服務人力資源匱乏困境的同時,也提高了志愿者服務過程的質量;其二,孵化社區養老服務自組織,讓社區居民對于老年人更加了解且讓老人有親近感。社會工作者在養老服務項目中,通過培養志愿者骨干,逐步孵化社區養老服務自組織,促進養老服務志愿者隊伍的規范化、專業化,保障社區養老的服務項目的獨立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其三,建立“自下而上”的社區、社會工作機構、政府三個主體聯動模式,社區工作人員搭建好橋梁,幫助社工反饋老年人養老的問題,社會工作機構根據社區養老問題,進行走訪調研,申報公益創投項目,再由政府撥款支持養老服務項目,相較于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購買服務,該聯動模式更加貼近社區養老的個性需求。另一方面,從長者的社區養老資源出發,構建長者的社會支持網絡。社會工作者運用專業工作方法,挖掘、盤活、整合長者潛在的個人、家庭、社區資源,滿足長者多層次的個性化需求。
(四)拓展籌資渠道,引入民間資本
目前社會工作機構的社區養老服務項目資金來源單一,以政府購買為主,資金鏈易因項目結項而中斷,限制了社區養老服務的可持續性。因此,在社會工作機構項目制的養老服務之外,還需要引入民間資本,一方面是通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政策優惠的方式,扶持更多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進入社區養老領域,引導養老服務領域的企業或盈利性養老機構進駐社區,增加企業贊助社區養老服務活動的機會;另一方面在盈利性養老服務機構設置更多的社工崗位,保障社會工作專業養老服務的穩定提供。
三、總結
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日趨嚴峻,發展適應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養老服務體系迫在眉睫,在現代家庭小型化,居家養老模式日益衰退的背景下,社區養老模式適應了新時代的養老需求,由此,探索發展社會工作介入社區養老的路徑也成了我國老年社會工作領域的一個新熱點。我國社區養老模式正處于萌芽發展階段,社會工作在探索介入路徑的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的問題和挑戰,針對社區養老社工專業人才短缺、服務對象個性化需求得不到滿足、社區養老服務參與主體聯動弱、資金養老單一等難題,需要在政府指導下,多方社會主體積極協同參與,共同努力,通過政策推動社會工作機構建立健全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訓激勵機制,促進社會工作介入養老服務資金的多元化,以服務對象需求為本位,整合社會資源,不斷構建和完善本土化社會工作社區養老服務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