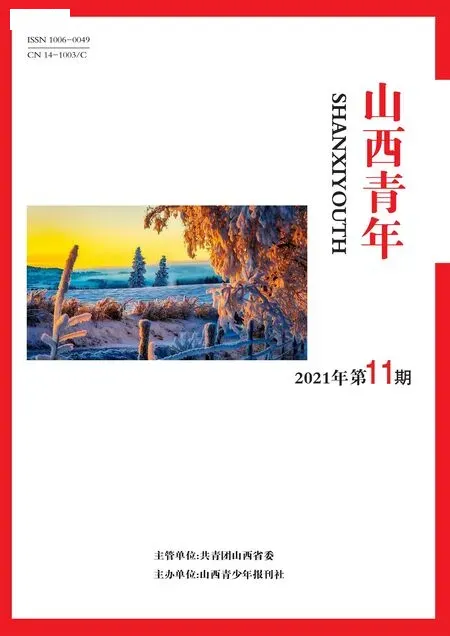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滄州音樂文化遺產保護的思路和對策研究
王 韻
(滄州師范學院,河北 滄州 061000)
滄州的音樂文化源遠流長,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凝結了當地民眾的民族文化和價值取向,表現出獨一無二的思維方式和民俗習慣。滄州有上百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音樂文化遺產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在“互聯網+”時代發展背景下,轉變傳統文化遺產保護觀念,以“互聯網+”思維重審音樂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對推進滄州音樂文化遺產的良性發展,有著長遠的意義。
一、“互聯網+”概述
所謂“互聯網+”,就是借助信息通信技術與互聯網平臺,促使互聯網和傳統行業的有機結合,從而創造出全新的發展生態。“互聯網+”是在知識時代創新2.0推進下構成的互聯網新業態與經濟發展新形態。“互聯網+”的特征是多樣化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信息化
“互聯網+”時代中,網絡信息化已經滲透到人類生活與生產中,諸多社會資源均整合于互聯網平臺中。現實與虛擬內容相融就會構成信息集群,信息集群與社會資源整合是現代化社會信息化的體現,現代文明充分貫徹了這樣的信息化理念。
(二)創新性
“互聯網+”是新時代技術開發的土壤,在“互聯網+”環境下諸多高新技術與應用內容均會伴隨時代需求持續發展與創新,互聯網的疏通與調整可以及時構成文化整合。所以,“互聯網+”可以給多種文化形式提供互動溝通平臺,在互動溝通過程中健全多元文化的融合,這種融合是相當及時和有效的,并為文化領域的創新思維提供理論基礎[1]。
二、滄州音樂文化遺產保護現狀
世界上很多國家很早就開展了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日本在1950年就頒布了《文化財保護法》,韓國也于1962年頒布了《文化財保護法》,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突尼斯、玻利維亞、阿爾及利亞、塞內加爾、肯尼亞等國家已經開始在國內層面采取了版權法或者準版權法的模式,力圖為其本國的民間文學藝術提供法律保護。同時,民眾對于本國文化遺產的認知和認可程度也處在比較高的水平。
2011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施行,對于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可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發展困頓之本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和發展需要根植于人們所處的周邊環境和社交活動中,而現代化、商品化帶來的種種大環境的變化,使得很多藝術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暢通無阻的網絡、豐富的電視節目和現代的生活方式,進一步瓦解了傳統藝術對觀眾的吸引力。
到目前為止,滄州的河間詩歌與青縣哈哈腔、吳橋雜技與武術、滄州落子與木板大鼓等被確定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滄州海興西路梆子與泊頭武術六合拳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黃驊漁鼓與任丘大鼓等五十個項目整合在了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里。除此之外,滄州地區共有六十多人被選作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在這些被選中的項目里,傳統音樂文化遺產占據比例最大,譬如木板大鼓、滄州落子、青縣哈哈腔等,均具備了非常高的藝術價值,尤其是木板大鼓,它為京韻大鼓的發展提供了很多藝術養料,并被稱為北方鼓詞類說唱音樂的塔基。而現如今,滄州地區音樂文化遺產保護情況并不樂觀,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滄州地區傳統教育投入不足,導致人才匱乏
目前全國都在提倡音樂的多元文化觀,而貫徹這種思想首先就應該關注我們國家本民族、本地域的多元文化音樂。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大環境的變化,原來很多承載著民間音樂傳承的載體在不斷削弱,而學校的音樂教育是目前傳承傳統音樂的最有效載體之一[2]。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很多學校的公共音樂課中傳統音樂的內容少之又少,并且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材使用等方面都出現了問題。由于教育投入的問題,導致了人才的缺乏,甚至影響了全民的文化認同感和民族認同感。
(二)傳統固化,缺乏創新
在滄州地區音樂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出現了欣賞模式單一、多元包容性差的問題。由于滄州民眾比較傳統的意識,長久以來一直維持著自我文化的發展與傳承習慣,而忽視了世界范圍內豐富多彩的音樂文化,而這樣的審美習慣,必定會對傳統音樂的發展產生嚴重的滯后作用。
(三)信息溝通不暢,音樂文化不能和時代相融
在滄州地區音樂發展中,尚未實現信息流通與現代化技術的有效結合,信息不通暢對滄州地區音樂文化發展影響比較大,導致滄州音樂無法在新形勢下得到全面開發和應用,僅僅停滯于自我封閉狀態,沒有形成良性循環的文化效應。
在“互聯網+”新形勢下,針對滄州音樂文化遺產的本體特征,探究新技術與新方法,找到適應滄州地區經濟文化發展需要的對策,已成為滄州音樂文化遺產研究人員的重要責任與使命。
三、“互聯網+”時代滄州音樂文化遺產保護舉措
(一)和現代音樂教育接軌
現代音樂教育采用的是新的教育模式,它是利用音樂教育的內容、手段、空間、時間的多樣化來實現課程育人的較靈活的教育模式。培養的是有個性并富于創造性的個體,并使受教育者成為主動的學習者。
在音樂的傳承過程中,一直把“口傳心授”作為音樂傳承的主要方式。這種言傳身教的方式確實能保證音樂文化遺產的原生態傳承,可是在經濟快速發展與文化漸微的人文生態下,這樣的傳統方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艱難的處境。倘若仍舊使用傳統的傳承方法,將難以調動年輕一代的學習興趣[3]。通過觀察可以發現,現代學習方法已經不再沿用聽講模式與學徒制,而是非常關注自主體驗與合作學習的探索;學習地點從家庭與學校轉移至各種空間,時間也不僅僅限制于課堂中,繼而延伸至各種碎片化時段。在“互聯網+”時代發展下,信息技術發展快速,新技術的持續涌現,為音樂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出現了互聯網與在線課堂等學習交流新生態,利用互聯網技術,確保音樂教育內容整合充分,利用豐富的網絡慕課帶動大家對滄州音樂文化展開深入了解。慕課的受眾是十分廣泛的,再加上慕課的學習沒有時間和空間限制,任何年齡、任何群體都可以隨時隨地借助慕課進行欣賞或者學習,慕課的開放性決定了它更有利于民間音樂的傳播。縣市區的群眾藝術館等非遺文化保護單位可以借助數字技術拍攝傳承人的經典唱腔與表演,把入選國家與省級名錄的音樂文化遺產項目編制成微課,構成在線慕課資源群。開發出適于現代人音樂審美需求的慕課,可以激發年輕一輩的學習興趣。
(二)音樂檔案的數字化管理
音樂檔案主要分為紙質、音頻、視頻三類載體。不可否認,很多音樂遺產在如今的大環境下,會不可避免地走向失傳的境地,所以,利用現代數字化技術對音樂遺產進行記錄、儲存、建檔是對音樂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補充[4]。但是由于認識問題和標準問題等原因,以往出現了重視紙質檔案,輕視其他檔案的問題。因此,要轉變傳統觀念,加大對音樂檔案數字化從人力、物力以及技術層面的投入;音樂檔案的數字化需要頂層設計,在實施之前需要統籌規劃其各個環節的技術指標和相關數據,這關系到民間音樂進行數字化加工后的存儲質量;引進專業人才,使用最合適的采樣技術和存儲格式,提高音樂檔案數字化的工作效率。
(三)建立多元音樂文化觀
在信息技術發展的大背景下,人們的娛樂方式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音樂的審美也應該順應時代潮流而產生質的變化。音樂人類學家布萊金曾經說過:“我們總是聽人說‘音樂是一門世界語’,但事實證明,今天我們欣賞和演奏的音樂,卻是一種狹小的局域的藝術形式,我們忽視民樂、原始音樂,以及亞洲卓越的藝術音樂……”。長久以來,欣賞模式單一,多元文化包容性差成了民間音樂發展的主要阻礙。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廣場舞這種健身運動在我國已經出現了很多年,但時至今日它的伴奏音樂依然是那幾首常見的歌曲,或者說是那幾種音樂風格的歌曲。可以說,世界范圍內有很多不同風格類型的音樂,但是我們不去選擇,就是因為我們缺乏音樂多元觀。音樂多元文化價值觀認為世界上不同的音樂文化有著相同的文化價值,這樣的觀點能使人們正視自己的民族音樂文化,從之前的狹隘單一的音樂欣賞模式中跳出來。建立多元文化觀可以使人們以更寬廣的視野、更全面地理解世界和各個民族豐富多彩的音樂文化,從而更深刻理解和接受我們本地的傳統音樂文化,這種觀念是繼承發展本地民族音樂的重要基礎[5]。
在這種觀念的引領下,我們會發現民間音樂里面那獨特而珍貴的美,比如,以五聲調式音階為骨干音的調式調性演繹出的中國旋律,民間音樂在審美層次展現出的中和之美等,這些都是我們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傳統藝術內涵,運用互聯網思維,將這些傳統音樂文化融入主流音樂文化和大眾音樂文化的多元文化市場中,為傳統音樂的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總而言之,滄州地區的音樂文化遺產項目,并非屬于文化的糟粕,而是在中華民族長期發展中凝聚的文化精髓。“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為滄州地區音樂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機遇,抓住機遇促進滄州音樂文化遺產獲得良好的傳承,是新時代賦予我們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