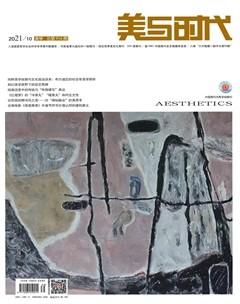“真正藝術家的勇氣”的時代內涵與當代意義
摘? 要:長久以來,馬克思主義美學界關于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這封回信的討論多集中于“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論。但少有人分析恩格斯對哈克奈斯的褒揚。其實,恩格斯稱贊她“表現了真正藝術家的勇氣”絕非客套話,而是在革命年代的背景下,具有特殊時代內涵的。一百多年過去了,“真正藝術家的勇氣”對當今文藝工作者而言,仍是種不可或缺的品質。
關鍵詞:恩格斯;真正藝術家的勇氣;現實主義;社會問題
1888年4月初,晚年恩格斯讀了女作家瑪·哈克奈斯轉寄來的小說《城市姑娘》,寫下了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致瑪·哈克奈斯》。他當時也許未曾想到,這封信中所提到的關于現實主義創作的理論問題將在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占據重要地位。迄今關于這封信的探討主要還是圍繞恩格斯那段經典的批評,即委婉地指出哈克奈斯未能“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藝術典型理論此后始終作為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核心問題,在百年間持續引起文藝評論界的討論。
但在這段批評前,其實還有一段對哈克奈斯女士的褒獎,恩格斯說道:“您的小說,除了它的現實主義的真實性以外,給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現了真正藝術家的勇氣。”[1]682為了理解這段話中恩格斯為什么稱《城市姑娘》展現了“真正藝術家的勇氣”,這“勇氣”又有何意指,我們就必須拋卻當下的成見,回到1888年,站在時代的大背景中體悟。
一、“真正藝術家的勇氣”之于瑪·哈克奈斯
19世紀80年代寫作《城市姑娘》的英國女作家瑪·哈克奈斯雖屬于小資產階級,但卻具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她在80年代初就經常深入到倫敦東頭工人區,調查了解工人的生活狀況,并且寫了一些有關工人問題的特寫和評論文章[2]。在她的小說《城市姑娘》里,紡織女工耐麗幻想上流階層的生活,因而被紳士格蘭特所引誘導致懷孕,此后耐麗在救世軍的救助下度日,產下一子后很快因病夭折。耐麗抱著死去的孩子在醫院與格蘭特相遇,受救世軍隊長洛布所感化的格蘭特為其安葬了孩子。在結尾,作者暗示耐麗將與工人喬治結婚。這的確是“無產階級姑娘被資產階級男人所勾引這樣一個老而又老的故事”。
但是,80年代的英國資產階級評論界早在恩格斯作出評論之前,對這部小說就幾乎一致抱持著否定的態度。他們認為這是“自然主義”“左拉主義”的小說,對作者批判資產階級角色阿瑟·格蘭特的態度大為惱火。顯然,哈克奈斯對英國生活現實的尖銳的揭露戳了他們的痛覺。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恩格斯才會稱贊哈克奈斯這部小說所表現出的勇氣:“這種勇氣不僅表現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庸人們而對救世軍所作的處理上……您覺得您有把握敘述一個老故事,因為您如實地敘述了它,使它變成新故事。”[1]682-683
可以看出,哈克奈斯的“勇氣”首先在于她“敢于冒犯傲慢的庸人們”。雖然她自身也屬于小資產階級,但她對工人階級的關切是真誠的。哪怕她對時代的革命潛流并不那么敏銳,哪怕她筆下的工人階級消極遲鈍、屈服于命運,她對苦難的倫敦東頭工人的同情是真摯的,她對資產階級自私、虛偽、冷酷本性的抨擊也是實實在在的。她揭露自己目光所及的社會問題,并嘗試進行解決。所以盡管恩格斯并不認同哈克奈斯為工人階級安排的最終出路——救世軍等慈善組織——本質上是利用資產階級的支持進行宗教宣傳、蠱惑苦難民眾放棄反對剝削的斗爭,他還是贊揚她敢于站在掌握話語權的階級對面,實實在在為貧弱的無產階級群眾發聲并為此切實遭受批評的勇氣。
再者,她“如實地敘述”了資產階級男人勾引無產階級姑娘的題材,沒有強行添加“一大堆生造的情節和曲意的修飾”來掩蓋階級對立的本質。階級的尖銳對立就是真實存在的,在這一點上,簡單樸素、不加修飾,勇于直面。這亦是一種勇氣。她筆下的青年女工耐麗平日給刻薄的裁縫鋪老板做手工,誠懇、善良、謙遜、篤信宗教的同時亦貪慕虛榮;幻想貴婦人的生活,結果被已婚資產階級紳士誘騙產子,失業而走投無路時,就自然地為救世軍所收容;甚至最后,她在孩子的墓地上想的也是孩子死去也好,否則活著也將和她一樣一生不幸。耐麗的確是一個消極的、毫無自助能力的無產者,但像她這樣的消極工人在當時的確存在,且并非少數。而那位“格蘭特先生”呢?在哈克奈斯筆下,他“外貌挺漂亮”“性格倒也溫順善良”“熱衷于政治”“善于辭令”。除此之外,他還有著當時的英國資產階級鮮明的特點——自私、虛偽、冷酷、傲慢。他誘騙、玩弄耐麗并把她拋棄之后,很欣賞自己的“懺悔”之意,“常常把自己的妻子比做德利絲;把自己比做盧梭”,“想起盧梭在陸德曼諾公寓巧遇德利絲后向她坦白的場面”;他為救世軍隊長洛布所感化,為耐麗盡義務——開了兩張支票,以此施舍便可替自己的良心贖罪。此時,英國資產階級狂傲又冷漠的形象躍然紙上。兩人的矛盾無疑正是兩個階級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樣如實地展現階級間的矛盾對立亦是一種勇敢。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恩格斯稱贊得更多的是哈克奈斯試圖追求現實主義寫作的勇氣,至于她的小說最終所呈現出的,顯然還有許多缺點,因為未能反映當時的典型環境,甚至“還不夠現實主義”。所以,恩格斯稱她“表現了真正藝術家的勇氣”既是對她所作嘗試的一種肯定,同時也是在鼓勵她沿著批判現實主義的道路繼續前行,要更深入地了解工人階級、了解科學的社會主義。這顯然是“一個有幸參加了戰斗無產階級的大部分斗爭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對初嘗試現實主義寫作的年輕文藝工作者的殷切期盼。
二、“真正藝術家的勇氣”之于當今文藝工作者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理論的產生都不可能絕對離開具體理論語境,正如卡岡所說:“風格的結構直接取決于時代的處世態度、時代社會意識的深刻需求,從而成為該文化精神內容的符號。”[3]在革命斗爭的時代背景下,恩格斯對文藝作品的點評皆是由革命功利性的視角出發的,他更看重作品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所具有的價值,而不太在乎作品在藝術層面的價值。馬克思、恩格斯所期待的現實主義文藝作品,其真實性應當是幾乎可與生活真實相等同的。對于這一點,朱立元先生曾指出,馬恩的現實主義理論與法國批判現實主義理論是有偏離的:“首先,出發點不同,法國現實主義文學是為了真實地再現社會現實,馬恩從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功利需要著眼;其次,思想基礎不同,法國現實主義奉行實證主義哲學,主張對客觀世界以自然的精確性加以描寫,馬恩則堅持唯物史觀;再次,理論側重點有很大不同,法國現實主義強調藝術描寫方面的真實性,逼真性和典型性,馬恩更注重作品對社會關系的正確把握與表現,前者使真實性服從藝術和審美要求,后者使真實性服從于認識的真理性和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上的價值觀念即傾向性,帶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功利色彩,而美學色彩相對沖淡了。”[4]
一百多年過去,同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革命年代相比,當今社會早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真正藝術家的勇氣”的理論內涵也當隨時代而有所更新。這些年間,現實主義之內涵經歷了繁復的衍變,衍生出許多的分類:“心理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意象現實主義”“現代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5]……但不論是哪一種現實主義寫作,要成為一個有勇氣的藝術家,都離不開對當前“典型環境”的持續關注,離不開揭露社會陰暗面的膽識,也離不開“如實地敘述”的能力和勇氣。
遙想1920年代,現實主義在我國的啟蒙階段,那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至今仍被當作現實主義文藝的典范。阿Q不是最早覺醒的那部分革命群眾,然而在辛亥革命大環境的影響下,愚昧的阿Q竟也叫嚷著要參加革命了。顯然魯迅筆下的未莊與辛亥革命的典型環境是不曾分割的。魯迅先生筆下的現實主義文學,字里行間透著當時最需要的、沖破一切黑暗的戰斗精神。在那之后,現實主義文學經歷起起落落,終于在當代擁有了更大的自由,能夠包容多樣的創作原則,“官場小說”“尋根文學”“底層文學”等,皆是從不同角度照見社會。譬如莫言的《蛙》,鄉村里的婦科醫生“姑姑”的身份隨著計劃生育政策三次起落,由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送子娘娘”到堅定執行政策、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再到晚年一心贖罪結果成為代孕行為的幫兇……這個形象非常復雜的典型人物亦是典型環境所造就的。莫言在寫作中,也沒有一味地歌頌或批判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帶著魔幻的色彩,但他終究還是給人一種“如實地敘述”的感覺。我們在《蛙》里,既能看到作者對于政治壓抑生命的探討和反思,更能看到主人公蝌蚪和“姑姑”以贖罪的方式釀造罪惡、以阻止悲劇的方式造成更大的悲劇,而作者對這樣沉浸于反思卻不關心當下的行徑做了不動聲色的質疑與批判。再譬如去年熱播的家庭電視劇《都挺好》的原著小說,“大女主”蘇明玉精明能干,可背后卻是她一地雞毛的原生家庭:蘇母精明強勢、蘇父懦弱自私、蘇明哲“圣母”老好人、蘇明成巨嬰不治,一家人矛盾不斷……網絡作家阿耐的文筆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相比,自然相去甚遠,但小說引起討論的重男輕女、啃老、養老難等話題無一不是我們身邊正在發生的、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僅從觀照現實、揭露社會問題、引起反思的角度看,可以說兩部小說同樣都體現著“真正藝術家的勇氣”。
三、結語
革命年代雖然遠去,但任何一個時代都呼喚“真正藝術家的勇氣”。孔子講,“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6]。文學是具有功利性的,它要求作家和批評家永遠以現實為依據來觀照文學。在消費主義甚囂塵上的當今社會,我們更加需要有“勇氣”的文藝工作者,沉下來,深入體驗生活,正確認識社會,關心人的命運,關注人的解放。筆者以為“真正藝術家的勇氣”之內涵在當下合該如此——勇于肩負關心全人類的社會責任感、勇于發現問題、勇于如實地揭露、勇于剖析與反思。惟其如此,現實主義文藝作品的時代透視力與藝術生命力方可得以長存。
參考文獻:
[1]恩格斯.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M]//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2.
[2]朱建良.科學的文藝批評的典范——重讀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J].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2):64-69.
[3]卡岡.文化系統中的藝術[C]//中國藝術研究院,《世界藝術與美學》編輯委員會,編.世界藝術與美學(第六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146.
[4]朱立元.偏離與錯位——對馬克思、恩格斯現實主義理論的歷史反思[J].上海文論,1989(1):45-74.
[5]徐芳.革命語境中的現實主義——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解讀[J].咸寧師專學報,2000(1):19-23.
[6]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208.
作者簡介:林賀曦,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美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