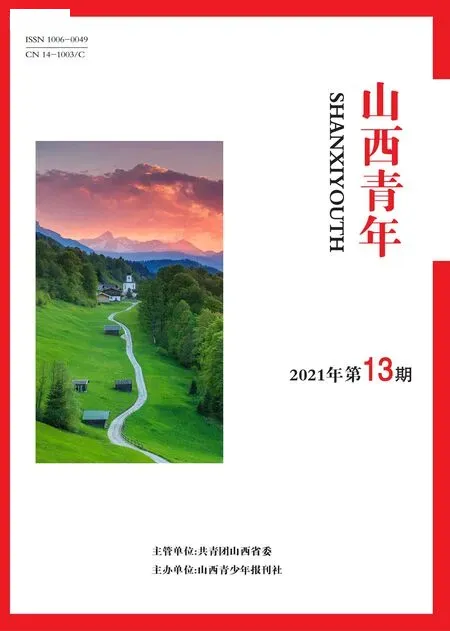譯者主體性視角下《王風· 君子于役》兩個英譯本的對比
——以理雅各和許淵沖版本為例
趙 月
(河北工業大學,天津 300000)
《詩經》又稱《詩三百》,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對《詩經》的翻譯始于16世紀的西方傳教士,而到了20世紀教會學術逐漸褪色,還原《詩經》以文學作品的本來面目[1]。詩歌是一種特別的文學形式,語言高度凝練概括,其中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和內涵,因此詩歌翻譯時不能僅僅關注內容傳達,譯者還應該帶領讀者體會原詩的美。譯者的主體性地位應該在詩歌翻譯中充分發揮出來,充分理解原作,再以同樣凝練的詩歌語言闡述出來,使譯入語讀者達到同原語讀者一樣的閱讀體驗。
一、譯者主體性概述
譯者在翻譯活動中擔任的角色舉足輕重,是整個翻譯活動的主體。但令人奇怪的是,一直以來,譯者的地位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甚至處于一種邊緣化的境地。在翻譯界內,人們對譯者的評價依然不高,甚至還強調譯者應該做一個“透明人”,在翻譯中隱去自己的痕跡。還有將譯者比作“媒婆”,將譯者的翻譯活動比作“帶著鐐銬跳舞”等等,強調譯者要忠于原文,不能發揮主觀能動性,可見譯者的地位較低問題已由來已久。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出現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形成了面向譯入語文化的文化學派翻譯理論,對我國的翻譯認識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因此譯者主體性研究成了譯學研究的主要內容[2]。
譯者主體性是指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其中,翻譯對象指譯者的實踐對象原作,參考對象原作者和目的對象讀者[3]。譯者主體性貫穿于翻譯活動的全過程。具體地說,譯者主體性不僅體現在譯者對作品的理解、闡釋和語言層面上的藝術再創造,也體現在對翻譯文本的選擇、翻譯的文化目的、翻譯策略和在譯本序跋中對譯作預期文化效應的操縱等方面。
詩歌翻譯作為文學翻譯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蘊涵著豐富的語言和文化內涵,如果說“翻譯是帶著鐐銬跳舞”,那么詩歌翻譯可以說是“不僅要帶著鐐銬跳舞,還要舞姿曼妙,令人賞心悅目”。詩歌翻譯的難度之大,甚至令弗洛伊德都驚呼“詩歌就是翻譯中丟失的那部分”。由于詩歌是一種集中反映社會生活并具有一定節奏和韻律的文學體裁,詩歌中承載了不同民族的情感和文化。因此在翻譯時,譯者不僅要將語言信息傳達出來,更應該將語言背后蘊藏的文化傳遞給讀者,但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存在差異,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尤其需要譯者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將詩歌中包含的意義盡可能地表達出來,傳遞給譯入語讀者。
二、理雅各和許淵沖的譯文對比分析
(一)詞意選擇層面的對比分析
首先是題目的翻譯,本詩的題目為《王風· 君子于役》,王風指的是反映民間生活的民歌,君子于役才是本詩的主體內容。在詩名的翻譯上,理雅各將其翻譯成了Ode,頗有“頌歌”的意味,這樣的處理可以使譯入語讀者聯想到西方頌歌詩,有助于讀者看到題目時,對本詩的體裁有一個大致了解。隨后理雅各又在Ode的后面音譯了(Keun-tsze Yu Yih)作為彌補,這種處理方式保留了原文的內容,是一種直譯的翻譯方法。而許淵沖則對原文做了充分的理解,采取意譯的方法,將題目翻譯為My Man Is Away,這種處理方式充分發揮了譯者的主體性,沒有拘泥于原文,但完全符合原文要表達的意義,同樣也易于譯入語讀者理解。個人更欣賞許淵沖的處理方式,理雅各將王風處理為Ode有失妥當,王風指的是反映民間生活的民歌,而Ode更多地指的是“頌歌”,和原文的民歌存在出入,會誤導譯入語讀者;另外理雅各將“君子于役”只做了音譯處理,沒有表達出原文包含的意思,譯入語讀者無法從中獲得有助于理解全詩的有效信息,沒有起到題目應有的作用。
首句“君子于役,不知其期”,理雅各譯為“My husband is away on service,/And I know not when he will return.”準確而達意,許淵沖譯為了“My man’s away to serve the State;/I can’t anticipate/How long he will there stay”,也做到了將原作的意思傳達清楚。兩個版本不同之處在于,理雅各符合原文的句式,譯成了兩個短句,而許淵沖則發揮了譯者的能動性,處理成了三句話。下一句“曷至哉”的意思是何時才能回家呢?理雅各的版本為“Where is he now?”,只是簡單地表示丈夫在哪里的疑問,沒有傳達出原作中妻子獨自在家,盼望丈夫早日回來的思念之情。相比之下,許淵沖處理成了“Or when he’ll be on homeward way”,明確表達了妻子希望丈夫早日歸家的心情,有助于譯入語讀者獲得同原語讀者相同的閱讀體驗。
接下來的三行“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從邏輯上講,似乎是先出“日之久矣”,然后“雞棲于塒”,接著是“羊牛下來”,但心理感受上卻是先看見雞歸巢,方知太陽落山,然后看到牛羊下山,更符合文學作品的順序。雖然理雅各保留了原文的順序,但缺乏深層心理感悟,因此譯文似有割裂感。而許淵沖先生則按照邏輯順序,調整了原詩的語序,首先譯出“日之夕矣”,接著翻譯雞歸巢和牛羊下山,這樣的處理方式雖然充分發揮了譯者的主體性地位,對原詩進行了調整和加工,但正是這樣也是譯文過于邏輯化,將全部的信息都做了顯化處理,缺少了文學意味。
下兩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是第一節的收尾,看到前面關于農家生活的描述,雞歸巢,牛羊成群結隊地回來,而妻子只能獨自面對落日,暗自傷感思念,這時妻子的情感達到了一個小高潮,因此不由得發出感嘆“如之何勿思”,意思是叫我如何不思念呢!理雅各和許淵沖的譯本都基于原文,使用how引導的特殊疑問句來表達妻子對丈夫的思念之深、語氣之強烈。不同之處在于前一句“君子于役”的處理,由于本句和上文第一句完全一致,因此理雅各服從原文,保留了這種一致性。許淵沖或許是考慮到同下文音韻的和諧,并未處理成與上文一致,而是調整了譯文語序,這也是許淵沖版最鮮明的特色所在:不拘泥于原文,譯者可以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礎上,靈活變通,產生更好的譯文。
第二節中“不日不月”的意思是已經數不清去了多久,“日”和“月”表示時間很久,對于這句詩的翻譯,理雅各依然忠實于原文,將“日”和“月”如實翻譯成了days or months,完全保留了原文的意象,而許淵沖的譯文則更為靈活,只將這句詩的實際含義“已經數不清去了多久”翻譯了出來,并未保留原文的意象。此外,本句詩和第一節的前三句在結構上有重復之處,因此,保留譯文結構的一致性,許淵沖先生也參照第一節的譯法,大部分譯文保持不變,只更改了少數細節之處。
接下來的三句與第一節相對應,只有個別字詞有所差別,體現了本詩在結構上采用重章疊句的藝術特點。理雅各的譯文同樣忠實于原文,結構上基本不變,只有個別字詞上按照原文做了相應的變動。許淵沖除了將“日之夕矣”做了時態上的變化外,剩余部分和上文完全一致,并未向原文那樣,對個別字詞做出改動。個人認為這兩種處理方式都可行,只是譯者采取的策略不同,導致產生的翻譯結果也不盡相同。
最后“君子于役,茍無饑渴”是全詩的結語,意思是“丈夫在遠方服役,但愿他不至于口渴挨餓吧!”這句詩也是妻子的情感達到頂峰,將上文對丈夫的懷念化作了對丈夫的美好祝愿,讀者從中可以感受到妻子對丈夫深厚的愛意。理雅各將“茍無饑渴”翻譯為“Oh if he be but kept from hunger and thirst!”,語氣詞Oh的使用,將原文妻子的深切情感表露無遺,譯入語讀者可以從中體會到詩中妻子對丈夫的愛和祝愿,如果說理雅各的譯文是將妻子的祝愿隱含在譯文中,那么許淵沖的版本“Keep him from hunger and thirst,I pray”,使用I pray,直接將妻子對丈夫的祝愿宣之于口,兩個版本一個隱晦低調,一個張揚顯著,都是譯者基于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對原文進行的再加工。
(二)格律層面的對比分析
原詩讀起來朗朗上口,主要歸功于韻律的運用。通讀一遍原詩,就不難發現,詩中的韻腳為AABCCD,即第一句的末尾“哉”和第二句的末尾“來”都押/ai/韻,第二節中第一句的末尾“佸”和第二句的“括”押/uo/韻,兩節的最后一句都不押韻。正是這種錯落有致的韻腳,使原詩讀起來朗朗上口,節奏感強。對比兩個譯文版本,理雅各的版本并未采取任何押韻方式,全詩沒有一個韻腳,可以說理雅各只關注到了詩歌字詞和形式的對等,而忽視了或者說無法兼顧音律方面的對等。相比這下,許淵沖的版本讀起來則更加順口,全詩在做到意義和形式符合原作的基礎上,兼顧到了詩歌的音律,譯本中包含著多個韻腳,例如/e/、/est/等,韻腳的變化使譯入語讀者讀起來充滿動態,可以感受到原語讀者同樣的韻律美。
三、結語
本文以譯者主體性為視角,從詞匯選擇以及格律兩個層面對比了理雅各和許淵沖兩個版本的譯文,發現總體上講,理雅各主張忠實于原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角色幾乎隱形,譯文基本按照原文亦步亦趨,力求盡可能保留原作的形式和內容;而許淵沖在翻譯中會在保證尊重原文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譯者主觀能動性,只求將原文含義傳達到位,而不會拘泥照搬原文字詞。不同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和方法不同,因此產生不同版本的譯文,通過對比和賞析不同譯文,有助于我們了解更多的譯者翻譯理念,在比較中增強詩歌翻譯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