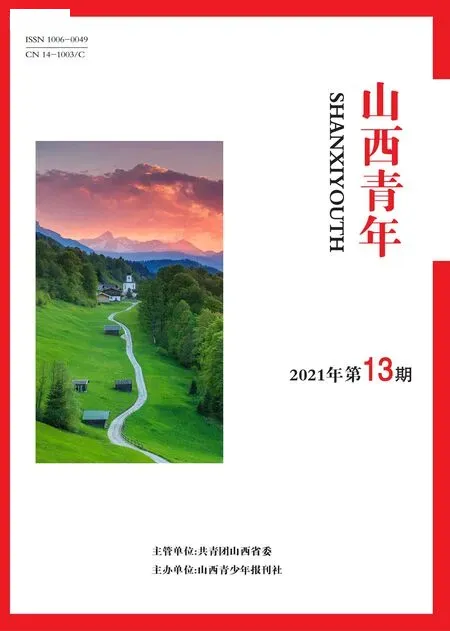從《白鹿原》看家本位文化
羅振華
(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湖北 宜昌 443002)
說起對家的重視,世界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與中國相比,家本位的傳統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了。《禮記· 大學》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修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1]把齊家作為修國的基礎,足見中國人對于家的重視程度。在以家為基本單位構成的中國鄉土社會里,家是每一個個體的根基所在,是他們人生的最終歸宿,亦是他們情感的最終寄托。正如《白鹿原》中鄉土社會的代表人物白嘉軒所言:“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腳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遲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頭。”[2]其實,無論是在傳統的白鹿原社會,還是在整個鄉土社會,“家本位”傳統在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中始終都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而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占據首位的也是“家”,每一個個體都是從屬于家庭的,他們的身上都背負著家族的榮辱興衰和整個家庭集團的利益。
一、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家本位思想
任何一種思想的背后都有其文化淵源,對于家本位思想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當時的原始人過著一種群居的生活,而他們所依附的群體就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所構成的氏族部落,每一個氏族部落都是一個整體,氏族部落中的個體在這個大整體中一起生產生活,他們開展一切活動的參考點是整個部落,也就是他們的“家”。古人在創造“家”這個漢字時就深受這種生產組織模式的影響。家,會意兼形聲字。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寫道:“家,居也。從宀,豭省聲。”[3]從“家”的甲骨文字形看,上面的“宀”是房屋,下面的“豕”就是豬,我們可以把這個豬看成是打獵獲取的獵物,在早期的原始社會,人們的食物來源基本上靠獲獵所得,放置獵物的地方也就是整個部落共同生活的地方,即他們的“家”。自大禹的兒子啟建立夏朝后,公天下變為了家天下,對于整個國家的領導權都停留在了一家一姓之間。但不管是公天下還是家天下,家本位的傳統是始終都沒有變的。
在此后長久的封建統治中,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社會倫理一直都占據著主導地位,而家本位思想作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也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社會制度、道德規范的制定標準也都與此息息相關。比如說古人所強調的天下一家、家和萬事興、家丑不可外揚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追求等。
一直到現在,家本位思想在我們的潛意識當中依然有著很深的根基。我們從一出生開始,家庭就會調動各種資源來培養我們。所以我們在長大之后取得的一切成就,不光是屬于個人的,更是屬于整個家庭的榮耀。當我們在經歷結婚生子、成家立業這些人生大事的時候,也會或多或少地涉及對家庭利益的考量,因為我們一直都明白:個人其實是從屬于家庭的,整個家庭的利益與其內部成員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沒有了家庭的個人就好像是沒有根基的浮萍,只能隨波飄搖,所以個人利益要服從家庭利益,以家為本。
二、《白鹿原》中家本位傳統的體現
白鹿原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家本位主義者就是白嘉軒了。在小說的一開始寫的就是白嘉軒連續娶了七個老婆,之所以會如此執著地娶妻,除了前六房女人短命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前六個女人都沒有為白嘉軒留下后代。在那個“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時代,沒有血親也就意味著整個家庭沒有了延續,沒有了發展下去的可能,這對于一個家庭來說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正因為如此,白嘉軒的父親秉德老漢在臨死之前,唯一的執念就是讓白嘉軒盡早娶妻,不要為他守孝,“哪怕賣牛、賣馬、賣地、賣房、賣光賣凈”也要為白家留下后代。在聽到白嘉軒答應了他的要求之后,秉德老漢才得以瞑目。隨后,白嘉軒在無意中發現了白鹿精魂所在之地,他認為這是神對自己的眷顧,為了借白鹿精魂改變自己的家運,他做了自己人生當中第一件見不得人的事:費盡心機地用自己的天字號水地換取了那片擁有白鹿精魂的人字號坡地。終于,在第七房女人仙草生下了頭胎兒子之后,白嘉軒才能心安理得地跪在主祭壇位上祭祀祖先。他也始終堅信,這是白鹿精魂帶來的好福氣。到了兒子孝義結婚的時候,他又發現自己的兒子不能生育,于是他又做了自己人生中第二件見不得人的事:讓自己的兒媳向長工的兒子兔娃借種。雖然這件事情他自己都有些反感,但為了整個家庭,他還是毫不猶豫地策劃了這么一出。縱觀白嘉軒的一生,應該也還算是一個比較正直的人,但在家庭利益面前,一向正直的他也選擇了做虧心事,可見整個家庭在他心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白嘉軒之所以如此看重整個家庭的利益,與他族長的身份是分不開的。作為一族之長,他的家庭就是整個家族的模范,所以他必須保證自己的家庭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存在,這樣才能起到模范帶頭的作用,得到整個家族的擁護,才能讓自己的家庭在整個家族中處于一個至尊的地位。因此,一旦出現有損家庭利益的事情,他都會不惜一切代價來挽救。眼見著大兒子白孝文和田小娥茍合在一起的事情已經暴露在了大家面前,他先是按照鄉約的規定狠狠地處罰了白孝文,隨后就果斷地選擇分家。盡管白孝文是他一直以來所培養的族長人選,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將白孝文趕出了家門,想要以此來保留整個家的顏面。在家庭的利益面前,一向寬厚仁慈的他也可以變得冷酷無情,哪怕是自己的親兒子,也不例外。
面對同樣的事情,長工鹿三也是像白嘉軒一樣來處理的,甚至比白嘉軒做得要更干脆。當他得知田小娥是一個不守婦道的女人后,就覺得娶這樣的女子進門簡直是有辱門風,所以一直不承認她的身份。而自己的兒子鹿兆謙還偏偏要與這樣的女子廝混在一起,他實在無法忍受,于是就和兒子斷絕了關系,放任他們在村外的破窯洞里不管不問。在黑娃被通緝期間,田小娥又和白孝文混在了一起,這讓鹿三更加看不下去了。要知道,白家對于鹿三來說,不僅僅只是簡單的主仆關系,更有著勝似親人的恩情。所以他絕對不允許這樣的女人再禍害下去了,于是就殘忍地將田小娥殺害了。鹿三寧愿做一個殺人兇手,也不能讓這樣一個女人侵害到整個家庭的利益。
與白嘉軒這樣一個地地道道的家本位主義者不同,鹿子霖則是一個官本位主義者,他從最開始的鄉約做到保長,一直以自己鄉約的身份為榮。實際上,他的官本位也是建立在家本位的基礎上的,他之所以喜歡做官,本質上還是想要通過做官給整個家庭帶來榮耀,再就是想要借此高過白嘉軒一頭,包括他后來設計讓田小娥勾引白孝文,也是出于此種心理。可惜后來他一直沒有如愿,在陪斗的時候發出一句“天爺爺,鹿家還是弄不過白家”的感慨,求而不得的他最終在瘋癲中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三、時代變遷對家本位傳統的沖擊:人本位意識的覺醒
我們知道“家本位”就是要以家庭為本位,以家族為本位,以團體和集體的意志和利益為重,這在過去生產力低下的小農社會里的確是十分受用的。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中國鄉土社會傳統的經濟體制發生了變化,社會流動性也增強了,人們逐漸淡化了“家本位”的意識,確立了“人本位”意識。當然了,我們這里的“人本位”并不是自私自利,所謂“人本位”是說在個人和家庭的比較中更重視個人,強調個人的生存、個人的利益、個人的意志、個人的發展,主張人的個性和獨立性。[4]白鹿原先后經歷了土地改革、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這些重大的歷史變革在改變外部環境的同時也在改變著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給整個白鹿原社會上的家本位傳統帶來了不小的沖擊。
在小說中,人本位意識表現最為強烈的就是田小娥、黑娃和白孝文,他們可以站在整個家庭的對立面去追求自己的個性,這實際上也是對封建禮教的一種反叛。在這三個人當中,白孝文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存在,他前期在白嘉軒的培養下也是屬于一個規規矩矩的家本位主義者,后來在鹿子霖的設計下走上了反叛的道路,這件事也給了他一個釋放內心本我的機會。不過最終黑娃和白孝文還是回歸到了家庭,從本質上講,他們對于家本位的傳統依然是認同的。除了他們,鹿兆鵬、鹿兆海、白靈這三個人的人本位意識則主要體現在對個人理想的追求上面,他們都是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青年,所以在思想覺悟上面要比前三者高出一些層次。在國家危難之際,他們選擇走出家庭,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革命理想,實現了自己人生價值的升華。
四、家本位傳統在現代社會的新生:“大家”與“小家”的交集
雖然在現代化的進程當中,家本位傳統受到了來自人本位意識的沖擊,但由于中國幾千年來文化傳統根深蒂固的影響,中國人今天在個人與家庭的比較中還是較為重家的。[5]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家本位傳統所強調的“重家意識”在具有很大凝聚力的同時,也是具有一定的狹隘性和保守性的,如今我國正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節點,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國家的繁榮富強奉獻出自己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國夢的實現,而不僅僅只是放眼于自己的小家庭。但我們也不可否認,在中國,要想增強整個國家的凝聚力,你就不能忽視中國人“家本位意識”的特點而簡單要求人們不顧家,而應在強調國家集體利益的同時,盡可能地照顧到各自的家庭利益。[4]
這就要求我們在新時代下,既不能徹底地拋棄家本位的傳統,同時也要兼顧時代賦予我們每一個年輕人的歷史使命,取“大家”與“小家”的交集。所謂“大家”就是我們共同生活的國家,還有我們所在的民族和社會。而“小家”就是我們個人的小家庭,這也就是我們常說到的家國情懷。國和家本就是一個統一體,家是最小的國,國是千萬個家,有了國我們才會有家。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才不會被家本位傳統中的保守性和狹隘性蒙蔽雙眼。就如小說中的鹿兆鵬、鹿兆海以及白靈一樣,他們在國家危難之際都投身到了革命中,保衛了自己的家園的同時也守護住了自己的國家。新時代下,我們需要更多像他們一樣的熱血青年為祖國建設添磚加瓦,為國家富強鋪路架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