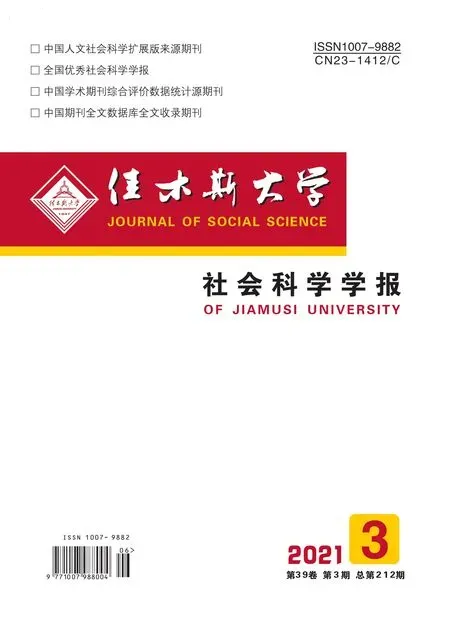遲子建《燉馬靴》的敘事藝術*
許青青
(安徽大學 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1)
作為當代文壇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遲子建的小說創作一直都保持在高產且高質的水準。她在2019年創作的短篇小說《燉馬靴》榮獲第十屆“茅臺杯”《小說選刊》年度短篇小說獎、“收獲文學排行榜”短篇小說獎,并入選了“中國小說學會2019年度小說排行榜”短篇小說榜。這部小說在思想意蘊上延續著遲子建對人性光輝的熱情贊美,在敘事藝術上的特色也因其短小精悍的形式顯得尤為突出。作者將個人的生存放置在特定的歷史環境、自然環境中,在人與人、人與物的牽扯中將“父親”絕境中的瞬間命運通過小故事的形式緩緩講述,既不失趣味,又能感人至深。
一、敘述者的雙重轉換
羅鋼在《敘事學導論》中提出:“任何敘事文學作品都必須具備兩個必不可少的要素,即一個故事和一個故事的敘述者。這是敘事作品區別于其他藝術和文學種類的最基本的特征”[1]158。《燉馬靴》最直觀的一個特色,也是該小說整體架構的一個基礎,就在于作者對小說敘述者的設計。她綜合運用了雙重敘述者,一是故事的講述者——父親,二是聽故事的人同時也是小說文本的敘述者——我。雙層嵌套的敘述者“父親”和“我”屬于不同的敘事視角,從而達到了不同的敘事效果。
法國的茲韋坦·托多洛夫把敘事視角分為三種形態:“全知視角(零視角)、內視角和外視角”[2]60。小說《燉馬靴》的敘事雖然具有歷史節點,但它不著眼于宏大的歷史敘事,反而將敘事視角轉向平凡的個人,以講故事與聽故事兩種視角相互轉換鋪開,通篇以“父親說”展開回憶性敘述,父親是講故事的人也是故事的經歷者,這是一種內視角,“我”作為聽故事的人,是一種外視角。而小說文本則由“我”轉述“父親”的故事,所以,便會產生不同的敘事效果。“父親”以內視角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的故事,作者包括讀者只能根據父親的口述內容知曉故事局部面貌。這在小說文本中多處可見:文本中一開始就表明故事時間不明;父親的抗聯部隊番號不明;后來在與日本兵的周旋過程中,父親不以“敵人”反而以“敵手”相稱;父親不解釋用手帕給敵手蒙面的具體原因;“再說狼得了吃的,就不會過來吃人。他說的吃人,是否包括敵手呢?這個話題我始終沒敢問他,直到他辭世”;父親點篝火,“是不是火葬了敵手?父親給出的答案總是模棱兩可的。”這種內視角的設置便產生了很大的敘事留白,作者和讀者都可以根據父親的敘述展開不同的想象與解讀。由此便產生了三種敘事效果:一是作者的想象以其外視角展開敘事,作者會根據自己的理解與體會展開文本的敘述,這就是小說整體呈現出的敘事效果;二是讀者根據父親的敘述展開自我想象填充,不受作者敘述介入的影響;三是讀者根據主觀設定后的敘述進行空白填充。小說中“父親自詡槍法不錯,用它打過野豬和狍子,為支隊改善伙食”,對此作者加入了自己的猜想“我一直懷疑他有吹噓的成分,因為在我童年時,看他參加武裝部的運動會,父親投擲的鐵餅和鉛球,都是不聽話的孩子,落腳點不在規定范圍內,沒一次成績有效的。”所以根據不同視角的敘述,在此呈現出三種相應的敘事效果,一是認同父親的說法,父親作為一名火頭軍神勇無比的形象再一次拔高;二是相信作者的敘述,父親的故事加入了自我渲染的成分,也許槍法確實一般般所以才被委任火頭軍;三是讀者根據文本自我解讀,或許父親槍法不差但也不算好,偶有一次打過野豬和狍子,槍法也在退伍后有所生疏,才會出現作者童年時看到的情景。文本中很多作者主觀上產生的疑問與情感傾向,都可以產生多重解讀效果。產生這種效果的前提是,正由于文本中的兩種敘事視角的轉換,打破了全知視角的無所不知的確定性限制,閱讀期待在文本的無限閱讀過程中形成多層次的敘事效果。
二、敘事空間的巧妙設置
“小說空間形式”理論是由美國文學批評家約瑟夫·弗蘭克最早提出的,他強調以空間干預時間,形成小說空間形式,特征是“事件的前因后果集邏輯順序被取消。”[3]71-77故事被拆解、破壞,通過拼貼、并置的方式重新組合。國內的空間敘事研究學者龍迪勇認為“小說家不僅僅把空間看作故事發生的地點和敘事必不可少的場景,而是利用空間來推動整個敘事進程。”[4]15-22空間要素在小說敘事功能中占有重要地位。
遲子建的小說研究中“鄉土”要素一直以來都是熱議的話題,這是因為她的小說背景基本都設置在北國大地,這便是一個整體上的空間范圍,河流森林、雪鄉凍土、東北風俗人情都成為這一特殊空間的具體表現。而短篇小說就像一個舞者在精小的圓桌上起舞,空間感常常要勝于時間長度,《燉馬靴》作為短篇小說,它的敘事空間感更為顯著。小說一開始便弱化了時間感,強化空間感,對于故事發生的時間“父親記得并不是很清楚,他說年份不重要,重要的是時令,寒冬臘月,祭灶的日子。”這里的時令并不是側重于時間,反而指向東北雪國大的空間,相較于南方,北方對于寒冬臘月的觸感更為強烈。緊接著就將故事發生的空間地點鎖定于四道嶺小黑山,在此父親所在的抗聯部隊與日本守備軍進行了激烈交火,故事后半部的空間地點是父親在雪地森林里與日本兵周旋、戰斗。不同于遲子建以往長篇小說廣闊的空間,《燉馬靴》將人物設置在一個封閉式的雪地森林中,故事的開展、高潮、結束都離不開這個封閉式的空間。這種相對狹小空間的設置,推動了整個敘事進程。正是空間距離小,所以在本來已是優勢的交戰中,日本兵突然返回,“父親說他們受到了前后夾擊,優勢立刻轉為劣勢。”這樣便轉入了下一個敘事,也就是“父親、日本兵、瞎眼狼”之間燉馬靴的故事,接下來這個故事的敘述也離不開這樣封閉式的空間,正是因為父親所在的支隊基本活動于頭道嶺附近的森林中,所以父親才有機會多次喂養并偶遇瞎眼狼,最后被其所救。在這樣封閉式的空間中,環境愈是惡劣,愈是能凸顯置身其中的人物心理,父親身處黑暗雪夜中被追擊,對于生的渴望的心理被極度放大,這是人類在絕境中生命意志的極致體現;敵手在同樣雪夜森林中,戰斗意志由強到弱,最后放棄掙扎,卻仍求得最后一點生命的尊嚴,這同樣也是對生命的尊重的一種體現。
除此以外,小說空間敘事也體現了約瑟夫·弗蘭克所說的“故事被拆解、破壞,通過拼貼、并置的方式重新組合”的特征。《燉馬靴》若以簡約的一句話概括,就是父親講述的一個抗戰故事,但卻是一個由“我”轉述故事,整個文本時間的長度整體拉長,并且打破了正常的故事時間,以碎片化式的拼接進行敘事。《燉馬靴》很明顯是由三個故事組成,一個是父親的抗聯支隊夜襲日本守備軍行動失敗,一個是父親被一個日本軍追擊,一個是父親瞎眼狼之間的故事。這三個故事之間本是相互聯系牽扯,但是在小說文本敘述中,作者多次加入自己的旁白、想象、回憶中斷故事時間,例如父親在繳了日本兵的槍后,作者隨之加入這個小馬蓋子槍成為父親俘獲母親芳心的后續。或者將故事中某些問題的原由后置,例如,襲擊行動那天日本兵為何突然返回?失敗后最終幾人從虎口脫險?這些問題的解答都并不存在于故事時間中,而是后來抗戰勝利之后才知道。也正是這樣封閉式的敘事空間才有了將故事進行拆解、拼接的可能性,因為它集中于故事發生的沖突點,不會涉及太多無關的人或物,造成敘事線性混亂。
三、敘事意象的別具匠心
敘事意象是楊義先生首次提煉出的中國敘事學的獨特范疇。所謂敘事意象,就是指在敘事作品中承擔敘事功能的、浸潤著創作主體主觀情感,能夠引發接受者的審美想象和審美情感,具有一定文化意蘊的特殊的藝術形象。筆者通過文本細讀發現《燉馬靴》中有兩個反復出現的意象——“狼”和“火”。這兩個意象,在敘事與審美功能上都有其特殊的價值含義。在遲子建的小說中經常能見到諸多動物意象,而且作者信仰萬物有靈,所以她筆下動物不只是單純的動物,常常寄托了作者的思想和愿望。《燉馬靴》中“狼”是貫穿小說始終的動物意象,甚至是小說的主角之一。瞎眼狼在故事中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它是故事進展的線索之一,同時也是后半程故事的光環所在。“狼”在一般人心目中往往是“惡”和“背叛”的象征,但是這部小說中的瞎眼狼反而是知恩圖報的存在,作者通過瞎眼狼與“父親”之間的互動,傳達出關于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關系。從自然環境角度看,“父親”不因慣常的偏見“狼是吃人不吐骨頭的野獸,喂不熟的”就對瞎眼狼置之不理,反而“實在心疼”,所以一次次給它投喂骨頭,后來“父親”陷入險境,也是多虧瞎眼狼相救。在這里,“父親”與“瞎眼狼”處于平等的地位,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們是互救的盟友。在此,遲子建想傳達的就是一種樸素的自然觀,人只要善待大自然,也會被大自然所善待。正如小說結尾父親的慨嘆:“人吶,得想著給自己的后路,留點骨頭!”
“火”也是小說中多次出現的意象,父親是一名火頭軍,行軍途中常備火柴,這是部隊陷入被動時的救生索。小說中對于火的多次精致描述主要體現在“篝火”上。父親用“篝火”來燒水、取暖、判斷敵手距離、燉馬靴充饑。在父親的逃生之路上,“篝火”在某種意義上對父親而言是活著,是希望,是光明。所以“父親說那夜的篝火太美了,將它周圍的雪花,映照得像一群金翅的蝴蝶!”對于敵手而言,他希望能葬于篝火,而非被狼吃掉,“篝火”是他保全生命最后一絲尊嚴的寄托。對敵手而言,“篝火”何嘗不也是一種希望與愿景。《燉馬靴》延續了遲子建一貫以來溫情地展示人性閃耀的創作主題,“狼”與“火”兩個意象對于連接敘事和深化主題產生了重要意義。
四、敘事倫理的引人深思
敘事倫理,在西方是伴隨各種倫理研究而興起的一門屬于倫理學的分支學科,對于文學研究而言,正式使用“敘事倫理” 這一專業術語的是亞當·桑查瑞·紐頓,他在其著作《敘事倫理》中從兩方面對這個概念進行了闡述,“一方面指敘事話語的倫理形態:另一方面指使敘事與倫理之間的關系更加本質和合乎文法的敘事形式。”[5]8-17在國內最早使用“敘事倫理”這一術語的是學者劉小楓,他認為,倫理學有兩種,一種是“理性倫理學”,探究生命感覺的個體法則和人的生活應遵循的基本道德觀念,從而制造出一些理則,讓個人隨緣而來的性情通過教育和培育,從而符合這些理則。而另一種倫理學則是“敘事倫理學”,它不探究一般的倫理法則,而是通過個人經歷的敘事提出生命的感覺,營構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6]3在漢語語境的文學研究中,劉小楓的二元分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為清晰的視角來看待文學作品中的敘事倫理,理性倫理學關注道德的普遍情況,敘事倫理學關注道德的特殊狀況,而文學常常就是從特殊敘事中反映出一種普遍的境況。同時著名人文學者徐岱從美學的角度,在《審美正義論 倫理美學基本問題研究》中從廣義角度闡述了“敘事倫理中的‘敘事’主要包括新聞敘事、歷史敘事和藝術敘事三大類,通常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的倫理要求。”[7]183前兩類可以用真實性和客觀化來要求,但是涉及藝術敘事則是更為復雜,徐岱最后給予的觀點是“敘事中所謂的‘倫理’,概括地講也就是一種德性之‘善’的體現。”[7]188但是他存在機械切分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之間界限的嫌疑,因為如若以“敘事功能”來看待文學與歷史,二者之間很難是涇渭分明的分割。在涉及歷史小說題材時,文學性與歷史性之間的關系常常都是論述的重點,祝亞峰認為中國當代歷史小說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敘事特征,從文學敘述的角度可以將之界定為輕逸與沉重,“沉重是從‘真’的角度看取歷史,力主‘真相’的浮現,輕逸則是從‘思’的維面,探尋歷史是怎樣的和可能呈現的面相。”[8]83
從敘事倫理角度來看待《燉馬靴》,它側重從“輕逸”一面探尋人性在那段特殊歷史中可能呈現的面貌。小說講故事的手法是雙重疊加的,父親講述他年輕時經歷的一次戰役,再由“我”轉述父親的故事。這種“講故事”的形式本身就削弱了那段歷史的沉重感,甚至在“我”的轉述中,對于父親反復講述的那場偷襲行動失敗被追逐的經歷提出質疑和不確定性,甚至最后逐漸厭倦了,也是在模糊歷史的“真”。但是對于后半程故事“總能在我心底攪起波瀾。我對后半程的故事永不厭倦,就像對一首喜歡的樂曲,不管循環播放多少次,依然愛聽。”也就是父親所經歷的“再遇瞎眼狼”、“燉馬靴”這兩段故事,在這里“我”以及隱藏于后的作者的情感態度乃至小說本身的價值取向才有所顯露。父親是否最后真的如敵手之愿火葬了他,“父親給出的答案總是模棱兩可的。”因為站在民族國家的角度,給敵手最后人間的溫暖,讓他死得其所,是對戰爭中死去的戰友的背叛。這是民族情感的一種倫理沖突。而在“我”看來最接近答案真相的一次,是父親說:“唉,讓他和那個姑娘的相片一起化成灰,他做鬼也值了吧。”這里沒有對于日本兵的痛恨與控訴,原本中日戰爭時期不可調和的民族矛盾與對立,原本沉重特殊的倫理情感在這里融化為對于人性善意的展現。父親保留了敵手最后生命的尊嚴,這是父親對于生命的尊重,是個人的一種超越民族的道德選擇。遲子建小說中以中日戰爭時期為背景的敘事有很多,最典型的是《偽滿洲國》,她一方面以客觀冷峻的筆墨展示日軍侵華給中國底層民眾造成的苦難生活,另一方面側重于戰爭時期具體的個人經歷,所體現的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善惡抉擇、道德選擇。人與動物,人與環境之間也是有著倫理訴求——萬物有靈且平等。父親與瞎眼狼互救的故事也是父親最開始的善意行為帶來的善果。且不論現實生活中狼性是善還是惡,但是作為小說敘事故事中的主角之一,作者想講述的是,即使人類與動物之間有著物種意義上的差別,但是“至善”這一倫理道德卻是能夠超越生物學意義上的物種限制,成為自然界倫理道德中的首選。
拋開宏大的歷史背景,《燉馬靴》更多體現的是個人的生命體驗,父親所經歷的一次戰役,對于日本兵的復雜情感態度,與瞎眼狼之間的互幫互助這段經歷不僅讓父親也讓“我”領悟到生命的意義所在。正如劉小楓“敘事倫理學”所說,通過個人經歷的敘事提出生命的感覺,營構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燉馬靴》的文本敘事著眼于父親年輕時的一次戰役經歷,父親所在連隊偷襲日軍是敘事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承載作者情感價值表達的一部分,而是后半部分父親與日本兵、瞎眼狼之間的牽連才是文本的主體,同時也是作者思想情感表達的載體,父親與日本兵之間的民族情感倫理的道德選擇,與瞎眼狼之間的善意互救,在這種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營構的背后,體現的是遲子建個人的一種獨特的敘事倫理,也就是一種人性之善的選擇,與徐岱的敘事倫理“德性之善”有著不同程度上的契合。這種敘事看似圍繞個人命運,實際上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民族國家之間,應該以怎樣的情感態度面對歷史遺留的種種問題?人與自然環境之間,又應該以怎樣的原則和諧相處?遲子建通過這部短篇小說傳遞出她的情感態度,即萬物有靈且平等,需善待生命。
短篇小說就像一個舞者在小小的圓桌上翩翩起舞,跳好很難。遲子建筆下的《燉馬靴》則是通過敘述者、敘事空間、敘事意象、敘事倫理四個支撐點,為我們講述了一個時間上遙遠卻又發人深省的故事。從敘事學角度來看,它一方面體現了遲子建作為一個小說家在短篇上日臻成熟的創作藝術,另一方面也延續著遲子建一直以來的文學理念,即絕境中不失希望與溫情,萬物有靈且平等的人道主義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