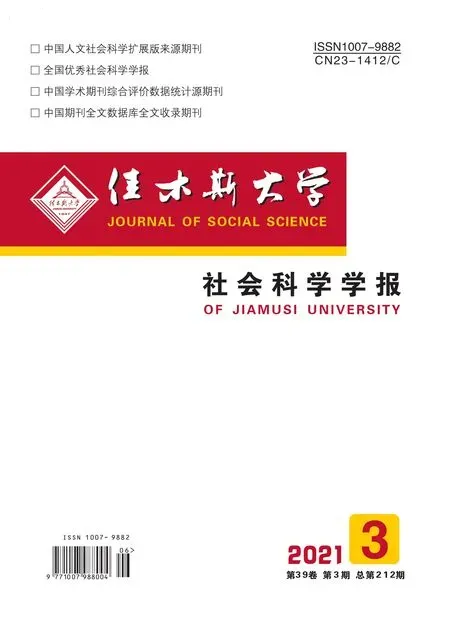記憶詩學視域下《祝福》再闡釋*
李梟銀
(上海大學 文學院,上海 200444 )
從記憶詩學角度對《祝福》的考察可以分為兩個步驟。首先,是基于文本細讀的方法,對主人公祥林嫂的精神記憶展開分析。其次,是基于祥林嫂的記憶現象的分析基礎上,對《祝福》文本所建構起的社會記憶(或集體記憶)的文化意義進行考察。這一分析策略是基于對《祝福》文本本體的尊重:它首先是文學文本,其次才是作為具有社會性的文學文本,換言之,這里所預設的大前提是:《祝福》文本的社會影響生成是建基于它高超的文學成就。此考察的目的是為了對《祝福》的闡釋增添新視角和具有說服力的話語,進而使這一經典性文本的當代影響能夠可持續進行。
一、祥林嫂人格結構分析
從記憶詩學的角度進行《祝福》文本展開闡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首選方法,因為《祝福》是關于祥林嫂悲劇的故事,因而考察祥林嫂悲劇的生成不能不對祥林嫂本人進行分析,特別是關乎其心理的精神分析。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我們可以發現祥林嫂內心深處一個病態的循環怪圈。
“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1]77-78——“本我”意義上的祥林嫂。弗洛伊德認為“本我”(ID,有直譯為“伊德”)是人格結構的第一層,他這樣論到:“伊德完全不懂什么是價值、什么是善惡和什么是道德。與快樂原 則如此緊密相連的效益因素,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叫數量因素,支配著伊德所有的活動。本能發泄總是在尋找出路,在我們看來,這就是伊德的全部內容。”[2]129從中可以發現,“本我”的本質屬性有三:其一,是無外在的價值判斷,即“本我”的運行是在潛意識的催動下自發產生的;其二,是追求“快樂原則”,從這一原則出發,可以理解為“本我”是趨利避害的;其三,“本我”是需要發泄的,它不安于隱秘的狀態,總是試圖進入“自我”狀態或直接作用于現實生活。那么,祥林嫂的“本我”是怎樣的呢?從單純的文本內容中,我們很難從“性”或“力比多”的角度發掘祥林嫂的“本我”,但是從祥林嫂一些“出格”或者“沖動”行為中,可以歸納出隱含于文本中的關于祥林嫂“本我”的部分特征。文中最明顯的一處就是當祥林嫂的婆婆準備將她嫁到賀家墺時,祥林嫂的表現是“一路只是嚎,罵”,她是被“用繩子一捆,塞在花轎里,抬到男家,捺上花轎”,最后是“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這一系列行為都體現出祥林嫂對于再婚的抗拒,這不是基于現實原則下的行動,卻恰恰是在“快樂原則”驅動下的沖動,盡管她的行為造成了她身體的傷害,但從心理的角度上說這是祥林嫂趨利避害的選擇。文中還有一處“非白”值得注意,即第一次祥林嫂到魯四老爺當女工是背著婆婆逃出來的。敘述者沒有交代她為什么逃出來,只是說她有一個“嚴厲的婆婆”。綜合上述兩件事,不難發現反抗是祥林嫂最重要的“本我”邏輯:她反抗婆家因而選擇逃離,她反抗婚姻因而大哭大鬧,所有的反抗所追求的僅僅祥林嫂想象意義上的快樂,盡管她的反抗都以失敗告終,并且給自己增添了更大的創傷。
“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自我”意義上的祥林嫂。“自我”(Ego)是人格結構的中間部分,“通過知覺意識的中介而為外部世界的直接影響所改變的本我的一部分”[3]173。與“本我”的無意識催動不同,“自我”是意識活動的產物,它的形成與社會教育、制度、法則等多重規定密切相關,它遵循的是現實原則。在此基礎上,人格結構的第一個矛盾便出現了:社會性的外力在相關程度上必然與“本我”的天性發生抵牾,此時也就出現了意識的“壓抑”,那些與“力比多”有關的或羞恥或亂倫或與社會法則不符的意識便內化為潛意識。由此觀照文本,可以發現祥林嫂在一定程度上是處于壓抑狀態,一個表征便是祥林嫂是趨于沉默的,當她第一次來魯四老爺家,便表現出“只是順著眼,不開一句口” ,后文直接描述到,“她不很愛說話,別人問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然而,此時祥林嫂的“本我”是處于“自我”的有效管理下的,二者的關系還是平衡的,這表現在祥林嫂在日常生活中十分能干,在忙碌的勞動中她卻感到一絲滿足,不僅僅是在魯四老爺家,之后嫁到賀家墺后,文本中還是用一個“胖”描述她,“母親也胖,兒子也胖;上頭又沒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氣,會做活……”。不難推斷出,祥林嫂“自我”遵循的現實原極為簡單,她所需要的僅僅是勞動的空間與勞動的條件,在勞動中她便處于一種滿足、健康狀態。
“早飯之后,她便到鎮的西頭的土地廟里去求捐門檻”——“超我”意義上的祥林嫂。“超我”(Super—ego)是人格結構的最高一層,是具有理想意義的“我”的存在形態,它遵循的是道德原則。然而,盡管“超我”是“自我”意義上的升華,但是這樣一種典范形態卻是基于社會文化認同,換而言之“超我”是具有社會性的,它是一定文化語境的產物。“超我”一方面勉勵著“自我”,一方面又嚴格約束著“自我”。在祥林嫂所處的社會大背景下,她的“超我”呈現怎樣的形態呢?在祥林嫂第二次到魯四老爺家時,魯四老爺曾這樣告誡四嬸:“這種人雖然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的,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時候可用不著她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干不凈,祖宗是不吃的”,這里的“不干不凈”極具深意,通過它可以去理解祥林嫂的“超我”:作一個“干凈”的人。這樣一個“超我”的形成,將其歸納為封建文化中對女性三從四德的規約,是耳濡目染的貞操觀念使然,是符合邏輯的闡釋。因此,當婆婆將她再嫁時,她竭力反抗。當聽到柳媽關于“陰司”“閻羅大王”的描繪時,她便急著去捐門檻。“干凈”就是祥林嫂理想的祈求,但是在婆婆的逼迫、魯四老爺的“祖宗文化”中,她的“超我”的規定性打破。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結合上文論述,祥林嫂“本我”意識中的反抗、求生原則,竟是趨向“超我”的方向,由此形成了病態的人格怪圈:追求的目標迫使她反抗,而她所反抗的方向卻是追求的目標。她的反抗不是向著生命本真的自由方向,而是趨向于迫害的方向。道德化的“超我”與本能化的“自我”趨同,這是祥林嫂真正麻木的體現,她的行為看似自主,實則是背后文化大手的推動,她無能為力,在有限的行動中,不斷加重自己的病態。
二、祥林嫂的創傷經歷與記憶扭曲
人格結構的病態對祥林嫂而言是隱性的,若是沒有突發事件,這病態或許將永遠潛伏在祥林嫂的無意識中。然而,祥林嫂之所以是“祥林嫂”,并不僅僅是人格結構中的病態,她的不幸在于她的遭遇,李長之說《祝福》“主要的故事,只有兩點,一是再嫁,一是喪子”[4]88。他的歸納頗為精準,圍繞“再嫁”和“喪子”,系列創傷襲向祥林嫂,它直接導致了祥林嫂記憶扭曲。正如創傷研究學者凱如斯指出:“在突然的,或災難的事件面前,一種壓倒性的經驗,對這些事件的反應通常是延遲的,以幻覺和其他侵入的現象而重復出現的無法控制的表現”[5]11。因此,對祥林嫂的精神分析另一個重要切口,是對她的創傷經歷展開解讀,由此分析其精神記憶扭曲的諸種不同形態,進而歸納出它們所生成的文本效果。
就祥林嫂的創傷經歷而言,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物質性創傷和精神性創傷。她的物質性創傷集中體現在“再嫁”情節中。因祥林嫂對再嫁的反抗,“她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這是最明顯的物質性創傷,盡管文中沒有交代后文中祥林嫂的“傻”、“瘋”與這次傷害的直接聯系,但是,這必然對祥林嫂日后精神的失常產生潛在的影響。然而,這樣一次物質性創傷對于祥林嫂而言只是一次“意外”嗎?如果她在再嫁的過程中沒有極力反抗,或許可以避免?這樣的假設是不符合人物真實性的:祥林嫂“超我”結構就是當時特定文化熏陶下的道德化“自我”,強烈的女子貞操意識驅動她必須全力反抗。盡管物質性創傷對于祥林嫂的傷害是嚴重的,但是伴隨著身體的康復,它并沒有顯性、直接地對祥林嫂的生活造成影響,文本中衛老婆子的言語可以佐證:“后來?——起來了。她到年底就生出一個孩子,男的,新年就兩歲了……哎哎,她現在是交了好運了。”可以說,祥林嫂最大的創傷是精神性的,在文本中至少可以發現四處:1.被婆家抓走時的恐懼;2.不準祥林嫂參與祭祀;3.魯鎮民眾對祥林嫂的冷漠;4.“我”回答祥林嫂有鬼魂、地獄的存在。
這里只是從論證角度按照時間先后順序列舉出文本中祥林嫂所經歷的創傷,嚴格地說,祥林嫂的記憶扭曲與創傷經歷形成不是線性發生的,毋寧說這是一個“創傷的循環”:經受創傷,導致記憶失常;記憶失常,回應著新的創傷,在系列的循環中一步步逼向精神的極限。祥林嫂記憶扭曲體現在兩個方面,即反復回憶與日常健忘,并且二者具有深刻的文本意義,記憶扭曲不是簡單的“跡象”或“情報”,而是發揮著“核心”作用。因為反復回憶,“我真傻,真的”成為祥林嫂的口頭禪,并且逢人就訴說她喪子的經歷,這樣一種獨白,“侵犯了別人的生活秩序……是一種跟一般人的生活秩序的斷裂,威脅別人的約定俗成的秩序”[6]30-36,由此祥林嫂被排除在魯鎮群體之外;更為重要的是,魯鎮民眾這樣一種取樂或拒絕的態度,使得祥林嫂移情的宣泄方式失敗,“……自己再也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她單是瞥他們一眼,并不回答一句話”,她徹底陷入壓抑之中。另一方面,因為日常健忘,祥林嫂在魯四老爺家的幫工越來越差,“不半年,頭發也花白起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于常常忘卻了去淘米”。正因為如此,祥林嫂終于被趕出魯四老爺家,成為魯鎮上無家可歸的乞丐,漸漸走向死亡。
三、祥林嫂的死因及其文化意義
學者殷鼎曾采用結構主義敘事學分析方法研究《祝福》,認為該文本“作為一個以不完全的形式進行的句子的文本,其結構如下:她的死(主語)乃由……造成。”[7]26-33因此,文本中每一次關于祥林嫂的創傷事件,都可以作為謂語之一,補充著謂語部分,使得這一句型完整化。但是,作者魯迅的高明之處就在于,這個謂語不是單一的,毋寧說謂語是以復數形式呈現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我們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性回答。
首先,是“祥林嫂自己”殺死祥林嫂的。我們可以假設,若她是一個樂天派,是一個無所知的人,一切得過且過,不去考慮“陰間”的遭際,祥林嫂是不會死去的。她的死,在于精神的“未完全麻木”,但這“未完全麻木”卻是浸透在精神的“絕對麻木”之中,這便是“本我”與“超我”之間深刻的矛盾。弗洛伊德論到,“可憐的‘自我’卻處境更壞,它服侍著三個嚴厲的主人,而且要使它們的要求和需要相互協調。這些要求總是背道而馳似乎常常互不相容,難怪“自我”經常不能完成任務。它的三位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8]86。上文分析到,祥林嫂的“自我”只是希望能夠安穩地勞動,道德化的“超我”驅動她能夠參加如祭祀這樣“重要”的慶典,然而在“自我”求生的原則、快樂原則下,所要反抗的就是“超我”的道德預設。然而,事實卻是外界的創傷使得祥林嫂的“自我”已經傷痕累累,她是一個寡婦、沒了兒子、“不干凈”的人,她是一個自我囈語的“瘋子”。這種情況下顯示出扭曲的“自我”,導致祥林嫂自己人格的嚴重分裂,“超我”與“本我”的背到而馳。終于,在經歷著系列的創傷,在“內傷”與“外傷”的雙重打擊下,祥林嫂的精神與身體走向忍耐的極限而死亡。從這個角度而言,祥林嫂首先是被自己殺死的。但這僅僅是問題的表象,在此基礎上,我們應該進一步發問:促使“本我”與“超我”扭曲的推動力是怎樣形成的?為什么沒有可以讓祥林嫂宣泄的途徑?
其次,殺死祥林嫂的是魯鎮上所有人的合謀。這樣的“合謀”,盡管是無意識的,但從客觀效果上而言的確是如此。老監生魯四老爺一開始就嫌棄作為寡婦的祥林嫂,并且定下“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的時候可用不著她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干不凈,祖宗是不吃的”的規矩;作為魯四老爺命令忠實的執行者,四嬸在祥林嫂捐門檻前后都表現出高度一致性,不論是前一次“祥林嫂,你放著罷!”還是“你放著罷,祥林嫂!”,內容一致,所不同的只是情緒更加激動。至于魯鎮其他民眾呢?他們先是對祥林嫂進行“情感消費”,當對祥林嫂的傾訴感到厭倦后,便是挖苦、嘲諷。魯鎮的民眾不僅僅是一般意義的“看客”,他們“看”中透露出的取樂、嫌棄、冷漠,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將祥林嫂推向死亡的邊緣。
最后,還有一位直接的“殺手”,那就是“我”了。錢理群通過分析認為,“我”對于“魯鎮社會”而言是“格格不入”的,“《祝福》中‘我’的‘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模式,只是表明了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中國社會的不相容性,他(他們)注定要扮演永遠的‘游子’(漂泊者)的角色”[9]10-12。然而,正是作為魯鎮社會“異己者”的我,在祥林嫂命懸一線之際,給予她一個大大的推力,使其精神一潰千里。這個推力就是我在吞吞吐吐中對祥林嫂的回答,以猜測的語氣告訴她“人死之后是有魂靈的”“地獄也是有的”。我的一番對話,使得祥林嫂對于死的看法也極為矛盾:在饑寒交迫中無法生存,但是出于對陰間的恐懼,她卻又不敢死,于是乎——她必須死,她又不敢死,祥林嫂一定是在惶恐、孤單中閉上眼睛。這是魯迅最為深刻的地方,他的批判不是外在性的,他將“我”也納入了批判的視野,他在進行全方位的反思。
可以說,《祝福》之中沒有一個人不是兇手,魯四老爺、四嬸、衛老婆子、至于魯鎮上的所有人、“我”、祥林嫂的婆婆、丈夫。“在這篇文字中,憤恨是掩藏了,傷感也是隱忍著,可是抒情的氣息,卻彌散于每一個似乎不帶情感的字面上”[4]90。魯迅的批判是深刻的,從“我”至全方位的魯鎮社會,從人間到地獄。然而,正如李長之所論,這種批判是具有抒情性的,《祝福》之所以是文學文本,是基于魯迅強烈的同情感。如果說,《祝福》書寫的是關于祥林嫂的創傷,那么,魯迅文字中的克制與隱忍,甚至一種虛無感、無力感的建構,凸顯出創傷敘事的深度與廣度,它不是一種簡單的苦難的宣泄、一種“苦難情懷”的販賣,而是一種關于政治、文化乃至“人”生存問題的叩問與反思。例如,有學者認為《祝福》是對封建制度的揭露,它體現出“封建的政權、族權、夫權、神權這四大繩索編織成的嚴密的網”[10]71;也有學者認為,“魯迅其實是以祥林嫂的遭遇為結構中心,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以儒釋道三教構成的‘魯鎮社會’將她逐漸吞噬的清晰過程和思想圖景,并通過祥林嫂的‘被吃’,宣判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死刑”[11]18-24。
四、作為集體記憶的祥林嫂
《祝福》一文寫于1924年2月7日,同年3月25日刊登于《東方雜志》。伴隨著1926年9月30日《世界日報副刊》中《痛讀<彷徨>》中首次涉及關于《祝福》的評論,圍繞《祝福》或祥林嫂的“接受/闡釋”系統漸漸形成。在這其中,對《祝福》接受產生較大影響的有兩個事件:其一,是1950年《祝福》首次編入語文教材,此后一直保留;其二,是1956年為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由夏衍改編的電影《祝福》正式上映,《祝福》的圖像化傳播時代開啟。誠然,《祝福》的接受與闡釋因具體社會語境的變遷而顯示出差異性,其中滲透著諸多話語權力的博弈,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文學現實是:《祝福》的經典性已得到社會認同,“祥林嫂”已經成為所指豐富的意義符號,從這個角度而言,祥林嫂形塑著獨特的“中國記憶”,這樣一種記憶是具有集體性質的,因而也可以稱之為集體記憶。集體記憶對于特定社會的認同感、凝聚力建構是極為重要的,“事實上,如果人們不講述他們過去的事情,也就無法對之進行思考。而一旦講述了一些東西,也就意味著在同一個觀念體系中把我們的觀點和我們所屬圈子的觀點聯系了起來”[12]94。基于此,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的是,在當代語境中,祥林嫂作為集體記憶的一個部分的存在意義是什么?或者這個問題,還關系到《祝福》文本經典性的持續問題。筆者以為,這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思考。
第一,是文化反思的督促。反思是一個有別于記憶與回憶的思維過程,如果說記憶是對過去的客觀化再現,要求是精準的還原,那么記憶是不具有感情色彩的,它具有一定的工具性質;回憶則是主觀性地思維過去的切身經歷過的人或事,因而回憶對于現實而言有可能是失真的,它是“主觀真實”、“主觀滿足”。對于反思而言,我們可以理解為“折返性思考”,返回 “過去”,這里的“過去”,不僅僅是“記憶”與“回憶”中的某一類型,寧毋說是二者兼有之,返回事件本身,返回闡釋的歷史,在此基礎上,結合當下語境進行“思”。《祝福》的悲劇性是公認的,魯迅在進行關于祥林嫂的創傷敘事時,其實無意中為民族的文化增添了一道創傷。這道關于文化的創傷是明顯的,它讓接受者看到了在曾經的一個文化悲劇的時代:對婦女的壓迫,對小人物的摧殘,其中的人物都在無意識地“殺人”,并且一個個都是基于對文化正統認同的合法性想象。因而,反思應當是對待《祝福》文本一個永恒的姿態:是什么造就了祥林嫂的悲劇?祥林嫂式的悲劇及其變形在當代社會還會發生嗎?唯有如此,在反思性立場下民族文化才有可能保證活力地、健康地向前發展。
第二,是底層關懷的表征。這是基于魯迅的寫作立場而言的,他筆下的小人物:阿Q、祥林嫂、閏土等總是具有鮮明的典型性,而這與作家本人強烈的關懷意識密切相關。正如上文分析到,《祝福》之中魯迅飽含著同情、也飽含著憤與怨,但是他卻隱忍著,沒有強烈表現在文本中,顯示出一種言外之味。有學者認為,《祝福》文本中的“我”隱約象征著1924年初魯迅自我生命危急與反省,他“承載的正是魯迅審視中國新型知識分子以及審視自我生存危機的苛毒眼光”[13]185-198,這在《祝福》文本中體現在“我”的思想中:一方面,“我”急迫地想要離開魯鎮;另一方面,我也感到無聊,想象著魚翅、想象著醉飲。那么,結合魯迅當時的生命狀態:一個人在苦悶與彷徨之中寫下的文字,一定是最真實的,它是一種無力的發泄,是靈魂深處的流露。因此,此時的魯迅以“祥林嫂”為中心,通過一個女人的創傷與生死,進行全方位的魯鎮批判,凸顯心系底層人物的深刻情感。“《祝福》這樣的作品,是他精神的注腳。那立場,就完全是民間的。……這種從弱小者的愛欲里思考問題的姿態,是本然的反應,可是沒有幾個讀書人意識到了這些。”[14]8這應當是對當下文學創作的又一個啟示,在城市化、“加速”社會的語境下,是否有一些被遺忘的小人物?他們或在農村,或在城市的最底層。從這個角度而言,魯迅的確還活著,《祝福》折射出的底層關懷,是每個時代文學精神不可或缺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