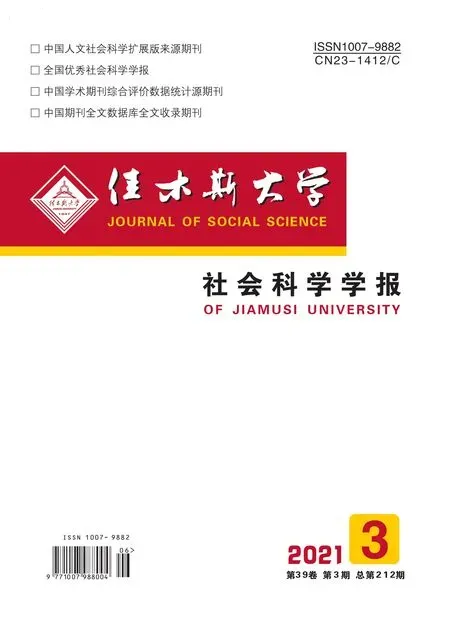魏晉南北朝官修圖書編撰初探*
曹文怡
(南寧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0)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圖書編撰興盛原因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圖書編撰業的重要發展階段,涌現了大批優秀的圖書編撰家,回顧這一時期的圖書史,可以算得上是大起大落。魏晉南北朝各代普遍重視文學發展,社會上層包括帝王在內,熱衷于文學創作。與此同時文學批評領域也取得了顯著成就,出現了諸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鐘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等優秀作品。然而三國混戰、南北割裂、社會動蕩不安,以及朝代的更替頻繁,導致圖書編撰事業失去了良好的發展環境,“永嘉之亂”和“蕭繹焚書”更是給了圖書業一記重擊。但即便是遭遇了這樣的打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圖書業仍然算是繁榮興盛。理由主要有四點:
(一)思想的解放
東漢末年漢靈帝廣招有才藝之士、置鴻都門學,逐漸弱化儒學的地位,扭轉了東漢以來“一說經至萬言”的繁瑣、浮華風氣。社會風尚轉向重視詩賦、小文的創作領域。此外魏晉士族為了穩固世家地位,沿續了前代以來儒學式微的狀態,開始逐步發展玄學思想。而對于普通的小家族來說,由儒入玄成為了躋入士流、增進家族地位的重要手段。綜合整個社會層面來看,儒學、玄學、佛學、道學思想在這一時期皆有其發展平臺,因而文學種類樣式繁多,各類著述圖書皆有人著寫。
(二)南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火紛飛、災難連連,百姓被迫背井離鄉、四處遷徙,來自各地的百姓匯聚到一起,彼此之間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也促進了圖書編撰出版業的發展。雖然南北分裂、山河隔絕,但是南北不時遣使來往修書交好,因而南北間百姓互通友好,文化也交匯融合。政治上北魏孝文帝改革、各族人民接連起義、少數民族與漢族人民錯居雜處,使得少數民族人民受到漢文化影響的同時,漢文化也接納了少數民族的文化思想。簡而言之,這一時期的文化是在以漢文化為核心的基礎上,吸收了南北方地區思想以及外來文化思想,促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更具魅力。
(三)統治者的重視
這一時期的統治者普遍重視文學發展。北魏孝文帝曹丕曾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1]2271又云:“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2]88,劉宋時期“宋代文學之盛,實由在上者之提倡”[3]73。到了梁朝,梁武帝蕭繹崇尚文學,“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4]517,蕭繹不光自己喜愛讀書,還重視興辦學校,不過學校錄取的學生僅限于貴族“胄子”。上層的重視激發了下層文人的創作熱情,因而這一時期的圖書數量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
(四)紙張的興起
紙張應用于圖書業最早出現在漢末,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促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圖書業發展。三國時期,由于漢末的紛爭混亂,社會生產緩慢,紙張的制造數量低,只能滿足一部分人的需要,因而使用率并不高,竹簡和帛書仍然是圖書編撰出版的重要方式。直至兩晉時期,紙張逐漸普及,東晉時期編撰出版的圖書如《晉書》《華陽國志》《姓氏簿狀》等證實了當時圖書業已經出現了紙張為主、簡帛為輔的局面。西晉左思有云:“豪富之家,竟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5]2377,表明了時人對紙張應用的態度。到了東晉桓玄下令:“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6]517。南北朝時期就到了圖書業的高潮階段,社會穩定、經濟攀升為出版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統治者重視圖書編撰出版、民間文學風氣濃厚,更是促進了這一時期圖書業的磅礴發展。至此紙張的應用已經取得了廣泛的認同與推廣,紙張物美價廉、便于攜帶抄寫,因而取代竹簡和縑帛的地位成為了一種必然趨勢。同時紙張的使用,使得書籍的復本大量增加,圖書的編撰與抄撰的速度更快、圖書規模更大、傳播的也更廣。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圖書編撰類型
(一)魏晉時期的官修機構
東漢時期設立官府專職藏書官員。“恒帝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異同”[7]1106,由此秘書監一職沿襲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同朝代和不同時期,秘書監的職官與職能也不盡相同。三國時魏設立秘書丞,地位僅次于秘書監。魏晉時正式設立秘書郎,主要從事圖書的收藏與抄寫等工作。但秘書監設立后其具體職能一直沒有確定下來,直至魏武帝曹操時才正式確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為監,掌藝文圖籍之事”[8]220。晉武帝時期在中書省下設秘書局和著作局,到了惠帝時“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5]735。簡而言之就是著作局不再歸中書省管轄而轉歸到秘書省管轄。到了南北朝時期,因襲晉制,未有多大改變。“魏、晉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余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9]720。秘書監掌管官府藏書、校讎典籍,經南北朝的完善發展,形成最終的秘書省,所任職人員都是當代著名的文學家,對圖書事業發展具有重大貢獻。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經書
經學自漢代大一統之后,其主流地位便確定了下來。東漢末年儒學衰微,禮分三禮、春秋分三傳、五經變為了九經。經書雖然有了些變化,但時人對經書的注疏卻一直沒有懈怠下來。三國時有王弼注《易》,此后晉代南北朝時也有文士接注《易》:“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系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梁有魏大司農卿董遇注《周易》十卷,魏散騎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亡”[9]909。西晉杜預著《春秋左氏傳集解》《春秋釋例》等:“既立功之后,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5]1031,郭璞注有《爾雅注疏》等:“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于世”[5]1910,范寧撰有《春秋榖梁傳集解》是今存最早的《榖梁傳》注解。“初,寧以春秋谷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5]1989。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書注解極為精妙,當時文士大家所撰的注解直至后世仍奉為經典。除了這些注解書還有一些經部書籍如張揖的《廣雅》、顧野王的《重修玉篇》等也頗負盛名。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史書
統治者們為了總結歷史經驗,以便更好地維護統治,因此令秘書監、著書郎等人參與修撰史書。受詔的官員掌握史閣的官藏文獻,因而內容豐富詳實。
三國時期,魏武帝令史官撰寫了第一部國史《魏書》,據載:“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后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10]346。可知《魏書》的成書歷經多人辛苦修撰。衛覬、繆襲草創,韋誕、應璩、王沈、阮籍、孫該、傅玄等撰定,最后由王沈修撰成書,這也是三國時期最有名的官修史書。此外吳國太史令受詔修撰的《吳書》:“孫亮即位,為太史令,撰《吳書》孫休踐阼,為博士祭酒”[2]1461,《吳書》歷經修撰者們幾十年的努力,編修者多已逝世,其中韋曜因政治原因被殺,使得該書最終未成。
兩晉時期,官修的晉史有許多家,西晉比較出名的官修史書有:佐著作郎王沈等人受詔編撰《晉書》:“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5]1432,秘書丞司馬彪撰的《九州春秋》:“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5]2141,王沈撰《魏書》:“正元中,遷散騎常侍,典著作。與荀顓、阮籍共撰《魏書》”[5]1143。東晉較出名的官修史書有:著作郎王隱、郭璞等受詔修撰的《晉書》“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5]2143。佐著作郎干寶受詔撰《晉記》:“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5]2150。著作郎謝沈撰《晉書》《后漢書》:“何充、庾冰并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余卷”[5]2152。秘書監孫盛撰《魏氏春秋》、《晉陽秋》:“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5]2148。著作郎徐廣奉敕撰《晉紀》:“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5]2158。
到了南北朝,修撰的史書不單有記錄當時的史書,也有整理三國兩晉時期的史書。宋時秘書監謝靈運受詔修撰《晉書》:“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11]1772,裴松之受詔撰《三國志注》:“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11]1701。著作郎何承天等受詔撰《宋書》然而最終未成。齊時王圭之奉敕修撰《齊職儀》:“從弟圭之,有史學,撰《齊職儀》”[12]903。王智深奉敕撰《宋紀》:“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12]897。著作郎王逡之撰《永明起居注》:“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12]902。梁時著作郎沈約奉敕撰《宋書》《齊紀》:“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啟,明帝有敕許焉。自此逾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余卷”[13]1414。吳均奉敕撰《通史》:“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13]1781。蕭子顯撰《后漢書》《齊書》:“子顯所著《后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14]512。梁武帝時期令沈約、周興嗣、鮑行卿、謝吳等人先后執筆修撰《梁書》一百卷,與此同時梁武帝還下令組織史官修撰《通史》。可見這一時期官家對史學的重視。
(四)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子書
1.官修類書
我國古代通過搜集官藏文獻來編輯類書始于曹魏,可以說魏晉南北朝時類書的發展時期,為后世類書編撰定了規矩做了榜樣。
三國時期最有名的類書要數由魏文帝曹丕組織編撰的《皇覽》:“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余萬字”[2]664。一同受詔修撰的還有繆襲、桓范、劉邵、韋誕等,《皇覽》的誕生乃是后世《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等著名類書的先驅。
兩晉時期陸機修撰《要覽》又稱《陸氏要覽》,《舊唐書·經籍志》收錄有三卷,后以佚。
到了南北朝時期,類書發展到了高潮時期。劉葉秋先生評價齊梁時的類書:“自魏文《皇覽》之后,六朝之帝室皇枝,名卿碩彥,靡不延攬文學,抄撰眾籍,而齊梁時尤盛。”[15]8梁武帝承襲魏文帝的方法下詔修撰類書,天監元年劉杳奉敕修撰的梁朝第一部類書《壽光書苑》二百卷。篇幅更大的還有一部由徐勉領修,何思澄、顧協、劉杳、王子云、鐘嶼、徐僧叔等數百人合力修撰的《華林遍略》歷經八年修撰而成,全書七百卷。唐代《藝文類聚》的修撰也是受到該書的影響,可惜到了宋代便已亡佚。此外南朝還有一些名氣較小至今已失傳的官修類書,比如說《新唐書·藝文志》記載的宋何承天并合《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徐爰并合《皇覽》八十四卷。南齊東觀學士奉敕修撰《史林》三十卷,蕭子良領眾學士修撰《四部要略》一千卷。梁朝劉峻撰《類苑》一百二十卷,簡文帝蕭綱令陸罩等人修撰《法寶聯璧》二百卷,陶弘景撰《學苑》一百卷,朱澹遠撰《語對》十卷、《語麗》十卷。北朝時北齊后主高緯下令修撰的著名官修類書《修文殿御覽》,該書以《華林遍略》為藍本,共三百六十卷,由六十余人修撰而成。除此北朝還有北魏崔安撰寫的《帝王集要》三十卷。官修類書的修撰往往需要大量的人才,這一時期的文人皆以參與修撰為榮,學者們修撰官修的熱情帶動了私撰的創作,因而極大地促進了文人創作的積極性,也為圖書編撰事業做出積極貢獻。
2.官修佛教經書
兩漢之際佛教傳入我國,直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才逐步發展起來,寺廟的興建、教義的傳播使得佛教經書也廣為流傳。自北魏起儒教式微,玄學興起,舶來的佛教理論常用老莊思想解釋,佛學與道學的融合造成官修的宗教類經書在這一時期不斷涌現。為了傳入的理論可以閱讀理解,這一時期興起一陣譯經修撰之風,其中官修佛學譯經有《道行品經》《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人本欲生經》《阿彌陀》《大智度論》《百論》《大品般若》《十誦律》《佛藏》《菩薩藏》《法華》《維摩》《金剛》《成實論》《經律異相》《佛所制名數教》《增一法教》《菩薩藏眾經要》《眾經要鈔》等等。由于政府的支持,本國與番邦互通經典,不只有舶來的經典佛學翻譯成漢化,漢化的經典也有翻譯成外語的,例如《涅槃經》等等。
3.官修韻書
韻書是一種按照漢字的聲、韻、調等來分類編排的書籍。目的是分辨規定文字的正確讀音,起到辭書、字典的作用。聲韻之說早已存在,但直到三國時期才真正編書成籍,系統地規范了漢字的音韻。據載,我國最早編撰的韻書是三國曹魏時期李登編撰的《聲類》,唐封演有云:“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16]11,還有西晉呂靜編撰的《韻集》,后世有載:“別仿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17]1963。齊梁時期俗樂興起,“永明聲律”的形成顯現了人們對于聲律之美的追求,在這種條件下,沈約《四聲》、張諒《四聲韻林》、王該《文章音韻》等聲韻類圖書的出現已然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五)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集書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思想和文化思想高度自由,總集和別集的編撰群體數量龐大,加速了這一時期的文學發展,促進文人們走向文化自覺的時代。
1.官修總集
總集的編撰,大多交代了這一時期的作家作品。我國最早的總集就出現在西晉時期。關于總集的源流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總集,《隋書》上有這樣的記載:“總集者,以建安之后,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益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后文集總鈔,作者紀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9]1089。這一時期有名的總集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論》,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5]1427,曹丕的《建安七子集》,蕭統組織修撰的《文選》,都是這一時期極為優秀的總集。此外還有梁武帝時徐陵修撰的《玉臺新詠》。這一時期總集的出現標定了圖書總集編撰的標準,為后代總集提供了參考,影響深遠。
2.官修別集
《隋書·經籍志》中關于別集有這樣的介紹:“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眾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后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為集。辭人景慕,并自記載,以成書部”[9]1081。別集雖成于漢代,但直到晉代才稍成氣候。曹之先生在《章學誠與圖書編撰學》中道:“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于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始仿于晉代”[18]。此外還有“其自制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嵎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于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19]1271。別集的大量修撰也側面促進了總集的修撰,總集與別集的相輔相成,呈現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圖書編撰的鼎盛局面。
(六)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目錄書
我國目錄學書始自西漢劉向的《七略》,自此目錄學在魏晉南北朝得到了充分發展。這一時期的目錄書數量相當可觀,較為有名的有三國鄭默的《魏中經簿》、西晉荀勖的《晉中經簿》、東晉李充的《晉元帝四部書目》、不詳人的《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東晉杜淳的《四部書大目》、南朝謝靈運的《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書目》、南朝王儉的《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南朝劉孝標的《梁天監四年文德殿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等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目錄學著書在數量以及觀念上超越了前代,開啟了將目錄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進行研究的先河。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圖書編撰特點
第一,官修圖書數量、門類較之先秦時代大量增加,這主要歸功于紙張的出現。竹簡、縑帛和紙張都是圖書編撰出版的載體,圖書載體的豐富為圖書編撰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第二,官修圖書編撰受到高度重視,修撰者學術程度高,政府重視圖書編撰,朝廷中專門設立管理圖書編撰、收藏的機構,不僅收藏天下圖書而且還直接參與圖書編撰,比如說秘書監、文林閣、麟趾殿等官修機構的設立。這些機構招納了當時極為優秀的文士,這也是魏晉圖書編撰水準高的原因之一。第三,版本目錄學取得了較大發展。分類學奠基于這一時期,《七錄》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標志。大型官修類書《皇覽》的出現更是促進了后世官修類書如《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等的編撰出版。第四,這一時期官修史書編撰極為興盛。紀傳體史書和斷代史史書均在這一時期產生,“二十五史”中最有名的前四史也是在這一時段產生,其體例與史學思想對后世影響巨大,經學、文學類書籍也愈加繁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