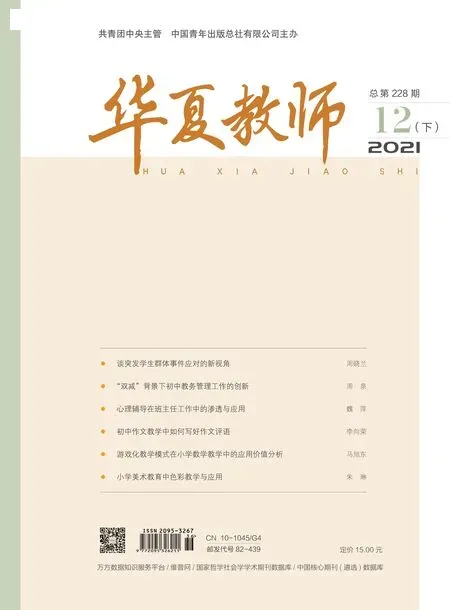詩歌教學的“詩性”回歸
江蘇省泰興市第二高級中學 盧葉青
一、關于“詩性”
“詩性”一般與“詩性智慧”“詩性教學”“詩性閱讀”“詩性教育”等提法一同出現,其共同點均指向感受文本時個體生命的浸潤與體驗,并從中追求一種超越自我的非功利化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在古詩詞教學中,“詩性”包括:詩性感知、詩性語言、詩性想象、詩性創造等,它存在于文本自身、讀者接受文本的過程,以及讀者的后閱讀階段。
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對“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詩性”理解,可以是對“巨浪滔天,滾滾東流”雄奇壯麗畫面的浪漫想象,可以是對“人世滄桑,天地永恒”千古興亡歷史的感慨喟嘆,也可以是“繼往開來,變化輪回”人生哲理的理性思索。所以說,“詩性”是一種通過生命參與獲得詩歌審美體驗的過程與方法。
二、回歸詩性的必要性
(一)詩歌教學的方向偏失
長期以來,詩歌教學本著“考什么”就“講什么”、“怎么考”就“怎么講”的原則,將詩歌教學上成表現手法題、內容概括題、作用分析題、思想感情題,單調乏味的課堂失去了詩詞鑒賞的知識性和趣味性,看似解讀,其實只是教師單向地向學生傳遞自己的閱讀感受,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學生的個體表達和思維的再創造。
詩歌教學呈現出功利化、模式化、技術化的弊端,詩歌鑒賞失去了詩味。對詩歌的考查形式除了題目就是背誦,且背誦直接以記憶為目的,忽視誦讀的過程,大大扼殺了學生學習詩歌的興趣。再加上時空隔閡,審美教育缺失等客觀原因,學生很難將個體經驗代入、嫁接到詩歌中,難以從詩歌中獲得心靈共鳴和情感慰藉,甚至有教師認為詩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只能靠學生感悟,不是老師教出來的。
試想,失去教師精心得法的引導,單憑學生去“意會”,詩歌教學的“詩性”從何而來?
(二)核心素養的內在要求
語文課程十分重視對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弘揚,以拓寬文化視野,增強文化的自覺和自信。詩歌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在弘揚傳統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它短小精悍,卻又凝練雋永,無論是意象的選擇、典故的運用、語言的錘煉,還是透過人、事、景、物傳達的個人真摯情感或對于人生、世界的普遍哲理,都能讓我們跨越時空,感受到作者的才情智慧和歷史文化恒久的魅力,從而在鑒賞詩歌的過程中,掌握祖國語言文字運用的規律,培養形象思維和創新思維,獲得豐富的藝術審美體驗,增強對祖國文化的熱愛和自信。
“中華傳統文化經典研習”學習任務群,要求學生能置身特定的文化場景,用歷史和現代的觀念考察、審視傳統文化經典作品。即通過研習文本語言,對學習過的古代作品進行橫縱聯系,進而在審美鑒賞與創造和文化傳承和理解上體會作品的“精深和豐富”。
(三)詩歌教學的價值旨歸
隨著新課標、新教材、新高考的全面實施,部編教材推薦的古詩文背誦篇目就有72篇,教師如何有效開展詩歌教學,讓學生在詩歌的閱讀、賞析、寫作中,積累古代文化知識,豐富內在性靈;在詩情、詩意、詩味、詩性的的潤澤中懂得詩意棲居,學會悲天憫人;在物我觀照、古今對話中體驗生命的存在,豐富生命的意義、實現生命的超越。這些成了語文教師必須面對的課題。比如詩歌誦讀,有的講究低吟,有的需要淺唱,有的輔以長嘯,這種沉浸式的誦讀有助于在讀者、文本、作者之間產生同頻共振,使詩歌學習富有詩情。
葉圣陶先生提倡的“美讀”就是在誦讀時最大限度地將作者的情感傳達出來。這個過程,教師既需要因勢利導,精心組織,具身示范,也需要注意營造氛圍,啟發想象,加強體驗,真正將詩歌創作的背景、內容、規律和讀者的想象、理解、體驗融為一體,方可教出“詩性”。
三、回歸詩性的途徑
(一)展開想象,在意象組合中營構詩性畫面
意象是蘊含了作者主觀感情的客觀物象,它具體而感性。作者正是將對自然、社會、人生的認識、理解和體驗附著于這些客觀的物象,從而形成內外和諧的詩意之美。
講秦觀《鵲橋仙》一課時,我引導學生這樣展開想象:從“金”“玉”“風”“露”四個意象,體會“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的妙處。引導學生從事物本身的審美屬性出發,挖掘四個意象的特點:“金”“玉”極言其奢侈、珍貴、難得,但所修飾的是轉瞬即逝、不肯停留的“風”和遇光則干、生命苦短的“露”。如此,短暫與珍貴,仙界與凡世,“一”和“無數”之間形成的藝術反差便呈現在學生眼前。這種“一”勝卻“無數”,短暫之于恒久背后巨大的審美空間進一步激發了學生用想象去填補的欲望。
同樣,在張孝祥《念奴嬌·過洞庭》一文中,如果只是背誦而不加以想象,就很難跳出“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的詩句,將西江水、北斗七星、天地萬物這種空間落差巨大的事物連綴起來,從而體會到因讒免官的詩人內心原來依然如此自信豁達,氣勢磅礴。
(二)品味語言,在時空綿延中體會詩性表達
詩是時空的藝術,因其體格之小,注定其內在有無限包容的可能。時空具有綿延性和超越性,既可包容過去,又可突向未來,從而使得詩歌可以借助詩性的表達實現在物我、宇宙之間自由游走。語言是傳達詩性的重要載體,通過對詩歌語言的品味,讀者可以跨越時空,獲得自然、人生、生命、宇宙的超體驗。
如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的內容簡單易懂,但時空綿延下,人作為生命個體的那種渺小感、無力感,以及其背后的曠世孤獨和心靈壓迫,只有通過對語言的不斷吟詠才能理解和體會。
再如蘇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也是將對亡妻悲痛的悼念之情置于“十年”“千里”的時空背景之下。“茫茫”極言時間之渺遠,“無處”極言空間之孤獨,雖說“不思量”,卻是難逃時間“自難忘”,明明要與你“話凄涼”,卻又苦于“無處”,只能遙祭“千里孤墳”。當詩人無法掙脫現實的時空之隔,開始轉向內部世界,以一種超體驗與亡妻“相逢”,可惜相逢的結果是“不識”,明明相愛卻又“不識”,“十年”“千里”背后又怎一個“悲”字了得!
(三)咀嚼涵泳,在理性思索中感悟詩性智慧
意大利學者維柯最早提出“詩性智慧”這個概念,他認為詩性是一種智慧,是人類天性中最為深層的、充滿感情的部分,是人類原初狀態對世界的樸素理解、體驗和認識。這就要求教師在進行詩歌教學時,突破單一的“景——情”這條線,往“景——情——境——理”的深度挖掘,從而引導學生通過詩歌語言、情感的咀嚼涵泳,在領略詩歌內在的深層智慧上走向理性思索,這對于提升學生對古代經典作品的思辨性和創造性大有裨益。
如對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鑒賞,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春江花月夜”美景的欣賞上和對游子思婦相思的感性同情上,要能通過對“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的浸潤遐思走向對時空運動、生命追問、世事變遷、自然永恒等哲學命題的理性思索上。只有如此,自然美景才有了生命的恒久之美,思婦游子才有相思相望的輪回之美。《春江花月夜》才不是一首簡單的寫景抒情的詩歌,而是一首景情境理兼備的哲理詩,才配得上“孤篇壓全唐”的贊譽。
總之,詩歌教學要改變以往的痼疾,就要更新理念,以培養人、發展人為目標,通過誦讀、品析、鑒賞等途徑,在意象、語言、思辨中涵養詩性,這樣學生才能體會到詩歌的文本之美、情感之美、意境之美、詩性之美,只有這樣,才是詩歌教學的本真價值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