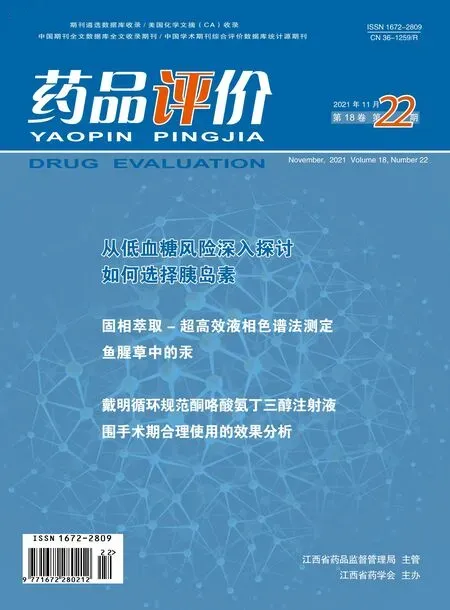從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深入探討如何選擇胰島素
沈建國(guó)
浙江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附屬第一醫(yī)院,浙江 杭州 310003
自1923年第一支胰島素上市,已近百年。胰島素制劑不斷發(fā)展,從動(dòng)物胰島素到人胰島素,再到胰島素類(lèi)似物。雖然新型降糖藥物層出不窮,但胰島素仍是有效降低糖化血紅蛋白(glycated hemoglobin A1c,HbA1c)水平的藥物,可降低HbA1c 水平1.5%~3.5%[1],且隨著病情進(jìn)展,胰島β 細(xì)胞功能逐漸減退,胰島素治療亦是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高血糖管理的重要手段[2],在T2DM 患者降糖管理中仍占有重要地位[3-5]。《中國(guó)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建議,若T2DM 患者在生活方式和口服降糖藥聯(lián)合治療的基礎(chǔ)上,血糖仍未達(dá)標(biāo),建議盡早(3 個(gè)月)開(kāi)始胰島素治療,通常建議選擇基礎(chǔ)胰島素[3]。MOTIV 研究[6]顯示,起始胰島素治療時(shí)的病程越短,HbA1c 達(dá)標(biāo)率越高,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越小。
然而,根據(jù)一項(xiàng)基于我國(guó)T2DM 患者基礎(chǔ)胰島素應(yīng)用的真實(shí)世界研究——ORBIT 研究,我國(guó)T2DM 患者起始基礎(chǔ)胰島素治療時(shí)機(jī)普遍較晚,且存在起始劑量偏低以及調(diào)整劑量不積極等問(wèn)題[7]。臨床中,低血糖是血糖控制的主要挑戰(zhàn),大多數(shù)糖尿病患者因恐懼低血糖而不愿使用胰島素,導(dǎo)致胰島素起始延遲[8-9]。此外,有調(diào)查顯示,約有80%的臨床醫(yī)師表示因?qū)Φ脱堑膿?dān)憂而不能積極調(diào)整胰島素劑量[10]。因此,應(yīng)加深廣大臨床醫(yī)師和患者對(duì)低血糖的認(rèn)識(shí),充分了解胰島素的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進(jìn)而合理選擇胰島素治療方案及胰島素制劑。
1 低血糖的診斷
1.1 低血糖引起機(jī)體的病理生理變化
加深對(duì)低血糖的認(rèn)識(shí),首先應(yīng)了解機(jī)體內(nèi)血糖調(diào)節(jié)的機(jī)制。正常情況下,血糖的來(lái)源與去路存在動(dòng)態(tài)平衡,在一定范圍內(nèi)上下波動(dòng)。體內(nèi)多個(gè)組織器官所分泌的多種激素共同參與了糖代謝的調(diào)節(jié),維持血糖的相對(duì)穩(wěn)定。當(dāng)血糖水平較低時(shí),這些激素會(huì)發(fā)生一系列錯(cuò)綜復(fù)雜的病理生理變化以促進(jìn)血糖升高[11]。
人體內(nèi)的降糖激素主要為胰島素,其通過(guò)促進(jìn)組織對(duì)葡萄糖的攝取,增加葡萄糖的利用,抑制糖原分解和糖異生,減少葡萄糖的產(chǎn)生,從而降低血糖水平。隨著血糖水平逐漸降至6 mmol/L 以下時(shí),胰腺分泌胰島素逐漸減少,當(dāng)血糖水平降至4.6 mmol/L 以下時(shí),會(huì)產(chǎn)生內(nèi)源性胰島素的抑制作用。人體內(nèi)存在多種升糖激素,主要包括胰高血糖素、腎上腺素、生長(zhǎng)激素、皮質(zhì)醇等。當(dāng)血糖水平進(jìn)一步下降時(shí),以上升糖激素的分泌明顯增加,并通過(guò)多種途徑最終引起血糖升高以維持血糖的穩(wěn)定。當(dāng)血糖降低至3.6~3.9 mmol/L 時(shí),釋放反調(diào)節(jié)激素,包括胰高血糖素和腎上腺素分泌。胰高血糖素分泌刺激肝內(nèi)糖原分解(糖原分解)和糖異生(從非碳水化合物來(lái)源生成葡萄糖),腎上腺素可促進(jìn)肝糖原分解和肝臟與腎臟的糖異生[11]。
在對(duì)血糖調(diào)節(jié)機(jī)制的認(rèn)識(shí)日益清晰之后,一個(gè)新的問(wèn)題浮現(xiàn)出來(lái)——何為低血糖?2005年美國(guó)糖尿病學(xué)會(huì)(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ADA)低血糖工作組首先提出,應(yīng)依據(jù)升糖激素的釋放閾值,將3.9 mmol/L 作為低血糖的診斷界值[12]。然而,以反向調(diào)節(jié)激素的釋放閾值定義低血糖似乎并不合理,其原因有以下幾點(diǎn):第一,在使用磺脲類(lèi)藥物及胰島素治療的糖尿病患者中,升糖激素的釋放閾值并不固定;第二,在不同血糖控制水平的患者中,低血糖反向調(diào)節(jié)的閾值不同;第三,即使對(duì)于糖尿病患者個(gè)體,波動(dòng)的HbA1c 水平及既往低血糖病史也可引起低血糖反向調(diào)節(jié)閾值的變化[13]。基于以上原因,包括歐洲藥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EMA);加拿大糖尿病學(xué)會(huì)(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CDA);美國(guó)臨床內(nèi)分泌醫(yī)師學(xué)會(huì)(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ists,AACE);國(guó)際糖尿病聯(lián)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IDF)在內(nèi)的各權(quán)威機(jī)構(gòu)紛紛提出對(duì)于低血糖定義的不同推薦意見(jiàn),由此引起臨床研究中低血糖定義的廣泛差異,導(dǎo)致各研究之間無(wú)法進(jìn)行橫向比較,極大影響了糖尿病領(lǐng)域臨床研究的臨床價(jià)值[14-17]。因此,達(dá)成對(duì)低血糖定義的共識(shí),統(tǒng)一低血糖的診斷界值有著重要的臨床意義。
1.2 低血糖診斷界值
2013年成立的國(guó)際低血糖研究組(International Hypoglycaemia Study Group,IHSG)進(jìn)而重新評(píng)估了不同低血糖診斷界值的臨床意義。研究發(fā)現(xiàn),并無(wú)證據(jù)顯示血糖水平低于3.9 mmol/L 會(huì)造成患者生活質(zhì)量的明顯下降以及健康和經(jīng)濟(jì)的負(fù)擔(dān)加重,而當(dāng)血糖水平低于3.0 mmol/L 不僅與患者認(rèn)知受損、心律失常的風(fēng)險(xiǎn)增加顯著相關(guān)[18-19],并且可顯著增加患者的全因死亡風(fēng)險(xiǎn)達(dá)93%[20]。基于以上研究結(jié)果,2017年ISGH 聯(lián)合ADA、歐洲糖尿病研究協(xié)會(huì)(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Diabetes,EASD)提出,臨床實(shí)踐中低血糖可劃分為三級(jí):(1)升糖激素反向調(diào)節(jié)低血糖的釋放閾值3.9 mmol/L 為一級(jí)低血糖的界值,其臨床意義僅作為低血糖的警戒值,如無(wú)特殊研究目的,無(wú)需在臨床研究中進(jìn)行報(bào)告;(2)血糖水平低于3.0 mmol/L為具有臨床意義的低血糖,推薦在臨床研究中進(jìn)行報(bào)告;(3)三級(jí)低血糖為嚴(yán)重低血糖,無(wú)明確血糖界值,其定義為重度認(rèn)知障礙且需要他人協(xié)助的低血糖[21]。根據(jù)IHSG 低血糖的定義,對(duì)在1 型糖尿病(T1DM)和T2DM 患者中進(jìn)行的為期64 周、雙盲、治療達(dá)標(biāo)研究(SWITCH 1、SWITCH 2)的數(shù)據(jù)進(jìn)行事后分析。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隨著低血糖診斷界值逐漸降低,德谷胰島素與甘精胰島素U100 的低血糖估計(jì)率比逐漸降低,提示兩種基礎(chǔ)胰島素的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的差異逐漸增加,直至3.0 mmol/L。提示該界值可以識(shí)別兩種基礎(chǔ)胰島素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的差別[22]。該推薦意見(jiàn)已得到包括中華醫(yī)學(xué)會(huì)糖尿病學(xué)分會(huì)(Chinese Diabetes Society,CDS)、AACE、IDF 等眾多權(quán)威機(jī)構(gòu)的認(rèn)可,各機(jī)構(gòu)目前均已修訂相應(yīng)指南,以3.0 mmol/L 作為具有臨床意義的低血糖的診斷界值[23]。2019年糖尿病先進(jìn)技術(shù)與治療國(guó)際會(huì)議(advanced technologies &treatments for diabetes,ATTD)共識(shí)對(duì)糖尿病人群基于持續(xù)葡萄糖監(jiān)測(cè)(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CGM)的控制目標(biāo)做出明確闡述,推薦以3.0 mmol/L 作為低血糖診斷界值以評(píng)估葡萄糖低于目標(biāo)范圍時(shí)間(time below rang,TBR),建議TBR 應(yīng)<1%[24]。至此,關(guān)于低血糖的診斷界值已經(jīng)清晰,3.0 mmol/L 作為具有臨床意義的低血糖的診斷界值。
2 低血糖的危害
2 型糖尿病患者中低血糖的發(fā)生率似乎遠(yuǎn)高于預(yù)期,全球大型的關(guān)于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發(fā)生率的非干預(yù)性研究——HAT 研究顯示,在1 個(gè)月的前瞻期中,19.3%的T2DM 患者曾發(fā)生低血糖[25]。而且,T2DM 患者的嚴(yán)重低血糖發(fā)生率亦不容樂(lè)觀,發(fā)生率可高達(dá)1.2~5.9/人年[26-28]。此外,低血糖常常較為隱匿,容易被忽視。前瞻性研究發(fā)現(xiàn),47%的T2DM 患者通過(guò)CGM 篩查出未被發(fā)現(xiàn)的低血糖[29];且在CGM 識(shí)別的低血糖事件中,其中高達(dá)83%的低血糖事件未被察覺(jué)[30]。
低血糖可在多個(gè)系統(tǒng)中導(dǎo)致多種近期、遠(yuǎn)期的不良臨床事件發(fā)生[31-33],明顯增加患者的心血管事件發(fā)生風(fēng)險(xiǎn)及全因死亡率[34]。對(duì)英國(guó)臨床實(shí)踐數(shù)據(jù)庫(kù)的分析顯示,出現(xiàn)低血糖的T2DM 患者發(fā)生心血管事件的風(fēng)險(xiǎn)是無(wú)低血糖的T2DM 患者的1.49倍(95%CI1.23~1.82),全因死亡率為無(wú)低血糖的T2DM 患者的2.48 倍(95%CI2.21~2.79)[35]。而對(duì)世界衛(wèi)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死亡數(shù)據(jù)庫(kù)分析顯示,近年來(lái)低血糖相關(guān)死亡率逐年升高,2014年低血糖相關(guān)年齡標(biāo)化死亡率相較于2000年增加了51%[36]。
3 減少低血糖策略的深入探索
如何權(quán)衡降糖治療帶來(lái)的獲益與低血糖的風(fēng)險(xiǎn)是制定減少低血糖策略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說(shuō),降低多少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才具有臨床意義?為此,2005年ADA 低血糖工作組的共識(shí)指出,嚴(yán)重低血糖(需要他人協(xié)助)風(fēng)險(xiǎn)顯著降低10%~20%,非嚴(yán)重低血糖(<3.9 mmol/L)風(fēng)險(xiǎn)顯著降低30%,則被認(rèn)為具有臨床意義。其中,這個(gè)“風(fēng)險(xiǎn)”可定義為發(fā)生低血糖的患者數(shù)量,也可被定義為患者發(fā)生低血糖的次數(shù)[12]。隨著CGM 的發(fā)展,2019年ATTD 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提出了一個(gè)新的答案,成人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目標(biāo)范圍時(shí)間(time in range,TIR)每增加5%被認(rèn)為會(huì)帶來(lái)顯著的臨床獲益,或以3.9 mmol/L 為截止點(diǎn)的TBR 小于4%,或以3.0 mmol/L 為截止點(diǎn)的TBR 小于1%,具有臨床意義[24]。SWITCH PRO研究顯示,德谷胰島素相比于甘精胰島素U100,其TIR 更高,增加了20.6 min/d,且德谷胰島素組達(dá)到臨床顯著意義的≥5%TIR 變化的患者比例更多,1 級(jí)夜間TBR(<3.9 mmol/L)更優(yōu)(P<0.05),2 級(jí)夜間TBR(<3.0mmol/L)更優(yōu)(P<0.05)[37]。
臨床策略方面,臨床醫(yī)師應(yīng)充分考慮患者的危險(xiǎn)因素,并提供相應(yīng)的健康教育,制定HbA1c控制目標(biāo)且不引起低血糖;對(duì)于需使用胰島素的患者,首選胰島素類(lèi)似物,并輔以胰島素泵及CGM等設(shè)備的應(yīng)用[38]。長(zhǎng)效胰島素類(lèi)似物在人胰島素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修飾,經(jīng)皮下注射后能更好地模擬生理基礎(chǔ)胰島素作用,低血糖發(fā)生風(fēng)險(xiǎn)較中性魚(yú)精蛋白鋅胰島素(neutral protamine hagedorn,NPH)明顯降低[5],可顯著降低總體確證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夜間確證的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嚴(yán)重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39-42]。DEVOTE 研究證實(shí)了德谷胰島素在低血糖方面的優(yōu)勢(shì)。研究結(jié)果顯示,與甘精胰島素U100 組相比,德谷胰島素治療組嚴(yán)重低血糖事發(fā)生率降低40%(RR:0.60,95%CI0.48~0.76)夜間嚴(yán)重低血糖發(fā)生率降低53%(RR:0.47,95%CI0.31~0.73)[41],在中國(guó)人群中也得到了類(lèi)似的結(jié)果。母義明教授等發(fā)現(xiàn),與甘精胰島素U100 組相比,使用德谷胰島素治療的T2DM 患者,夜間確證的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降低57%(P<0.05),HbA1c 達(dá)標(biāo)(<7%)且無(wú)低血糖的患者比例更高(53.1%vs43.1%,P<0.05)[43]。真實(shí)世界研究CONFIRM[44]結(jié)果顯示,治療180 d 后,與甘精胰島素U300 相比,德谷胰島素組低血糖發(fā)生率顯著降低30%(RR:0.70,P<0.05),低血糖發(fā)生患者比例顯著降低36%(RR:0.64,P<0.05)。
此外,德谷胰島素?zé)o論是用于成年T2DM 患者(年齡65 歲以下),還是老年T2DM 患者(65 歲及以上);抑或用于不同病程的T2DM 患者,不同腎功能狀態(tài),有心血管病史的T2DM 患者,德谷胰島素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小的優(yōu)勢(shì)依然存在,仍低于甘精胰島素。
4 結(jié)語(yǔ)
對(duì)低血糖的擔(dān)憂是積極治療糖尿病的重要障礙。胰島素降糖療效明確,在糖尿病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恐懼低血糖事件,部分患者對(duì)胰島素治療存在抵觸心理。因此,克服低血糖帶來(lái)的恐懼,是我們?cè)谶x擇胰島素治療中不得不面對(duì)的問(wèn)題。多個(gè)權(quán)威機(jī)構(gòu)統(tǒng)一推薦,具有臨床意義的低血糖診斷界值為3.0 mmol/L。長(zhǎng)效胰島素類(lèi)似物能更好地模擬生理基礎(chǔ)胰島素作用,具有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小的優(yōu)勢(shì),其中,德谷胰島素相較于甘精胰島素U100 和U300,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更小,且德谷胰島素在增加TIR、減少TBR 方面,優(yōu)于甘精胰島素U100,用于年齡≥65 歲,病程>15年,不同腎功能狀態(tài)及心血管病史等人群,低血糖風(fēng)險(xiǎn)小的優(yōu)勢(shì)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