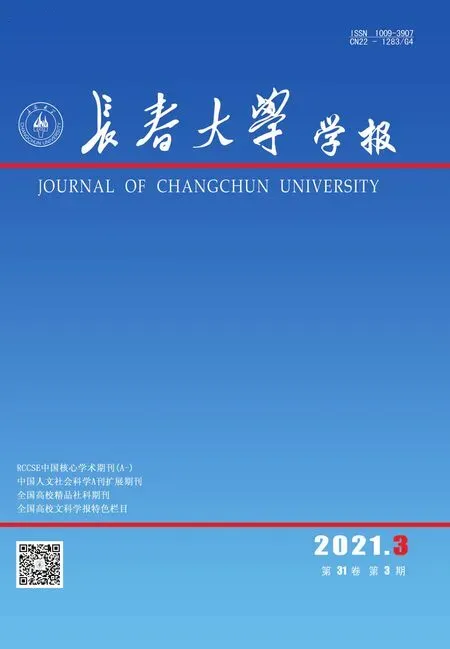《史記》英譯之譯者行為批評(píng)研究
李小霞
(中南林業(yè)科技大學(xué)涉外學(xué)院 語(yǔ)言文化學(xué)院,長(zhǎng)沙 410012)
中國(guó)文化是構(gòu)成世界文化的因子,中國(guó)歷史典籍是中國(guó)典籍的元素,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與碰撞的媒介。作為一部史學(xué)巨著和中國(guó)歷史上第一部史傳類(lèi)文學(xué),《史記》得到了西方漢學(xué)研究者的關(guān)注。《史記》在英語(yǔ)世界的譯介與傳播歷史悠久,英譯《史記》最早出現(xiàn)于1894年,由英國(guó)漢學(xué)家赫伯特·艾倫和法國(guó)學(xué)者雷昂·羅斯奈合作翻譯。由此,《史記》在英語(yǔ)世界的翻譯拉開(kāi)帷幕,眾多漢學(xué)家和翻譯家加入到《史記》英譯的行列,但他們大都是選擇零星的篇章進(jìn)行譯介。在中國(guó)和英語(yǔ)世界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史記》譯家有伯頓·華茲生、楊憲益/戴乃迭和倪豪士翻譯團(tuán)隊(duì)。楊戴和華茲生的翻譯行為發(fā)生于上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倪豪士團(tuán)隊(duì)的全譯工程于上世紀(jì)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式啟動(dòng)。“時(shí)代越特殊,人的行為也越特殊;政治對(duì)翻譯的干擾越大,譯者行為的差異和研究?jī)r(jià)值也越大”[1]282。目前學(xué)界對(duì)《史記》英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譯作,較少關(guān)注譯者,更沒(méi)有人從譯者行為批評(píng)視角對(duì)《史記》譯者行為進(jìn)行系統(tǒng)研究。本文擬從譯者行為批評(píng)視角對(duì)楊憲益/戴乃迭、華茲生和倪豪士等人的翻譯行為進(jìn)行描寫(xiě)研究,解讀同一歷史時(shí)期不同國(guó)家譯者和不同歷史時(shí)期同一國(guó)家譯者行為的差異性,探討導(dǎo)致譯者行為差異的原因,力求客觀描述并闡釋典籍譯者行為的復(fù)雜性和合理度。
一、譯者行為批評(píng)理論
(一)譯者屬性
譯者行為批評(píng)理論是我國(guó)學(xué)者在翻譯批評(píng)理論領(lǐng)域的一重舉。譯者是社會(huì)中的譯者,其翻譯行為一方面有語(yǔ)言性,另一方面又有社會(huì)性[1]2。譯者有自身的意識(shí)行為,譯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譯者的行為蹤跡。譯者身上既有語(yǔ)言性,也有社會(huì)性。當(dāng)譯者行為表現(xiàn)為再現(xiàn)原文文本的意義時(shí),譯者將其表達(dá)的意思用另一種語(yǔ)言呈現(xiàn)出來(lái),這就體現(xiàn)出語(yǔ)言性;同時(shí),考慮到譯文在目的語(yǔ)語(yǔ)境中的接受,譯者行為又表現(xiàn)為譯者對(duì)譯文進(jìn)行的各種調(diào)適,此時(shí)更凸顯其社會(huì)性。
如果語(yǔ)言性和社會(huì)性是譯者行為的兩個(gè)終端,那么譯者永遠(yuǎn)只能在這兩個(gè)終端內(nèi)部活動(dòng),超越語(yǔ)言性或社會(huì)性就不再是翻譯行為。譯者屬性體現(xiàn)在從語(yǔ)言性到社會(huì)性的動(dòng)態(tài)變化中[1]66。為使譯文滿(mǎn)足特定讀者的閱讀期待,譯者可能會(huì)將一些內(nèi)容進(jìn)行加工,盡管在翻譯的學(xué)理上講這樣做并不“合法”,但這莫不是譯者社會(huì)性和客觀上行為社會(huì)化的反映[1]16。譯者的語(yǔ)言性翻譯行為是翻譯的基本層,體現(xiàn)了譯者作為語(yǔ)言人的行為。譯者的社會(huì)性翻譯行為是翻譯的高級(jí)層,譯者在語(yǔ)言人和社會(huì)人之間切換身份。在翻譯的高級(jí)層,譯者行為的差異性和復(fù)雜性更明顯,因?yàn)榇藭r(shí)意志體譯者考慮的因素更繁雜,除了原文,還要考慮目的語(yǔ)社會(huì)的需求,根據(jù)需求借助譯文對(duì)原文進(jìn)行不同程度的調(diào)整,甚至對(duì)原文進(jìn)行改造,這都是譯者的常見(jiàn)行為。因此,復(fù)雜和存在差異的譯者行為可以在譯文中不同側(cè)面或角度得到體現(xiàn)。
(二)“求真-務(wù)實(shí)”連續(xù)統(tǒng)評(píng)價(jià)模式
翻譯批評(píng)理論的另一內(nèi)容以譯文評(píng)價(jià)為研究對(duì)象,即“求真-務(wù)實(shí)”連續(xù)統(tǒng)評(píng)價(jià)模式。“求真”可以理解為譯者完全或部分表達(dá)原文意義的過(guò)程,而基于“求真”之上進(jìn)一步深入考慮務(wù)實(shí)性需求的翻譯行為被視為“務(wù)實(shí)”行為[1]2。不論是“求真”還是“務(wù)實(shí)”都是譯者的行為構(gòu)成要素。譯者追尋的理想狀況是在“求真”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務(wù)實(shí)”效果,不過(guò)在實(shí)踐的過(guò)程中,可能性微乎其微。因?yàn)樽g者行為受各種因素制約,且目的語(yǔ)社會(huì)的需求是譯者首要考慮的因素,譯文的可讀性、流暢性和自然性成為譯者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此時(shí)譯者偏向“務(wù)實(shí)”,彰顯的是其社會(huì)性的一面。有時(shí),譯者選擇尊重原文,將原文所處的異質(zhì)文化置于頭等位置,期望將獨(dú)特的異質(zhì)文化呈現(xiàn)給目的語(yǔ)讀者,譯出盡可能忠實(shí)于異質(zhì)文化的譯文成為譯者的追求,“求真”便成為譯者行為的標(biāo)桿,譯者的語(yǔ)言性得到彰顯。譯者對(duì)“求真”和“務(wù)實(shí)”的把握不僅受譯者自身因素制約,也受制于社會(huì)歷史語(yǔ)境。因此,在一定的社會(huì)歷史文化語(yǔ)境下,譯者行為的“求真”度和“務(wù)實(shí)”度呈現(xiàn)動(dòng)態(tài)的變化,是一個(gè)完整的動(dòng)態(tài)的連續(xù)統(tǒng)一體,互不可分。
二、《史記》英譯行為解讀——譯者行為批評(píng)視角
(一)楊憲益、戴乃迭翻譯行為解讀
1.宣傳中國(guó)經(jīng)典,構(gòu)建中國(guó)形象
《史記選》(SelectionsFromRecordsoftheHistorian)英譯本由楊憲益、戴乃迭二人共同翻譯,自出版以來(lái)享有較高的聲譽(yù)和認(rèn)可度。他們是中國(guó)第一次把《史記》介紹到英語(yǔ)世界的翻譯家。在翻譯過(guò)程中,楊戴夫婦夫唱婦隨,譜寫(xiě)了一段翻譯佳話(huà)。上世紀(jì)40年代,戴乃迭跟隨楊憲益回到中國(guó),50年代,他們收到外文出版社的邀約,著手將中國(guó)經(jīng)典翻譯成英文。譯者的翻譯行為總能折射出時(shí)代的印記,楊憲益、戴乃迭的翻譯行為也不例外。這一點(diǎn)從楊先生的話(huà)語(yǔ)中清晰可見(jiàn):
在1952年的時(shí)候,劉尊棋是外文出版社的社長(zhǎng),在我們到達(dá)之后他表現(xiàn)得很歡迎,在打算詳細(xì)的對(duì)外國(guó)推廣中國(guó)文學(xué),首先是《詩(shī)經(jīng)》,之后列了一份目錄,有100多部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著作,我認(rèn)為非常好……。《宋明平話(huà)小說(shuō)》和《史記》是我覺(jué)得翻譯的最優(yōu)秀的兩部作品。[2]
上述話(huà)語(yǔ)表明,楊憲益和戴乃迭的翻譯行為與他們所處的時(shí)代有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其翻譯軌跡刻上了鮮明的時(shí)代烙印,涂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他們的翻譯行為受命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由國(guó)際新聞局演變而來(lái),對(duì)外宣傳新聞報(bào)道和出版是其主要工作,是國(guó)家官方的專(zhuān)門(mén)外宣機(jī)構(gòu),是向西方世界系統(tǒng)介紹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和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發(fā)起主體和組織實(shí)施機(jī)構(gòu)。“在國(guó)家專(zhuān)門(mén)外宣機(jī)構(gòu)發(fā)起并資助外文出版社的運(yùn)作機(jī)制下,中國(guó)文學(xué)外譯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動(dòng)機(jī),例如塑造新中國(guó)在國(guó)際上的良好形象,對(duì)外輸出中國(guó)革命的經(jīng)驗(yàn)及其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等”[3],最后達(dá)到政治宣傳和傳播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目的。20世紀(jì)50年代,西方世界對(duì)新中國(guó)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誤解。國(guó)家需要借助外宣機(jī)構(gòu)向世界介紹中國(guó),讓西方世界了解新中國(guó),建立良好的國(guó)際形象,提高國(guó)際影響力。此時(shí),最恰當(dāng)、最柔和的途徑便是通過(guò)國(guó)家外宣機(jī)構(gòu)對(duì)外傳播中國(guó)文化,通過(guò)文化交流提升新中國(guó)的知名度。歷史典籍是中華民族的精華,反映了中國(guó)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的方方面面,可以幫助西方世界的讀者認(rèn)識(shí)中國(guó)和了解中國(guó)。《史記》的英譯便在時(shí)代的需求下應(yīng)運(yùn)而生。
2.注重“求真”,彰顯譯者語(yǔ)言性
作為意志體譯者的楊憲益和戴乃迭,他們的《史記選》翻譯行為發(fā)生在向世界介紹中國(guó)、樹(shù)立良好中國(guó)形象的特定時(shí)期。翻譯時(shí),譯者首先滿(mǎn)足國(guó)家政治、文化和外交的需要,關(guān)注何種譯文能在目的語(yǔ)中最大程度地保留并再現(xiàn)中國(guó)歷史文化。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對(duì)楊戴譯本給予了較高評(píng)價(jià):“楊憲益、戴乃迭《史記選》譯本的一個(gè)顯著特點(diǎn)是譯筆簡(jiǎn)潔爽直,完美再現(xiàn)《史記》雄健剛毅的風(fēng)格。”[4]對(duì)內(nèi),楊、戴二人要滿(mǎn)足國(guó)家的外宣需要,最大程度地忠實(shí)于原著,盡量將《史記》的形式、內(nèi)容、風(fēng)格和思想原汁原味地呈現(xiàn)給西方讀者;對(duì)外,他們肩負(fù)著傳播中國(guó)歷史文化的使命,希望譯文能夠被西方一般讀者接受,在英語(yǔ)世界樹(shù)立良好的新中國(guó)形象。基于譯者自身和時(shí)代背景,譯者將“異化”當(dāng)作首要策略,“歸化”其次,尊重原文文化,又盡量保持譯文的流暢和可讀性。例如,他們的節(jié)譯本保留了《史記》的紀(jì)傳體體例,忠實(shí)于原文風(fēng)格,同時(shí)也有對(duì)文字段落重新進(jìn)行邏輯整合,甚至改變?cè)牡亩温鋭澐郑苑嫌⒄Z(yǔ)的行文習(xí)慣。比如,楊憲益將《史記·李將軍列傳》由原來(lái)的19個(gè)段落重新調(diào)整為61個(gè)段落,可見(jiàn)譯者對(duì)原文的行文進(jìn)行了邏輯重組,目的是在忠實(shí)原文內(nèi)容的基礎(chǔ)上保證譯文的可讀性與敘事的流暢性。楊憲益中文功底深厚,對(duì)《史記》原文的解讀準(zhǔn)確到位,戴乃迭的母語(yǔ)是英語(yǔ),他們?cè)谶M(jìn)行翻譯的過(guò)程中發(fā)揮各自?xún)?yōu)勢(shì),揮灑自如,譯文既能精確傳遞原文的意義和思想,又能保證語(yǔ)言精致、流暢、傳神。在“求真-務(wù)實(shí)連續(xù)統(tǒng)評(píng)價(jià)模式”下,楊戴的《史記》翻譯行為注重“求真”,彰顯了譯者的語(yǔ)言人屬性。
(二)華茲生之《史記》英譯行為解讀
1.借譯《史記》之名,行文化利用之實(shí)
華茲生被認(rèn)為是英語(yǔ)世界研究并翻譯《史記》的第一人。華茲生的一生與《史記》有著不解之緣,寫(xiě)過(guò)的很多論文都和《史記》有直接聯(lián)系。他的《史記》選譯本語(yǔ)言流暢自然,是上述譯者的三個(gè)譯本中可讀性最強(qiáng)的譯本,曾一度受到美國(guó)研究者的高度贊譽(yù),在美國(guó)甚至全世界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二戰(zhàn)之后,美國(guó)和蘇聯(lián)形成了對(duì)抗的局面。美國(guó)建國(guó)歷史短,欠缺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yùn),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影響力不突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guó)的國(guó)家形象。為了能在短時(shí)間內(nèi)提升其文化地位,美國(guó)政府欲在世界上推行以美國(guó)為主導(dǎo)的對(duì)外文化戰(zhàn)略,企圖把自己的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和思想觀念強(qiáng)加于他國(guó)。同時(shí)決定攫取中國(guó)等歷史文化悠久的第三世界國(guó)家的文學(xué)歷史,為己所用。“在當(dāng)時(shí)的美國(guó),這樣對(duì)待外國(guó)文化的態(tài)度形成了一種單一文化,只愿意容納符合美國(guó)期望的外國(guó)事物”[5]126。以流暢、自然為主的“歸化”策略在當(dāng)時(shí)占了主導(dǎo)地位。“這種主流翻譯政策在美國(guó)英譯中國(guó)經(jīng)典的過(guò)程中尤為明顯”[5]126。那時(shí)候,中美關(guān)系緊張,美國(guó)意圖譯介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以此來(lái)豐富本國(guó)文化,于是提出“用民主的觀點(diǎn)重新闡釋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6]。一方面,作為具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guó)對(duì)美國(guó)有巨大的吸引力,在文化上是美國(guó)可以攫取和利用的對(duì)象;另一方面,政治、經(jīng)濟(jì)和軍事上如此強(qiáng)大的美國(guó)不愿意照搬中國(guó)的傳統(tǒng)經(jīng)典,而是要進(jìn)行過(guò)濾,利用美國(guó)的意識(shí)形態(tài)和價(jià)值觀念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進(jìn)行改造,改造成符合美國(guó)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模式。在這種背景下,美國(guó)政府和各大基金會(huì)資助了東方經(jīng)典翻譯工程項(xiàng)目,其中對(duì)中國(guó)經(jīng)典的翻譯就包含《史記》。所以,華茲生翻譯《史記》是為美國(guó)國(guó)家文化戰(zhàn)略服務(wù)的,實(shí)質(zhì)上是一種文化利用,而非文化認(rèn)同。
2.追求“務(wù)實(shí)”至上,彰顯譯者社會(huì)性
譯者行為具有復(fù)雜性和差異性,因?yàn)樽g者可以同時(shí)扮演多個(gè)角色。譯者的“社會(huì)人”角色和翻譯行為的社會(huì)屬性在特定歷史語(yǔ)境中表現(xiàn)尤為突出。一旦譯者的“社會(huì)人”得到凸顯,譯者就會(huì)根據(jù)相應(yīng)的個(gè)人需求和社會(huì)需求調(diào)整翻譯行為,例如翻譯選材、翻譯策略選擇、讀者定位等一系列復(fù)雜的翻譯決策。作為意志體譯者,華茲生翻譯行為中“社會(huì)人”角色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并在譯本里留下了明顯的痕跡。
主觀上,華茲生有翻譯《史記》的強(qiáng)烈愿望,這種愿望在他寫(xiě)作博士論文期間就已經(jīng)萌發(fā)。客觀上,恰逢美國(guó)對(duì)外文化戰(zhàn)略調(diào)整,欲通過(guò)譯介第三世界的文化資源提升美國(guó)的文化地位,東方經(jīng)典翻譯工程項(xiàng)目由此誕生。華茲生在時(shí)任哥倫比亞大學(xué)東亞語(yǔ)言與文化系教授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建議下成功申請(qǐng)了該項(xiàng)目中的《史記》翻譯,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縱了整個(gè)翻譯過(guò)程。在翻譯選材上,華茲生主要選取了《史記》中文學(xué)性和故事性較強(qiáng)的部分。在篇章編排方面,完全顛覆了《史記》原有的紀(jì)傳體體例和敘事方式,按照西方讀者所熟知的西方小說(shuō)敘事模式重新編排了《史記》的主要故事情節(jié),讓西方讀者閱讀《史記》時(shí)仿佛是在閱讀一本故事情節(jié)跌宕起伏的歷史小說(shuō)[7]。就翻譯的方法而言,他不主張給譯文加注釋。關(guān)于選材和翻譯策略,華茲生晚年曾有過(guò)論述:
對(duì)于《史記》而言,我的絕大部分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學(xué)上的,我覺(jué)得我翻譯的《史記》已經(jīng)翻譯出了很大程度的文學(xué)作用和影響。……我打算盡量利用最大的空間來(lái)壓縮一部分導(dǎo)言和評(píng)論,并最大限度地去翻譯司馬遷自己說(shuō)過(guò)的話(huà)。[8]
由此可見(jiàn),華茲生的翻譯行為是其個(gè)人意志的體現(xiàn),他欣賞《史記》的文學(xué)價(jià)值和美學(xué)價(jià)值勝過(guò)其史學(xué)價(jià)值。為了再現(xiàn)《史記》的文學(xué)特質(zhì),向英語(yǔ)世界的讀者呈現(xiàn)一部故事情節(jié)跌宕起伏的歷史小說(shuō),流暢性和可讀性成為華茲生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這樣做使得閱讀障礙最小化,向目的語(yǔ)讀者靠攏的行為凸顯其《史記》翻譯行為的社會(huì)屬性,但客觀上遠(yuǎn)離了原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譯者的“語(yǔ)言人”角色和譯者的語(yǔ)言屬性。基于“求真-務(wù)實(shí)”模式,華茲生的翻譯是為了滿(mǎn)足美國(guó)社會(huì)特定時(shí)期的文化需求,一切過(guò)程都圍繞“務(wù)實(shí)”至上,把譯者的社會(huì)人角色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三)倪豪士團(tuán)隊(duì)之英譯《史記》行為解讀
1.秉承求同存異,走向文化認(rèn)同
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蘇聯(lián)解體,中美關(guān)系不再如五六十年代那般緊張,世界文化格局也在悄然變化,以“西方為中心”的單一文化格局逐漸向文化多元化和多樣性轉(zhuǎn)變。2001年,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重申應(yīng)尊重人類(lèi)文化多樣性。“任何文明都是歷史的產(chǎn)物,是特定傳統(tǒng)、地域、生存條件下的具體形態(tài),都有內(nèi)外理?yè)?jù),特定的價(jià)值體系。沒(méi)有一種文明可以宣稱(chēng)比其他文明更為優(yōu)越,也沒(méi)有理由以主流文明自居,歧視、否定甚至取代其他文明”[9]。越來(lái)越寬松的國(guó)際環(huán)境使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不同價(jià)值體系有可能實(shí)現(xiàn)平等交流。美國(guó)改變對(duì)華文化政策,一改五六十年代“居高臨下”的文化姿態(tài),而以一種更加包容和更加開(kāi)放的態(tài)度對(duì)待包括中國(guó)在內(nèi)的第三世界國(guó)家的文化。狄百瑞等學(xué)者不再?gòu)?qiáng)調(diào)用美國(guó)的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和價(jià)值觀改造中國(guó)傳統(tǒng)經(jīng)典,而將了解并尊重中國(guó)傳統(tǒng)經(jīng)典視為理解近現(xiàn)代中國(guó)的一個(gè)必然階段[10]。狄百瑞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反映了美國(guó)政府對(duì)華文化戰(zhàn)略的改變,這在宏觀上影響譯者的翻譯行為。
倪豪士是美國(guó)著名的《史記》研究專(zhuān)家,自20世紀(jì)80年代至今,一直活躍在世界漢學(xué)界。倪豪士曾多次來(lái)中國(guó)進(jìn)行《史記》研究及翻譯的交流。他認(rèn)為華茲生的《史記》英譯本堪稱(chēng)完美,驚艷于他翻譯的功底并感嘆華譯本的文學(xué)特質(zhì)。然而,英語(yǔ)世界一直不曾有《史記》全譯本,更何況之前的譯本都未能詮釋《史記》的史學(xué)價(jià)值。因此,倪豪士萌生了全譯《史記》的想法,并著重關(guān)注《史記》的史學(xué)價(jià)值和研究?jī)r(jià)值。于是,倪豪士組建了自己的翻譯團(tuán)隊(duì),開(kāi)始《史記》全譯工作,得到了太平洋文化基金會(huì)、美國(guó)威斯康星大學(xué)研究生院研究委員會(huì)、中美學(xué)術(shù)交流委員會(huì)等機(jī)構(gòu)的幫助。至今,這一偉大的《史記》全譯工程仍在進(jìn)行。倪豪士渴望英語(yǔ)世界的讀者能認(rèn)識(shí)并研究《史記》的史學(xué)價(jià)值,而不是僅僅將其界定為文學(xué)作品。“譯出一種忠實(shí)的、具有詳細(xì)注解的盡可能可讀的、前后連貫的《史記》全譯本”[11],是倪豪士翻譯團(tuán)隊(duì)追求的目標(biāo)。倪豪士的翻譯行為反映了他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認(rèn)同和尊重,希望將《史記》原汁原味地呈現(xiàn)給英語(yǔ)世界讀者。
2.兼顧“求真”與“務(wù)實(shí)”,體現(xiàn)譯者語(yǔ)言性與社會(huì)性的統(tǒng)一
關(guān)于《史記》的翻譯定位,倪豪士曾在一篇專(zhuān)訪(fǎng)中這樣說(shuō):
華茲生的翻譯沒(méi)有腳注,沒(méi)有評(píng)述,只是翻譯,和我們的譯本大為不同。華茲生的譯本很重要,至今仍然有很多讀者閱讀,但他的譯本對(duì)學(xué)者們來(lái)說(shuō)不太有用。……于是我們提供學(xué)者們需要的英語(yǔ)譯本。精確性、確切性首先是我們要考慮的問(wèn)題,它是第一位的,優(yōu)雅、可讀是第二位的。華茲生翻譯出一種流行的優(yōu)秀譯作,而我們的翻譯目標(biāo)是提供一種精確的學(xué)術(shù)性譯本。一般而言,西方學(xué)者總是產(chǎn)出兩種翻譯,第一種是想要達(dá)到一般閱讀人的要求的翻譯不會(huì)有很詳盡的注解并且十分通俗易懂,而另一種是為了學(xué)者的翻譯,這種翻譯對(duì)文本與上下文都給予廣泛而詳盡的注釋。[12]
倪豪士團(tuán)隊(duì)將讀者主要定位在專(zhuān)家學(xué)者型。他們譯介《史記》的目的是為英語(yǔ)世界讀者提供一種精確的學(xué)術(shù)性譯本。倪豪士等人努力還原《史記》本來(lái)面貌,讓西方世界的讀者更加精確地了解中國(guó)歷史,突出表現(xiàn)其史學(xué)價(jià)值。他們?cè)诜g過(guò)程中,得到過(guò)中外史學(xué)專(zhuān)家的指導(dǎo),倪豪士多次到德國(guó)、法國(guó)、中國(guó)參加《史記》方面的研討會(huì)和學(xué)術(shù)交流會(huì)。倪豪士譯本最顯著的特色莫過(guò)于譯本里飽含豐富的副文本信息,這些副文本信息可以幫助讀者更真切、更深入地融入彼時(shí)的文化語(yǔ)境,帶他們穿越到司馬遷《史記》中描寫(xiě)的彼時(shí)代,補(bǔ)充豐富的漢語(yǔ)歷史文化知識(shí)。與華茲生不同,倪豪士翻譯團(tuán)隊(duì)以尊重原文、尊重異域文化為己任,渴望目的語(yǔ)文化的讀者認(rèn)識(shí)并深度理解源語(yǔ)文化。倪豪士等人的《史記》翻譯行為表明他們更注重《史記》的史學(xué)研究?jī)r(jià)值,譯者的“語(yǔ)言性”得到了較好的體現(xiàn)。在“求真-務(wù)實(shí)”連續(xù)統(tǒng)評(píng)價(jià)模式下,譯者兼顧“求真”與“務(wù)實(shí)”,體現(xiàn)了譯者“語(yǔ)言人”與“社會(huì)人”角色的有機(jī)統(tǒng)一。
三、結(jié)語(yǔ)
翻譯行為是一項(xiàng)復(fù)雜的社會(huì)行為。譯者行為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如譯者身份角色、譯者屬性、譯者行為發(fā)生的宏觀環(huán)境。反之,不同的譯者行為折射出了譯者的意志性、譯者角色和譯者屬性。在“求真-務(wù)實(shí)”譯者行為連續(xù)統(tǒng)評(píng)價(jià)模式下,若譯者傾向“求真”,則彰顯其語(yǔ)言性,若偏離“求真”、傾向“務(wù)實(shí)”,則彰顯其社會(huì)性。譯者行為批評(píng)理論為客觀公正地解讀楊憲益/戴乃迭、華茲生和倪豪士團(tuán)隊(duì)的英譯《史記》行為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楊憲益、戴乃迭意在弘揚(yáng)中國(guó)傳統(tǒng)經(jīng)典,構(gòu)建良好的國(guó)家形象,突出了“求真”的譯者行為,彰顯了譯者的語(yǔ)言性;華茲生借譯《史記》之名,行文化利用之實(shí),是一種追求“務(wù)實(shí)”為上的行為,彰顯了譯者的社會(huì)性;倪豪士團(tuán)隊(duì)秉承求同存異、走向文化認(rèn)同的原則,兼顧“求真”與“務(wù)實(shí)”的行為,彰顯了譯者語(yǔ)言性與社會(huì)性的有機(jī)統(tǒng)一。他們的翻譯行為都是時(shí)代的產(chǎn)物,同時(shí)也都滿(mǎn)足了彼時(shí)代的需要,并產(chǎn)生了積極的效果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