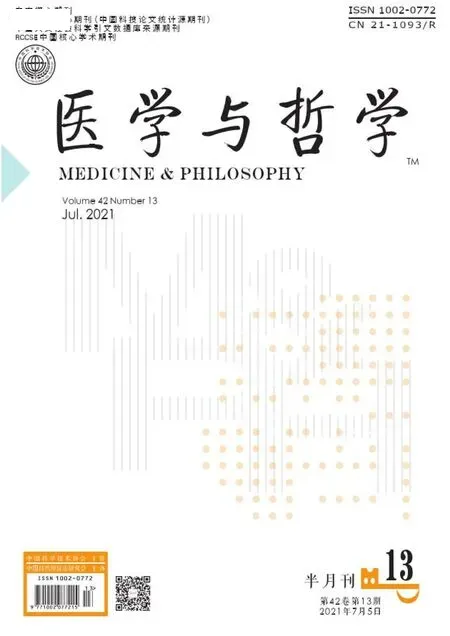身體理論視域下的醫者德性之養成*
劉俊榮 趙麗霞
1 德性內涵之透視
“德性”是美德倫理學的核心概念,對這一概念的界定和解讀直接影響著對德性養成路徑的分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德性”一詞最早出自《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就是說,君子應當尊奉德性,善學好問。其中的“德”指品德,如《易·乾·文言》主張:“君子進德修業。”“德”也可以指道德,“道德”二字連用始于荀子《勸學》篇:“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即,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范。“性”指人或事物的本身具有的特質,如《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則天之明》認為:“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德”與“性”合用即“德性”,是指人的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之性。如鄭玄主張:“德性,謂性至誠者也。” 孔穎達指出:“‘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
在西方,蘇格拉底提出了“德性即知識”的著名論斷,認為德性是可教的,主張人的諸如公正、節制、虔誠、勇敢等卓越品質為美德;柏拉圖在蘇格拉底的基礎上,提出了“德性即正義”的主張。而亞里士多德則強調“德性即中道”,并系統論述了德性的本質、形成、培養等系列問題,首創了德性倫理學。在他看來,“人之為人的德性,就是實現最即也就是成為最高貴的、優秀和最卓越的自己,而這個‘自己’是超越了人的‘自然’的第二個自己,讓靈魂中最高貴的部分起主宰作用的自己。這種意義上的德性就是做(實現)最好的自己”[1]。在現代倫理學研究中,關于“德性”的界定,仁者見仁,不一而足。如以美國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lntyre)[2]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德性是獲得實踐的內在利益的必需品質,是有益于整體生活的善的品質。” 我國學者江暢[3]在其《德性論》一書中認為:“德性是人運用理智或智慧,根據其謀求生存得更好的本性的根本要求并以生存得更好為指向培育的,以心理定勢對人的活動發生作用,并使人的活動及其主體成為善的善品質,即道德的品質。”
基于以上的知識梳理,本文所謂的“德性”是指人應當具有的好的、優秀的道德品質,即美德,包括孔子的“仁愛、忠恕、修己”,孟子的“仁義禮智”,朱熹的“居敬、窮理、省察”,以及古希臘強調的公正、智慧、勇敢、節制、虔誠等優良品質。它不同于可好可壞、可善可惡的一般意義上的道德品質。
“德性”不同于“德行”。在現代漢語中,“德性”同“德行”被視為同義語,實際在用法上是有所不同的。“德性”是內在的,是人本身所特有的道德品性。而“德行”是外在的,如鄭玄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但是,二者又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只有具備優秀的德性,并依此去行動,才能產生善良的德行;只有按照善良德行的準則、規范做事,才能逐漸養成優秀的德性。也就是說,要達到作為行為規范的“禮”的目的,就必須要有良好的“德”的修養為前提;反之,如果要完成“德”的修養,也必須有“禮”作為規范,二者在作用上雖有所不同,但其實質是相輔相成的。這也可從“德”與“得”的關系上反映出來。據《釋名·釋言語》云:“德,得也,得事宜也。”亦有“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之說。也就是說,“德”就是“得”,做事做得適宜,于人是德、是好事,于己也是收獲,是善事。
然而,德性與德行并非是絕對統一的。具有了好的德性并非必然能夠表現出善良的德行,現實生活中從善良的動機出發未必一定能夠做成好事;做成了一件好事也并非就可以說具備了善良的德性,歪打正著、出于壞心而做成好事的現象也并非罕見。因此,如何能夠在養成好的德性的同時,促成善良德行的形成,是當前德性教育的根本問題。
2 醫者德性教育之反思
中國古代十分重視“禮”在德性養成中的作用,并被置于周代“六藝”之首。如孔子強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并提出:“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禮”即在社會生活中基于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形成并為大家共同遵守的準則和儀式,包括祭祀之事的吉禮、冠婚之事的嘉禮、賓客之事的賓禮、軍旅之事的軍禮、喪葬之事的兇禮等五禮,這些禮制成為當時約束人們行為的基本規范,并對中華民族文明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古人在傳授這些禮制時,并不是先講授為什么要這樣做,讓人們事先明白做的道理,而是告訴人們本應這樣做,只有這樣做,才能體現對上蒼、土神、祖先、圣賢、長輩、賓客的敬重,才符合禮制的要求,故古代強調“習禮”而不是“講禮”。盡管舊時的禮制并非都適用于當下,但古人傳授“禮”的方法對當下有借鑒之處。在現代德性教育中,儀式、“禮”的作用日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講授,將傳授道德知識、提升道德判斷能力等作為德性教育的重要任務,而忽視了道德體驗、道德品質的養成。雖然在各類學校各個階段均設有道德教育、人生修養等課程,但因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的超驗性,造成了知與行、說與做的分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重道德知識,輕道德踐行
自近代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以來,知識便成為力量的同義語。尤其是自然科學知識,更被視為力量的象征,過去學校曾流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說法。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即使德性教育也不例外。在目前的德性教育體系中,大多把講授基本范疇、基本理論、基本原則、基本規范等系統的知識,作為德性教育的重要內容。教師主要是知識的傳播者,道德理論的講授者,學校對學生德性的考核也主要局限于道德知識,較少關注學生的道德踐行。
我國古代教育十分重視道德踐行和德行的養成。孔子強調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墨子主張“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君子要“以身藏性”。而荀子根據言與行的關系,將人分為四個類別:第一類人言行一致;第二類人能做不能說;第三類人能說不能做;第四類人是說得好做得壞。他說:“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
隨著現代教育的規模化,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學生集中于一個教室學習,表面上看提高了知識傳播的效率,強化了教育的同質性,但也喪失了古代傳統教育中場景式、個體化教學的優勢。孟母斷杼、張良拜師等情境式德性教育,以及對話式、討論式的體驗性教育正是現代德性教育所欠缺的。孔子指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應當按照學生的特點,根據學生的需求和體驗因材施教,即“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他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一個人只有到了發奮求知、努力鉆研,有了百思不得其解的體驗時,去引導他、給他講授相關的道理,才能達到啟發、解惑的效果。在當前的醫學倫理及醫德教育中,問而不答、啟而不發、滿堂灌、填鴨式的德性教育方法,值得深刻反思。
2.2 重道德理性,輕道德直覺
肉體、情感、欲望等作為非理性的存在,自古就被柏拉圖、基督教等哲學派別所鄙視,甚至被當作罪惡、墮落的象征。尤其笛卡爾開創理性主義之后,本能、直覺、意志等因素日益被弱化,直至人本主義者叔本華、尼采重新喚起內心深處的意志,非理性主義才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是,與理性主義相比,非理性主義始終沒有獲得好的名聲。在理性主義者看來,道德判斷是一系列理論推理的結果,患者的自主選擇必須是基于理性的、深思熟慮的決定,否則就不可作為醫療決策的依據。事實上,這種對“理性”的偏愛潛在著一種預設,這種預設忽視了本能、直覺等身體的維度,認為只有理性才能體現個體的意志和價值,而身體直覺、非理性、本能等是不可靠的、無用的。我們姑且不論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對與錯、是與非,僅就理性與直覺而言,二者不可偏廢。正如雅斯貝爾所說:“理性若沒有它的另一面——非理性,是不可思議的。”而且,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道德判斷包括直覺系統和推理系統兩種加工,很多時候人們的道德判斷更多的是一種直覺和情感的結果[4]。
但是,在當前的醫學倫理及醫德教育中,課堂上講授更多的是,作為醫者為什么應當這樣做,道德判斷的原則、準則及依據是什么,應當遵循什么樣的醫德規范及要求等理論。無疑,這有助于增進醫學生判斷善惡、明辨是非的知識,引導醫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理念。但是,如果缺乏按照原則、準則、規范要求做事的堅定信念,失去為挽救他人生命和財產奮勇獻身的沖動、本能和良知,理性的道德判斷和算計可能成為追求道德高尚、踐行善良德行的桎梏。而堅定信念、道德意志的養成,除了需要理性灌輸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過情境教育、習慣強化等直觀性的身體規訓。
古代之所以強調“有志者,事竟成”“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在心為志”等,也正是看到了信念、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而且,古人還高度重視環境熏陶在性情、意志培育中的作用。《孔子家語·六本》指出:“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晉代傅玄在其《太子少傅箴》也強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遷等,這些都強調了外在環境、感性直觀等在德性養成中的作用,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純粹理性教育的弊端。
2.3 重道德言傳,輕道德身教
古往今來,教育家們無不主張“言傳身教”。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些都強調只有自己行得端、處事公、做得正,才能有效地號令他人、教導學生,事半功倍,否則就沒有說服力、號召力。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第三十個教師節時在北京師范大學強調全國廣大教師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實知識、有仁愛之心”的好老師,其意義也正在于此。“身教”除了強調教者本人應率先垂范、以身示教之外,還意味著應充分重視榜樣的力量,弘揚榜樣精神。孔子主張“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9月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上講話時提出:“崇尚英雄才會產生英雄,爭做英雄才能英雄輩出。” 鐘南山院士作為“共和國勛章”獲得者,作為“抗非”抗疫英雄,在抗擊疫情的戰斗中,其榜樣人物、英雄模范的勇敢、正直、執著、樸實的鮮明品格是德性教育的最好例證。
“身教”除了以身示教之外,還包括身體教育。所謂身體教育就是“主張身體是教育的根本,在教育過程中始終堅持把每個人的身體作為教育的出發點和中心點,而不是以知識、技能或其他除身體外的功利化的如應試等為目標的教育學說”[5]。身體教育強調身體既是教育手段的載體,也是教育手段的服務對象,注重身體在人的品性、體格培養中的作用,呼吁認識身體、保護身體、磨煉身體、控制身體、美化身體、運用身體,試圖通過“文明其精神,野蠻其身體”,達到人心與獸身的合一,以實現孔子所期望的身體教育的目標:“從心所欲不逾矩”。事實上,“初始的教育實踐原本就是‘身體力行的教育’,大量地顯示為親身感受、以自己的身體與野獸搏斗、以自己的身體與自然對抗等‘身體活動’。與之相應的教育觀念可稱為‘古代教育學’。這種‘古代教育學’的核心精神是重視身體‘感覺’的‘身體教育學’”[6]。至近代,由于“哥白尼革命”揭示了人類“感覺”的不可靠性、可錯性,對人類的“感覺”給予了無情的、顛覆性的打擊,身體教育才開始轉向“知識教育”,身體在教育中的作用日漸弱化,直至到現代仍未能恢復其原本的地位。
2.4 重道德他律,輕道德自律
我國古代特別強調社會評價、社會輿論等道德他律的作用,如《史記·張儀列傳》有“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說,《晉書·劉喬傳》有“群言淆亂,異說爭鳴,眾口鑠金,積非成是”之言。在荀子看來,“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人的本性是惡,要使其從善必須通過后天教化、加強道德教育,需要外在的強制、約束、鞭撻,否則就無法達到修身之目的。因此,在荀子看來,人的道德素養的提高,只有通過他律來實現。孟子從人性善出發,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強調人生來固有善端,應當積善累德。因此,他認為修身是一個內省的自律過程,需要激發人內心的善性,需要提升自我反省的能力。
他律與自律是道德規范發生作用的不同方式,二者原本是統一的,人的德性之養成既離不開道德他律,也離不開道德自律,既需要靠教育、教化、良心來維系,也需要有輿論、規章、制度作支撐。但是,在當前的醫者的德性教育中,學生成為被動的知識接受器,而基于教化的自修、慎獨的時間越來越少,基于良心的內省日漸弱化。往往以旁觀者的角色去審視他人、審視社會,面對問題抱怨、牢騷多于內省、自責,擔當意識、責任意識亟待加強。
3 基于道德本能的醫者德性之踐行
奧克肖特[7]認為,人類的道德生活形式有兩種,分別是“道德本能”和“道德判斷”。道德本能是自然的、固有的、感性的、直觀的、不可論證的,它表現為一種不假思索的本能的道德反應,如同情感、羞恥感、敬畏感、母愛等。道德本能不受理性所控制,就像一個正常人無法刻意控制自己的臉紅一樣,我們也無法控制道德本能所支配的道德活動。在道德活動中,道德本能并不是可有可無的、隨意馭使的、依需到場的器物,尤其在“應對生活中那些沒有時間和機會進行反思的急事”時,它有其獨特的作用,如在緊急境況下舍己救人者,大多出于本能的道德良知或內心的“應當”而無暇進行道德思量和權衡。這與道德判斷不同,道德判斷是行為主體根據自身訴求、道德境遇、行為后果、社會輿論等進行權衡思量的結果,是文化、社會、理性、反思、可論證性等因素的反映。道德判斷把特定的價值歸因于個人或者社會的自我意識,不僅規則與理想是反省思考的結果,而且對這種規則或理想的運用也是一種思考性活動。在此,道德生活形式表現為一種有根有據的思考,是依照道德標準、道德規范、道德原則進行道德推理、分析、評估、權衡的結果。
關于道德本能與道德判斷在人類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主義與理性主義持有相反的觀點,前者以良心、良知、同情這些先天的道德感為根基,把道德規范和原則最終還原為自然進化的結果,歸結于“利他”基因的傳承。理性主義則將道德規范和原則最終視為人類群體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需要,歸結為理性的約定。二者均無法擺脫懷疑論和相對論的陰影。
事實上,道德判斷與道德本能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共同建構了人類道德生活的內容。一方面道德生活有其自然本能的根源,另一方面道德生活需要通過理性而進行合理的必要道德約定。舍棄道德本能,道德生活就會變得乏味、單調、死寂或機械;舍棄道德判斷,道德生活就會顯得散漫、放蕩、無政府主義或零亂。因此,理性主義者蒙田[8]在論及良心問題時,也不得不說:“即使人在作惡時感到樂趣,良心上卻會適得其反,產生出一種憎惡感、引起許多痛苦和聯想,不論睡時醒時都折磨自己。”古今中外有不少的思想家對道德本能給予了關注,如孟子的不學而知、不習而能的性善論強調:“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在孟子看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四種情感即“四端”,是人所普遍具有的天生道德能力,是仁義禮智的道德之源。而盧梭[9]則把“自愛”與“憐憫”看作是兩個先于社會性的原動力,他說:“即使沒有社會性這一動力,我覺得,自然法的一切規則也能從其中(即從自愛與憐憫這兩個原動力中)產生出來。”此外,亞里士多德強調的友愛之德,休謨偏好的仁愛等,都是以“良知”的名義對道德本能的弘揚。現代神經科學研究表明,鏡像神經元能夠表征與個體自身行為相似的動作圖式,這一成果為憐憫、同情的形成提供了生理學的詮釋。
當下,盡管我們還沒有充分的證據能夠說明道德本能發生的內在機制及其與道德判斷的關系。但是,至少我們可以說人類的道德生活離不開道德本能,純粹的道德教育和道德說教,雖然能夠增強人們的道德思維和道德判斷能力,但未必能夠強化人們的道德行為,增進人們的善行。舍勒[10]曾說:“沒有人通過倫理學而變得‘善’。”人的善行只能基于內在善或德性,如果在人的本性中缺少善的能力,單純的理性約定不可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此,《內經》強調對于習醫之人必須有高尚的美德,“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 “十不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古時疑殆”。魏晉時期的楊泉在其《物理論》中指出:“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 這些都強調了學醫之人在本性中必須擁有善的德性和良好的品質。人也許正是具有其他動物所不具有的道德本能和德性,人才能通過教育、學習、鍛煉、規訓形成符合道德標準、規范、原則等身體善行和道德習慣。正因如此,別爾嘉耶夫[11]說:“沒有同情,倫理學是不可能的。”
4 身體規訓與道德本能之養成
道德本能盡管不受理性所控制,與行動者的道德知識沒有直接的聯系,但并不是說道德本能完全是先天的、與后天教育無涉,只是說僅憑道德思想教育、道德理論說教不足以影響道德本能,難以達到應有的道德善行。道德善行需要身體的行動,而身體作為一種歷史和文化現象,對其建構重要的不是通過理性和說教,而是反復和持久的“操練”活動,即對身體的規范化訓練。梁漱溟[12]曾指出:“個人后天習慣無不是從社會生活中養成的,這就關聯到社會生活規制問題上。”“生活規制必從身體實踐養成習慣,乃得落實鞏固。”
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認為,在權力社會中身體與權力是交織在一起的,權力熱衷于發號施令,以戒律禁止某些話語和行為,通過紀律和調節技術,采用規范的準則而達到控制行為和身體之目的。權力對身體的控制主要是通過稱為紀律技術的身體解剖—政治(anatomo-politics)實現的。它首先將群體解剖為一個個的肉體,通過將個體納入到規范化、制度化的時空安排中實現對個體檔案的編制、信息的收集,以及對個體的監視、編碼、訓練和強制,由此制造出一個個被馴服的身體,并通過對其所建構的單個身體的組合,從馴服的身體到規范的大眾,從而實現對群體的控制。在福柯看來,身體作為權利的建構之物,不僅是權利的工具和客體,也是被馴服的主體,作為主體,它無法逃脫紀律權力的檢查和監視。紀律權力通過強化身體及其行為的可見性,使他們被置于持續的、全景式的監視之下,成為可見的客體。在全景展示的空間中,被監視的個體完全陷于一種無法預期的不可見的監控之中,“紀律權力通過其不可見性被實施;同時它強加給那些從屬于它的人一種強迫的可見性原則。在規訓中,這些從屬者必須被看見。他們的可見性確保了權力對他們的統治。正是始終被看見和在任何時候都能夠被看見這一事實,確保了被規訓的個體處于從屬的地位”[13]。在紀律權力凝視下的操練活動,不需要軍隊、暴力和物質的約束,每一個人在紀律權力的凝視下將通過內化而成為其自身的監工。紀律權力所養成的服從主要來自于習慣性的自我控制,它是建立在身體信仰之中的,表現出主動的服從。作為被權力監視的客體,身體是可見的,而可見性使其被置于更嚴密的監視中。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被監視下的規范行為日益得到強化,從而使個體從某種權宜的服從轉向了自我的制約,紀律權力轉變為一種內在的自動運轉機制。紀律權力對身體的監視通常是非暴力的,不是依靠外部壓制的,它是通過紀律機構中所展開的一系列細致的安排和層層的監視,通過在特定區域中的反復和持久的規范化操練所形成的自我規訓去發揮效能。規范化是現代社會管制的一項重要特征,它與偏向罰款、鞭笞的司法模式不同,規范化主要通過重視獎勵及反復的操作為其懲罰的方式,通過對個體的強化操作和規訓,縮小不同個體間的差異和個性,達到步調一致。
福柯的上述思想,對我們思考道德本能向道德判斷的演進機制,探討德性向德行轉化的路徑,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按照福柯的身體理論,道德本能、行為習慣是可以后天習得的,通過文化、政治、權力對身體的規訓,可以實現對身體的改造,并可以通過一整套的監視系統來實現對“群體”的控制,由此確保所有身體的標準化,達到道德訓誡之目的。如護士在執業過程中應堅持“三查七對”的制度(三查指操作前查、操作中查、操作后查;七對指對床號、對姓名、對藥名、對劑量、對時間、對濃度、對用法),對這一制度的遵守僅僅通過護理倫理知識的講授、倫理原則的剖析是不夠的,需要通過身體規訓機制來實現。按照福柯的身體理論,規訓機制需要具備三個可供實施的情境:其一,單元定位。依據紀律權力即護理規范,為了培養合格的護士,首先將同一年級的護理學生分成不同的班級小組,每一個護理學生服務對應的患者,在特定的空間即病房內,操作必備的護理儀器、藥品等設施,在指導教師的監督下按照“三查七對”的要求嚴格操作。這樣,“三查七對”就成為一項在特定空間內可供監督和實施的訓練計劃。其二,活動控制。以時間為例,將“三查七對”行為分配到具有嚴格的時間計劃之中,不同患者甚至同一個患者在一天中的不同時間服藥、注射、輸液的事項是不同的。通過明確規定護理學生在一天中應什么時間給患者服用什么樣的藥物、什么時段進行什么樣的藥物注射、在何時輸什么液體等,以此可見性的操作使護理學生逐漸形成習慣性的自我控制。其三,評定考核。通過對每個人的時間的控制,調節時間、肉體和精力的關系,以高度的注意力、在規定的時間內以嫻熟的操作高水平地完成規定的任務,并以此為標準對每個人的表現進行評定。這種身體規訓把教學進程分解成了最簡單的元素,把每個發展階段分解成小的步驟,通過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形成了一種完整的分解教育,并最終通過對單個身體的馴服和建構,達到對大眾的規范,從而實現對護理學生群體同一行為的操作控制。
總之,身體規訓有助于從控制的身體中創造出一種具有單元性、可控性、可測性、組合性的個體,并通過時間的累積形成自我控制的習慣,達到規范德行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