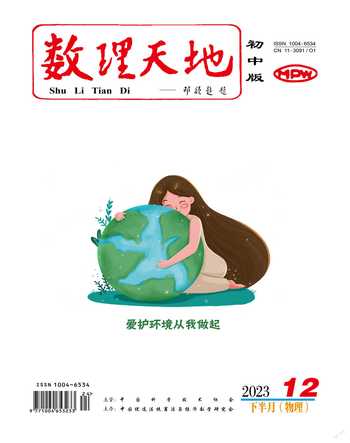基于問題解決方法的初中物理課堂教學(xué)研究
廖玉秀
【摘要】初中物理課堂是學(xué)生打下物理基礎(chǔ)、培養(yǎng)科學(xué)素養(yǎng)的基石.通過將問題解決法應(yīng)用于課堂教學(xué),教師可以幫助學(xué)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物理知識,同時(shí)也能有效提升學(xué)生的自主學(xué)習(xí)和問題解決能力.本文旨在探討基于問題解決方法的初中物理課堂教學(xué),針對初中物理課堂教學(xué)現(xiàn)狀,提出真實(shí)有趣符合現(xiàn)實(shí)的問題、設(shè)計(jì)有效的問題解決策略、建立和諧合作學(xué)習(xí)氛圍等策略,通過這些措施,可以更好地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促進(jìn)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
【關(guān)鍵詞】問題解決方法;初中物理;課堂教學(xué)
問題解決方法是一種基于學(xué)生自主思考和實(shí)踐的教學(xué)方法,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生在解決實(shí)際問題過程中的主體作用.在初中物理教學(xué)中,傳統(tǒng)的教學(xué)模式過于注重知識的灌輸和記憶,缺乏對學(xué)生思維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yǎng).因此,引入問題解決方法成為一種有益的嘗試,能夠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實(shí)際應(yīng)用能力和創(chuàng)新思維.
1 問題解決方法的概述
問題解決方法是一個(gè)通過系統(tǒng)性的步驟和技巧,科學(xué)地解決各種問題和挑戰(zhàn)的過程.它通過科學(xué)的思維方式和邏輯推理,幫助人們深入分析問題的本質(zhì),尋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并采取相應(yīng)的措施來實(shí)現(xiàn)預(yù)期的目標(biāo).在問題解決方法的實(shí)施過程中,需要遵循以下原則:首先,要進(jìn)行科學(xué)思考和分析,通過系統(tǒng)性的思維和分析來揭示問題的本質(zhì),以便更好地理解問題;其次,要進(jìn)行有效的信息收集和處理,獲取充足的信息來支持決策制定,并且利用適當(dāng)?shù)墓ぞ吆图夹g(shù)來對信息進(jìn)行處理和應(yīng)用;再次,要進(jìn)行合理的規(guī)劃和目標(biāo)設(shè)定,明確解決問題的目標(biāo)和步驟,制定相應(yīng)的計(jì)劃和策略并加以實(shí)施;最后,問題解決方法還強(qiáng)調(diào)團(tuán)隊(duì)合作和協(xié)作的重要性.
通過與他人的交流和合作,匯集各方的智慧和經(jīng)驗(yàn),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這種方法具有科學(xué)和系統(tǒng)性、全面和綜合性、靈活和創(chuàng)新性、持續(xù)學(xué)習(xí)和改進(jìn)等特點(diǎn).通過明確步驟和技巧,問題解決方法能夠確保解決問題的一致性和可行性.同時(shí),通過多角度思考和分析,綜合各種因素,能夠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并提供相應(yīng)的解決方案.
2 問題解決方法在初中物理教學(xué)中的教育價(jià)值
2.1 激發(fā)學(xué)生學(xué)習(xí)興趣和動(dòng)機(jī)
問題解決方法可以通過引導(dǎo)學(xué)生主動(dòng)參與解決實(shí)際問題的過程,激發(fā)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和學(xué)習(xí)動(dòng)機(jī).物理學(xué)科中的很多現(xiàn)象和原理都可以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找到應(yīng)用,通過問題解決法,教師可以把生活中的實(shí)例或現(xiàn)象引入到課堂教學(xué)中,引導(dǎo)學(xué)生運(yùn)用所學(xué)的物理知識和原理去解決實(shí)際問題.這樣可以讓學(xué)生感受到物理知識的實(shí)用性和趣味性,同時(shí)也可以增強(qiáng)他們對物理學(xué)習(xí)的積極性和主動(dòng)性.
2.2 培養(yǎng)學(xué)生解決實(shí)際問題的能力
問題解決方法注重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實(shí)踐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物理教學(xué)中,通過設(shè)置真實(shí)的問題情境和解決過程模擬,引導(dǎo)學(xué)生主動(dòng)運(yùn)用所學(xué)物理知識和技能,分析和解決實(shí)際問題.這樣的教學(xué)方法可以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觀察、實(shí)驗(yàn)、測量、推理和運(yùn)算等能力,使他們具備解決實(shí)際問題的實(shí)踐動(dòng)力和能力,提高物理學(xué)習(xí)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2.3 發(fā)展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和合作精神
問題解決方法強(qiáng)調(diào)從多個(gè)角度考慮問題、靈活應(yīng)用知識和技能,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在物理教學(xué)中,通過引導(dǎo)學(xué)生分析問題、總結(jié)規(guī)律、提出新的解決方案等,激發(fā)學(xué)生的創(chuàng)造力和思維能力,培養(yǎng)他們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創(chuàng)新能力.同時(shí),問題解決方法也鼓勵(lì)學(xué)生進(jìn)行團(tuán)隊(duì)合作,通過與他人的合作與討論,共同解決問題,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合作精神和團(tuán)隊(duì)合作能力,使他們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xué)會(huì)與他人進(jìn)行有效溝通與協(xié)作.
3 初中物理課堂教學(xué)現(xiàn)狀分析
3.1 重視理論而忽視實(shí)踐
傳統(tǒng)教學(xué)模式下,課堂主要以講授知識點(diǎn)和解題技巧為主,缺乏實(shí)驗(yàn)和實(shí)踐環(huán)節(jié).這種教學(xué)方式讓學(xué)生只是死記硬背,而無法真正理解物理原理和規(guī)律,也無法培養(yǎng)學(xué)生的科學(xué)探究能力和創(chuàng)新思維[1].同時(shí),由于缺乏實(shí)踐機(jī)會(huì),學(xué)生無法將所學(xué)知識應(yīng)用到實(shí)際生活中,也無法通過實(shí)驗(yàn)驗(yàn)證自己的想法和假設(shè),進(jìn)一步影響了學(xué)生的科學(xué)素養(yǎng)和實(shí)踐能力的提高.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教師需要重視實(shí)驗(yàn)和實(shí)踐教學(xué),讓學(xué)生有更多的機(jī)會(huì)親身參與和動(dòng)手操作.
3.2 缺乏足夠的互動(dòng)和討論
在傳統(tǒng)教學(xué)模式下,教師單向傳遞知識,學(xué)生以被動(dòng)的接受者角色參與課堂.缺乏學(xué)生之間的互動(dòng)和討論,不利于學(xué)生思維的激發(fā)和能力的培養(yǎng).由于每個(gè)學(xué)生理解和掌握知識的能力不同,缺乏互動(dòng)和討論會(huì)讓一些學(xué)生無法及時(shí)發(fā)現(xiàn)和解決問題,影響學(xué)習(xí)效果.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教師可以采用互動(dòng)式教學(xué),讓學(xué)生在課堂上積極參與討論和交流.
3.3 學(xué)生學(xué)習(xí)興趣不高
傳統(tǒng)的初中物理教學(xué)模式注重知識點(diǎn)的獨(dú)立傳授,缺少趣味性和實(shí)用性的引導(dǎo)[2].因而學(xué)生容易感到枯燥乏味,學(xué)習(xí)興趣不高.初中學(xué)生正處在心理和生理的快速發(fā)育階段,對于新奇有趣的事物充滿了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如果物理課堂無法激發(fā)他們的興趣和熱情,他們就可能對物理學(xué)科產(chǎn)生消極的態(tài)度,影響學(xué)習(xí)效果.
4 問題解決法在初中物理課堂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策略
4.1 構(gòu)建真實(shí)有趣符合現(xiàn)實(shí)的問題
問題解決法的核心是構(gòu)建真實(shí)、有趣、符合學(xué)生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問題.這種方法強(qiáng)調(diào)將問題與實(shí)際生活緊密相連,引導(dǎo)學(xué)生通過解決問題來理解知識、提高能力.在構(gòu)建問題時(shí),教師需要關(guān)注學(xué)生的興趣和實(shí)際生活經(jīng)驗(yàn),讓問題既有趣又具有挑戰(zhàn)性.同時(shí),問題需要與教學(xué)內(nèi)容緊密結(jié)合,讓學(xué)生通過解決問題來理解和掌握物理原理和規(guī)律.
例如 在講解“阻力對物體運(yùn)動(dòng)影響”的知識時(shí),在演示實(shí)驗(yàn)后可以構(gòu)建以下問題:“為什么從斜坡滑下來的小車會(huì)逐漸減速停下來?這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這個(gè)問題與學(xué)生的實(shí)際生活經(jīng)驗(yàn)相連,他們可能經(jīng)常觀察到“不踢足球后,原來滾動(dòng)的足球會(huì)慢慢停止運(yùn)動(dòng)”這類現(xiàn)象.通過引導(dǎo)學(xué)生思考和探究,可以讓他們理解到摩擦力對物體運(yùn)動(dòng)的影響.他們會(huì)學(xué)到摩擦力的概念,即在物體與表面接觸時(shí),存在一種阻礙相對滑動(dòng)的力.此外,還可以構(gòu)建一些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問題,如:“夏天去海邊游玩,踩在沙子上感覺很燙,踏進(jìn)海水卻感覺涼爽,同一個(gè)位置,接收太陽照射的強(qiáng)度和時(shí)間相同,為什么卻出現(xiàn)如此不同的現(xiàn)象?”這個(gè)問題可以引導(dǎo)學(xué)生探究溫度、熱量以及比熱容等概念,幫助他們理解和掌握這些基本的物理原理.
4.2 設(shè)計(jì)有效的問題解決策略
設(shè)計(jì)有效的問題解決策略是問題解決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在制定問題策略時(shí),教師需要考慮學(xué)生的實(shí)際情況和學(xué)習(xí)能力,設(shè)計(jì)出適合學(xué)生的問題解決策略[3].同時(shí),教師還需要對問題的解決策略進(jìn)行預(yù)設(shè),并準(zhǔn)備好相應(yīng)的解決方案.在實(shí)際教學(xué)中,教師還需要根據(jù)學(xué)生的反映和問題解決的情況進(jìn)行靈活調(diào)整,以適應(yīng)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需要.
例如 在復(fù)習(xí)初三“電學(xué)”部分的知識時(shí),教師可以設(shè)計(jì)以下問題鏈解決策略:首先,激發(fā)學(xué)生的興趣,引入問題:在電路中,為什么燈泡會(huì)亮起來?讓學(xué)生思考燈泡亮起來的原因.接著再提出遞進(jìn)問題“電流是怎樣形成的?”,引導(dǎo)學(xué)生回顧電流與電壓的概念,“基本電路由哪些部分構(gòu)成?”這個(gè)問題就水到渠成提出來了.通過實(shí)際操作或觀察,讓學(xué)生總結(jié)基本電路的四個(gè)部分:電源、用電器、導(dǎo)線、開關(guān),并發(fā)現(xiàn):只有電路閉合且電源供電時(shí),燈泡才會(huì)亮起來.最后提出:“電路中電流的方向是怎樣的?”引導(dǎo)學(xué)生思考電流在電路中的流動(dòng)路徑和方向,并突破易錯(cuò)知識點(diǎn)“當(dāng)負(fù)電荷發(fā)生定向移動(dòng)時(shí)的電流方向”.通過設(shè)計(jì)這樣的問題鏈解決策略,可以引導(dǎo)學(xué)生主動(dòng)思考和實(shí)踐,從而深入理解電學(xué)原理和規(guī)律.
4.3 建立和諧合作的學(xué)習(xí)氛圍
建立和諧合作學(xué)習(xí)氛圍是問題解決法中一個(gè)非常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在一個(gè)和諧的氛圍中,學(xué)生能夠更加自由地表達(dá)自己的觀點(diǎn)和想法,與同學(xué)進(jìn)行深入的交流和討論.同時(shí),教師也需要給予學(xué)生充分的自主權(quán)和信任感,讓學(xué)生成為學(xué)習(xí)的主人,主動(dòng)參與到學(xué)習(xí)中來.為了營造一個(gè)良好的學(xué)習(xí)氛圍,教師還需要加強(qiáng)對學(xué)生的心理疏導(dǎo)和情感關(guān)懷,注重學(xué)生的心理健康和情緒體驗(yàn).
例如 在講解“光學(xué)”部分的知識時(shí),教師可以組織學(xué)生進(jìn)行小組討論,共同探討光的折射、反射等基本原理.通過小組討論的形式,可以促進(jìn)學(xué)生的交流合作,同時(shí)也能夠鼓勵(lì)學(xué)生主動(dòng)分享自己的見解和思路.在這個(gè)過程中,教師需要發(fā)揮主導(dǎo)作用,巡回指導(dǎo)并參與到小組討論中來,及時(shí)發(fā)現(xiàn)并解決學(xué)生在討論中出現(xiàn)的問題和困難.教師還可以組織一些小組競賽活動(dòng),如:“如何設(shè)計(jì)一個(gè)最省材料的窗戶?”,讓學(xué)生運(yùn)用光學(xué)知識來設(shè)計(jì)和制作窗戶模型.在這樣的合作學(xué)習(xí)氛圍中,學(xué)生能夠積極參與、互相幫助、共同進(jìn)步.
4.4 鼓勵(lì)學(xué)生創(chuàng)新思維
在問題解決法中,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也是一個(gè)重要的方面.在解決問題時(shí),教師應(yīng)該鼓勵(lì)學(xué)生嘗試不同的方法或思路來解決同一類問題.同時(shí),教師也應(yīng)該盡可能地設(shè)置一些能夠激發(fā)學(xué)生創(chuàng)新思維的問題或任務(wù).
例如 “如何用一把尺子測量一個(gè)不規(guī)則物體的密度?”這樣的問題需要學(xué)生運(yùn)用創(chuàng)新思維來解決.學(xué)生可以通過測量物體的質(zhì)量和體積來計(jì)算密度.但是,有些物體的質(zhì)量和體積不容易直接測量出來,這就需要學(xué)生嘗試不同的方法來解決.有的學(xué)生可能會(huì)想到利用浮力知識來解決密度測量的問題等.通過這種方式能夠讓學(xué)生擺脫定勢思維的束縛.
為了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教師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鼓勵(lì)學(xué)生對問題進(jìn)行多角度思考,當(dāng)學(xué)生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法時(shí),教師不要急于評價(jià)或判斷,而應(yīng)該鼓勵(lì)學(xué)生嘗試和探索不同的方法或思路;可以提供相關(guān)資料和信息,引導(dǎo)學(xué)生探索不同的解決方案;引導(dǎo)學(xué)生自主發(fā)現(xiàn)和解決問題;鼓勵(lì)學(xué)生進(jìn)行實(shí)踐操作.當(dāng)學(xué)生提出某種解決方案時(shí),教師可以鼓勵(lì)學(xué)生進(jìn)行實(shí)踐操作,驗(yàn)證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這些措施有助于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5 提供及時(shí)的反饋與評價(jià)
在問題解決法中,及時(shí)反饋與評價(jià)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huán).當(dāng)學(xué)生在解決問題時(shí)出現(xiàn)困難或錯(cuò)誤時(shí),教師需要及時(shí)給予反饋和評價(jià).通過及時(shí)的反饋和評價(jià)能夠讓學(xué)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學(xué)習(xí)情況并及時(shí)調(diào)整自己的學(xué)習(xí)方法和思路.同時(shí),教師也需要對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成果進(jìn)行綜合評價(jià).綜合評價(jià)包括學(xué)生自主完成情況、小組討論情況、課堂表現(xiàn)情況等多個(gè)方面.在反饋和評價(jià)的過程中,教師需要注意以下幾點(diǎn):首先,反饋和評價(jià)需要具有針對性和具體性,不能過于籠統(tǒng)或模糊;其次,反饋和評價(jià)需要具有及時(shí)性和有效性,盡快給予學(xué)生反饋和評價(jià),以便學(xué)生能夠及時(shí)調(diào)整自己的學(xué)習(xí)方法和思路;最后,反饋和評價(jià)需要具有激勵(lì)性和鼓勵(lì)性,肯定學(xué)生的優(yōu)點(diǎn)和進(jìn)步,同時(shí)也要指出學(xué)生的不足之處并給出建議和意見.
5 結(jié)語
問題解決方法在初中物理課堂教學(xué)中具有重要的教育價(jià)值和應(yīng)用意義.通過引入問題解決方法,可以激發(fā)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和動(dòng)機(jī),培養(yǎng)學(xué)生解決實(shí)際問題的能力,發(fā)展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和合作精神.在實(shí)際的教學(xué)中應(yīng)該采取一系列策略來應(yīng)用問題解決方法,包括構(gòu)建真實(shí)、有趣并符合學(xué)生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問題、設(shè)計(jì)有效的問題解決策略、建立和諧的合作學(xué)習(xí)氛圍、鼓勵(lì)創(chuàng)新思維以及提供及時(shí)反饋與評價(jià)等.這些策略的實(shí)施將有助于提高初中物理課堂教學(xué)的質(zhì)量,促進(jìn)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未來的研究可以進(jìn)一步深入探索問題解決方法在不同學(xué)科和年級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以及開展長期的教育跟蹤研究,為教學(xué)改革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持和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
參考文獻(xiàn):
[1]蘇艷.新課標(biāo)視域下初中物理實(shí)驗(yàn)教學(xué)策略探究[J].數(shù)理天地(初中版),2023(18):66-68.
[2]關(guān)紅慧.初中物理課堂情境創(chuàng)設(shè)的嘗試與思考[J].數(shù)理天地(初中版),2023(18):18-20.
[3]李如亮.初中物理教學(xué)生活化情境的創(chuàng)設(shè)[J].數(shù)理天地(初中版),2023(18):30-32.
[4]褚珈寧.初中物理教學(xué)實(shí)施科學(xué)方法教育對策概述[J].數(shù)理天地(初中版),2023(18):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