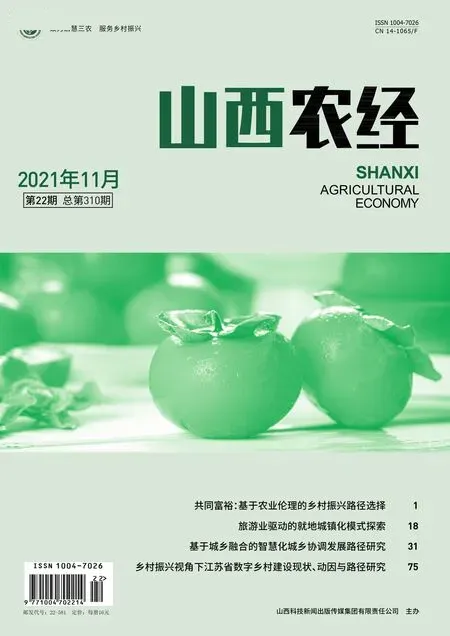蘇南地區(qū)村級治理中的精英流失探究
——基于無錫市Z社區(qū)的調(diào)研
□高 群
(江南大學(xué) 江蘇 無錫 214122)
1 研究背景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日益拉大,使越來越多的農(nóng)村人口走進城市。華中鄉(xiāng)土派的代表賀雪峰教授指出:“精英在農(nóng)村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其類型與村莊記憶共同決定村莊性質(zhì)。”[1]這一群體恰恰是指擁有一定資源優(yōu)勢的農(nóng)村能人、具有較高素質(zhì)的青壯年勞動力以及離開家鄉(xiāng)進城讀書的大學(xué)生和技術(shù)人員等。2006 年,國家全面取消農(nóng)業(yè)稅,農(nóng)民進一步得到解放并紛紛涌入城市,鄉(xiāng)村人才缺失問題日益嚴重。
為加快鄉(xiāng)村社會的全面發(fā)展,縮小城鄉(xiāng)差距,必須采取措施遏制鄉(xiāng)村精英流失這一嚴重問題,同時應(yīng)吸納和培育更多精英投身于鄉(xiāng)村建設(shè)和發(fā)展之中,帶動村民發(fā)家致富,共同建設(shè)鄉(xiāng)村。
2 Z 社區(qū)精英流失的基本狀況
通過查閱網(wǎng)上相關(guān)資料以及訪問當?shù)仡I(lǐng)導(dǎo)和村民,對Z 社區(qū)鄉(xiāng)村精英流失現(xiàn)象有了深入了解。該社區(qū)地處軍嶂山旁,總面積5 km2,隸屬“豐糧倉”之美稱的雪浪街道,下設(shè)1 個安置小區(qū)和6 個自然村。該社區(qū)的地理位置、資源優(yōu)勢和氣候條件比較出眾,非常適合種植農(nóng)作物和果樹。
由于涉及本研究的主體相對復(fù)雜,個體之間差異比較大,在此不便于做定量研究,只能進行定性研究,主要借助深度訪談的方式來了解Z 社區(qū)精英流失的實際情況。主要訪談對象是Z 社區(qū)婦女主任M,其在2004 年軍南村和軍北村合并為Z 社區(qū)之前就已擔(dān)任婦女工作,不僅在村中有較大的影響力、號召力,還對村里變化情況非常了解。
2.1 鄉(xiāng)村精英的流失緣由
中國自古以來以農(nóng)立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tǒng)農(nóng)耕生活方式延續(xù)數(shù)千年[2]。但隨著市場經(jīng)濟因素逐步滲透農(nóng)村,大量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憑借各種“借口”跑向城市。通過與主任M 訪談得知,“近幾年,村里流出的大多是在外經(jīng)商人士、外出讀書流出的人口、因婚姻關(guān)系流出的人口、為追求高質(zhì)量生活流出的人口等”。這些人不僅是鄉(xiāng)村社會建設(shè)的主力軍,還握有一定的社會話語資源,能夠推動鄉(xiāng)村發(fā)展與進步,而現(xiàn)代化和城市化的推進,使鄉(xiāng)村社會的“主心骨”不再留戀鄉(xiāng)村。
2.2 經(jīng)濟精英定居城市增多
改革開放以來,現(xiàn)代化的思想沖擊了鄉(xiāng)村社會的各個角落。在市場經(jīng)濟的沖擊下,村民的思想變得開放活躍,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小農(nóng)思想。農(nóng)業(yè)土地的附加值比較低,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只能維持在溫飽狀態(tài),并不能發(fā)家致富。一些敢闖敢拼、有想法的村民不甘心將自己的發(fā)展前途限制在“一畝三分地”上,他們或到大城市就業(yè),或出去創(chuàng)業(yè),或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大顯身手。村民代表談及:“社區(qū)里住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尤其在自然村,幾乎都是老年人,年輕人已經(jīng)流向城里務(wù)工經(jīng)商了。在家種地又比不上城里掙錢多,生活也不如城里方便,這幾個村子的‘空心化’‘老齡化’都比較嚴重。”目前,越來越多的Z 社區(qū)經(jīng)濟精英有了一定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在城里買房落戶,平時只有周末才回來,不會長期居住。
2.3 留守精英能力有限
我國的鄉(xiāng)村政治精英主要是村支書、村干部等體制內(nèi)人員,他們在社區(qū)的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務(wù)居于核心地位,能夠利用上級政府部門所賦予的政治資源和優(yōu)勢來治理社區(qū)。不同于北方地區(qū)的合村并居的聚集性,蘇南地區(qū)在合村并居后大部分都保持了“安置小區(qū)+自然村”的形式,Z 社區(qū)也不例外。在安置小區(qū)居住的外地人口約占全社區(qū)的1/3,另外6 個自然村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不同地方,社區(qū)工作人員很難照顧到方方面面。當訪問員問及“這些自然村分布如此分散,在日常治理中有阻礙嗎”時,主任M表示有一定障礙,“全社區(qū)3 000 多人,工作人員就只有14 名,而且村和村之間過于分散,工作人員就只能管理大的方面,顧不到細節(jié)方面。社區(qū)要舉辦活動,還得去每個村一一通知,而且老人們也不會用手機。”
3 村級治理在鄉(xiāng)村精英流失背景下的問題
近年來,在農(nóng)村中的鄉(xiāng)村治理經(jīng)營中鮮少有真正的精英出現(xiàn),一般是直接從村民中選舉出較有能力的村民,在農(nóng)村中真正的精英很少,鄉(xiāng)村精英流失現(xiàn)象嚴重[3]。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huán)境中,單靠企業(yè)自身的資源去參與競爭已遠遠不夠。通過戰(zhàn)略采購來獲取和整合供應(yīng)商的資源以獲得競爭優(yōu)勢,是我國生產(chǎn)型企業(yè)的必然選擇。集成化供應(yīng)鏈就是在戰(zhàn)略采購的背景下應(yīng)運而生的產(chǎn)物,是指供應(yīng)鏈的所有成員單位基于共同的目標而組成的一個“虛擬組織”,組織內(nèi)的成員通過信息的共享、資金和物質(zhì)等方面的協(xié)調(diào)和與合作,優(yōu)化組織目標(整體績效)。基于VMI(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模式的集成化供應(yīng)鏈管理是對整個供應(yīng)鏈上的供應(yīng)商、生產(chǎn)商、運輸商、分銷商以及最終消費者的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進行計劃、協(xié)調(diào)、控制等,使其成為一個無縫的連接,實現(xiàn)集成供應(yīng)鏈的整體目標。
3.1 村級治理和發(fā)展缺乏動力
鄉(xiāng)村精英的流失導(dǎo)致鄉(xiāng)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shè)受到嚴重阻礙[4]。經(jīng)濟環(huán)境的自由化造就了一大批經(jīng)濟精英,他們在村級治理中掌握比以往更多的話語權(quán)和發(fā)言權(quán),這改變了以往以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為主體的治理格局。但是,經(jīng)濟精英對家鄉(xiāng)心理認同感和興趣降低,很多公共工程和公共事業(yè)的建設(shè)無法順利完成。當問及“是否樂意回社區(qū)參與公共事業(yè)建設(shè)”時,流出精英的意愿情況見表1。

表1 流出精英參與社區(qū)公共事業(yè)的意愿
在電話采訪中發(fā)現(xiàn),高達87%的流出精英對社區(qū)公共事業(yè)建設(shè)沒有興趣,他們以享受不到便利為由拒絕參與社區(qū)公共事業(yè)建設(shè)。因此,要提高村級治理的成效,就必須為村莊注入新鮮“血液”。
3.2 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緩慢
鄉(xiāng)村精英的流失在經(jīng)濟方面也造成了損失和影響。一方面使很多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政策難以落實,另一方面使農(nóng)村經(jīng)濟失去實踐力量和主體。鄉(xiāng)村發(fā)展的動力和活力取決于鄉(xiāng)村精英的活躍性。
根據(jù)調(diào)查可知,Z 社區(qū)村民多種植果蔬,如桃子、楊梅、橘子和枇杷等,這些作物依靠肥沃的土地和濕潤的氣候長勢旺盛,每年都會吸引大量游客采摘。但是很多年齡大的老人沒有好的銷售渠道,獲取不了市場信息,導(dǎo)致果蔬的出售價遠遠低于市場價格,這是當?shù)仄毡槊媾R的現(xiàn)實問題。
當訪問員問及“老人無法順利出售蔬菜和水果,社區(qū)有幫助過他們嗎”時,主任M表示,“也有想過辦法來解決,村里也辦過合作社,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沒有繼續(xù)辦。”當訪問員問及“您認為目前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最大的困難是什么”,村干部表示,“村里有本事的年輕人都出去城里打工了,社區(qū)工作人員很少,平時處理雜七雜八的事情比較多,只能解決大方向的問題,細節(jié)做不到位。”
目前,在社區(qū)中,主要由老人和婦女從事基本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一方面,他們無法承擔(dān)繁重的農(nóng)業(yè)勞動,更沒有能力找到銷售渠道;另一方面,他們無法利用鄉(xiāng)村中寶貴的資源,因地制宜發(fā)展本地特色農(nóng)業(yè)。
3.3 鄉(xiāng)村文化傳承和精神面貌受損
鄉(xiāng)村治理精英的流失造成鄉(xiāng)村文化建設(shè)滯后[5]。傳承傳統(tǒng)文化需要繼承者了解文化的特質(zhì),進行選擇性地吸收改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代文化融合在一起,實現(xiàn)兩者的融合。在社會文化方面,社會文化精英的老齡化趨勢導(dǎo)致農(nóng)村中很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面臨后繼無人的危險狀況,如剪紙、吹糖人等手工藝已經(jīng)很少有人懂得欣賞和傳承。“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之間碰撞的跡象不斷出現(xiàn),看得出傳統(tǒng)雖然也活著,但是過去的風(fēng)俗和信仰已經(jīng)四面楚歌。”[6]刻根雕和寫族譜是Z 社區(qū)的一大特色,是幾千年來祖祖輩輩生活和生產(chǎn)的歷史沉淀,蘊藏著很多精華。但是現(xiàn)在村里會雕刻根雕的人越來越少,只有幾位老藝術(shù)家會做,年輕人幾乎沒興趣了解。村民代表談及鄉(xiāng)村文化傳承時表示,“凡是有點本事的、有點文化的都出去打工了,對村里這些家里家常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以后不知道還能不能傳承下去。現(xiàn)在村里還會寫族譜,記錄著同宗共族的生活資料,可以將祖祖輩輩記載下來,但不知道會不會一直有人寫下去。”
4 鄉(xiāng)村精英培育和發(fā)展路徑
農(nóng)村精英的流失是隨著改革開放后進城務(wù)工潮出現(xiàn)的,主要是指由于多種原因使農(nóng)村精英由農(nóng)村涌向城市這樣一種“單向度”流動,從而造成農(nóng)村治理中的精英缺失[7]。
4.1 實現(xiàn)城鄉(xiāng)資源公平化,為農(nóng)村創(chuàng)建良好的生產(chǎn)和生活環(huán)境
長期以來,國家采取“重工業(yè)輕農(nóng)業(yè)”“重城市輕農(nóng)村”等政策,形成了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拉大了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在此基礎(chǔ)上,城市資源越來越豐富,并吸引著鄉(xiāng)村精英流向城市發(fā)展事業(yè)、定居落戶,很顯然這不利于鄉(xiāng)村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為此,必須積極推進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和公共事業(yè)均衡化,努力縮小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
首先,加強農(nóng)村基礎(chǔ)設(shè)施,吸納鄉(xiāng)村精英回歸鄉(xiāng)村,投身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
其次,加大鄉(xiāng)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努力縮小城鄉(xiāng)差距,使更多鄉(xiāng)村人口享受到高質(zhì)量、高水平的教育。
4.2 出臺優(yōu)惠政策措施,吸納鄉(xiāng)村精英到農(nóng)村投資創(chuàng)業(yè)
鄉(xiāng)村精英回歸農(nóng)村,最先考慮的就是增加經(jīng)濟收入,其措施有三。
首先,在融資方面,鄉(xiāng)村企業(yè)經(jīng)常由于受到各種銀行和信貸機構(gòu)的“排擠”而不能順利獲得資金,這就要求基層政府在兩者之間積極溝通,盡可能在稅收、貸款、場地、水電等方面提供幫助。
其次,以傳統(tǒng)種植業(yè)為主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并不能帶來高額收入,只能解決溫飽。所以要促進鄉(xiāng)村經(jīng)濟的多元化發(fā)展,細心發(fā)掘本村的優(yōu)勢所在和潛在資源,制定適合本村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策和規(guī)劃。
再次,應(yīng)通過各種途徑從外部引進更多精英人才,從根本上解決鄉(xiāng)村精英流失的問題。
4.3 培育優(yōu)秀鄉(xiāng)土文化和民風(fēng)民俗,重塑農(nóng)民的故土情結(jié)
鄉(xiāng)村精英的流失,使鄉(xiāng)村優(yōu)秀文化面臨著遺失和斷層的雙重風(fēng)險。為此,村里應(yīng)多組織一些活動和搭建相應(yīng)的平臺,努力挖掘優(yōu)秀鄉(xiāng)土文化,并使其滲透到鄉(xiāng)村社會的方方面面。對城市的過度“迷戀”和對鄉(xiāng)村的過度“淡漠”加速了鄉(xiāng)村精英流失,各高校應(yīng)該積極引導(dǎo)大學(xué)生樹立正確的就業(yè)觀和擇業(yè)觀,讓大學(xué)生明白回歸鄉(xiāng)村也是一個良好的就業(yè)路徑。政府應(yīng)加大關(guān)于“傳統(tǒng)民間文化教育”的宣傳,培養(yǎng)和深化大學(xué)生的“鄉(xiāng)村情結(jié)”。
5 結(jié)束語
通過考察鄉(xiāng)村精英流失現(xiàn)象,認為這既是現(xiàn)代化的一大特征,又是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自古以來,鄉(xiāng)村精英作為一座“橋梁”,在國家和農(nóng)村社會之間起著上傳下達的關(guān)鍵作用。但是在城鎮(zhèn)化的浪潮中,城鄉(xiāng)差距的懸殊吸引著大量鄉(xiāng)村精英流向城市。就Z 社區(qū)而言,精英流失已經(jīng)造成了人才主體缺失,以及“空心村”“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問題。同時,更應(yīng)該引起警覺的是,隨著城市化步伐加快,將會有更多鄉(xiāng)村精英離開農(nóng)村、涌入城市,這是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因此,必須正面、積極地應(yīng)對這個問題,因地制宜,對癥下藥,從而采取更多措施促進精英回流和培育更多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