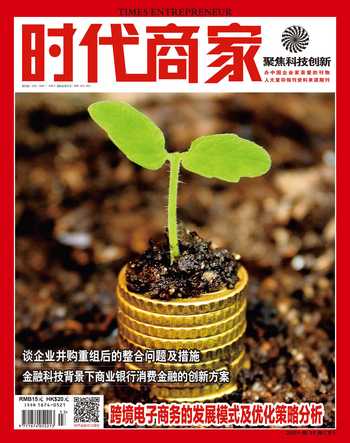數字經濟時代平臺“二選一”行為的監管思考
金琳玉 李將軍
摘要:隨著數字經濟產業的蓬勃發展,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愈發演變成行業內部普遍存在的現象。平臺“二選一”是平臺借助市場力量、平臺規則、用戶數據、算法實現等技術手段,采取多種獎懲措施執行“二選一”行為,以維持和增強平臺市場實力,獲取不正當競爭的優勢。該行為侵犯了消費者選擇權和商家的自主經營權。本文從平臺“二選一”的法律界定,結合近期多家大型互聯網企業的“二選一”事件進行分析,并給出監管方面的可行性建議,旨在營造良好的平臺經濟交易環境。
關鍵詞:數字經濟;平臺“二選一”反壟斷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一、數字經濟
(一)定義
隨著5G、大數據、云計算等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數字經濟在國內各生產部門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明顯。雖然目前對數字經濟尚未有完整清晰的認識,但眾多學者普遍認可《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中給出的界定,即以數字化信息和知識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化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二)特征
馬太效應與網絡外部性是數字經濟的顯著特征。其中馬太效應指隨著發展,行業逐步呈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象。當頭部電商企業依托大量用戶數據和深度學習的算法技術,其平臺自身實力和市場占有率會不斷上漲,逐漸使市場呈現兩極分化的現象。
網絡外部性,指的是連接到網絡的價值大小取決于已經連接的其他用戶數量。簡言之,使用該網絡的人數越多,個體從網絡中得到的效用也越大,即單個用戶效用與用戶總數量呈正相關關系。數字經濟時代下網絡的外部性特征愈發凸顯,平臺企業中用戶數量越大時,對每個用戶的價值也越大,增強用戶的黏性的同時也提高了用戶的轉移成本。
(三)平臺企業的常見壟斷行為
基于數字經濟的特征,頭部平臺企業充分利用了互聯網的馬太效應和網絡外部性優勢,積累了大量用戶數據和網絡資源。當企業具備一定話語權后,個別企業會做出欺壓小型平臺企業、賺取消費者和商家剩余價值的壟斷行為。例如平臺“二選一”、大數據殺熟、差異性交易方式等行為不僅損害相關方利益,還擾亂了市場秩序、打破公平競爭格局,因此完善該行為的法律認定和實施監管措施則尤為重要。
二、“二選一”行為的法律規制
在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發展的新格局下[1],國民消費升級,使“雙11”“618”變成重要的促銷活動,電商平臺企業為賺取更多利潤而涉嫌實施“二選一”的行為頻繁上演。“二選一”行為是指平臺方要求在平臺上的商家只能選擇一個平臺進行交易或合作,或者確保商家給到該平臺的促銷活動必須是全網最低折扣。
對于平臺“二選一”行為的具體實施辦法業內仍存在爭議,“二選一”在反壟斷法中認定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反壟斷行為,一般需要從市場界定、支配地位、濫用行為等幾個角度分步驟進行,該步驟也是本次2021年4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某頭部電商平臺企業處罰決定的分析框架。下面將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具體分析。
(一)相關市場界定
判定平臺是否占據壟斷或支配地位,以及是否排除和限制市場競爭的首要前提,是界定相關市場,相關市場是指經營者所生產的商品或從事競爭的范圍,包含商品市場和地域市場,一般監管方先界定商品市場再界定地域市場,從商品特點、價格、使用功能等進行需求替代和供給替代分析。
以某頭部電商平臺為例,市場監管總局根據《反壟斷法》中市場界定的一般做法,結合數字經濟的特點將相關市場界定為中國境內網絡零售平臺服務市場。從消費者需求替代角度,線上平臺不受物理空間限制,能為消費者提供多種品類選擇,產品與物流鏈連接緊密,購物體驗比線下零售更方便快捷。從供給替代角度,首先二者盈利模式有顯著差異,電商平臺向商家收取交易傭金、推廣廣告實現盈利,線下零售業向商家收取固定店鋪租金盈利;其次二者的轉換成本高,線下轉線上需要達到一定的經營規模和必要的技術支持,進入線上市場的壁壘較高。因此,將該電商平臺的相關市場界定為網絡零售平臺服務市場,且與線下零售商業服務不屬于同一相關商品市場。
(二)支配地位界定
占支配地位是指某企業在相關市場上擁有決定產品價格、產量和銷售等方面的控制能力,占支配地位的企業能左右市場競爭,或不受市場競爭約束。在監管局判斷企業是否占支配地位時,主要從市場份額、市場集中度、市場控制力等方面來裁定。在電商行業中,中國網絡零售平臺市場集中度高且競爭者數量少。該頭部電商平臺市場份額超過50%,2019年HIH赫芬達爾指數即產業集中度達5350。其次,該企業具有較強的市場控制能力,在與平臺內經營者的商業談判中,以格式合同的方式規定傭金費和廣告費,具有很強的話語權,再加上雄厚財力和高新技術條件,使平臺上的商家對平臺的依賴度越來越高。因此,裁定該企業在行業內占支配地位。
(三)濫用行為
電商平臺做出的禁止本平臺商家在其他同類有競爭關系的平臺上銷售商品,這類行為違反《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關于“沒有正當理由,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進行交易”的規定,因此判定該電商企業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三、“二選一”行為的影響
“二選一”不僅是一個法律概念,更是新興產業和傳統企業經營者普遍使用的競爭手段。這樣的競爭方式也不只存在于企業,受疫情影響直播帶貨行業應運而生,某兩名頭部帶貨主播,曾限制商家只能在他本人的直播間上架商品或要求最低折扣。雖然該行為的影響范圍不及平臺企業的范圍廣,但的確損害了商家的相關經濟利益,因此我們應該客觀多角度分析“二選一”行為。
(一)“二選一”的積極意義
“二選一”有利于穩定平臺企業自身的經營穩定性并保持競爭力[2]。由于互聯網的外部效應,當平臺上綁定更多的消費者和商家時,其平臺自身價值就會增大。伴隨著用戶依賴性和轉移成本增加,會形成平臺鎖定效應,因此“二選一”行為能有效增加平臺的自身實力和競爭力。
(二)“二選一”的消極意義
1.損害消費者選擇權和消費者福利
其一,平臺“二選一”行為限制了消費者自由選品的權利[3],當消費者養成到某平臺購買的習慣時,增加了重新選擇商品的成本和平臺轉移成本,易對電商平臺形成負反饋;其二,損害消費者福利,當某平臺掌握一種商品的銷售權時,有可能提高價格或降低優惠力度,消費者承擔了這部分增加的成本。
2.損害商家自主經營權
平臺限制商家不能入駐其他平臺的規定,極大損害了商家的自主經營權,同時也讓商家承擔了經濟損失。商家都會傾向于在多個平臺銷售商品以獲得更多利潤,而平臺綁定商家,必然使商家對平臺的依賴度越來越高,話語權越來越弱。
3.阻礙平臺經濟創新發展
企業“二選一”行為阻礙了商品在不同平臺的流通,影響商品供需的有效匹配。商家不能根據產品特性、用戶特點與渠道來自由選擇不同平臺,或者制定不同的經營策略,抑制了商家的創新與活力。
四、平臺經濟監管的完善建議
(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我國數字經濟和電子商務產業發展仍處于初步階段,對于新興產業的法律規制存在不完善與滯后性,建議相關方從《電子商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多部法律中從公平交易、公平自由競爭的維度,合理區分平臺“二選一”的具體實施情形,搭建法律條款的系統性規制框架[4]。
(二)創新行業自律監管體制
相較于直播賣貨進行“二選一”的個人行為,平臺企業實施“二選一”行為性質更為惡劣、影響更加重大。平臺本身負有維護市場公平、良性競爭的義務,然而憑借掌握大量流量和消費者黏性來規定商家“二選一”,更容易產生商業信任危機,阻礙行業發展。作為大型平臺企業應當規制自身行為,律己而后律人,制定行業自律公約。平臺內部設置內部監管平臺,明確各部門職能劃分,設置最高違規處罰,對于違反公約的行為,與國家監督管理總局協同作出相關處罰規定。
(三)建立平臺經營者信用等級評定制定
平臺與商戶、消費者的信息不對稱一直以來是備受詬病的問題,平臺作為流量和信息的入口,能輕易通過多種渠道獲取消費者信息,商家和消費者被動地依賴平臺所提供的信息,這增大了商家和消費者維權難度。因此,建議在平臺監管過程中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定期對平臺企業的行為進行規制,對其信用進行打分評價[5]。建立平臺經營者失信懲罰機制,將嚴重違反行業公約的企業拉入企業黑名單,限制其再次進入行業內的機會。
五、結束語
理論界和執行界在平臺“二選一”行為的定性及懲罰實施問題上仍存在爭議,由于反壟斷法在新興產業,特別是針對電商平臺的不完善與滯后性,決定了現行法律對平臺“二選一”的規制也陷入了困境。隨著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對平臺企業的壟斷行為界定有困難、平臺未盡公平審慎義務、平臺與消費者和商家的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凸顯。為解決現行監管現狀難題,應盡快完善相關法律對“二選一”行為的定性和懲罰規定;與此同時,平臺應建立自律監管體制、引入第三方機構進行信用等級評定機制等,以便更好地履行監管職責,營造公平的平臺交易環境。
參考文獻:
[1]陳阿興,相佳秀.數字經濟時代電商平臺壟斷治理研究[J].河北地質大學學報,2021,44(03):121-126.
[2]孟烈鋼.循環經濟背景下生鮮食品物流管理研究[J].食品研究與開發,2021, 42(16):229-230.
[3]吳太軒,趙致遠.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的反壟斷法規制——兼論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理論的適用不足[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2(06): 59-68.
[4]譚袁.互聯網平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規制的困境與出路[J].法治研究,2021(04):110-123.
[5]荊坤.淺析電子商務平臺對“大數據殺熟”的監管義務[J].中國商論,2021(13): 31-33.
[6]石靜.鄉村振興背景下貴州特色農產品可持續發展對策研究[J].食品研究與開發,2021,42(15):225-226.
指導老師:李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