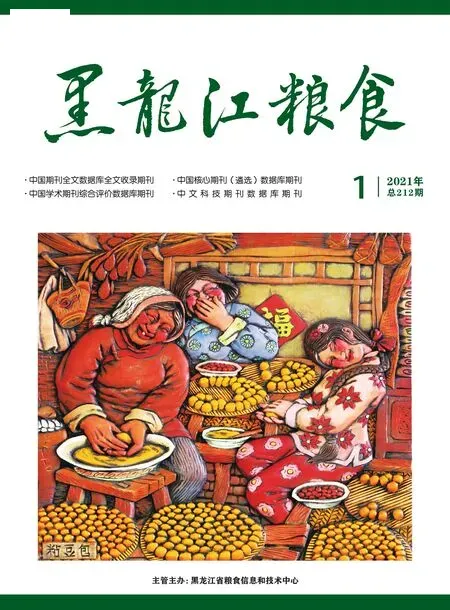王夫之等清代思想家的糧價主張
□ 李 旭
價格是經濟的重要內容。歷史上,清朝的經濟歷經200余年的沖刷與考驗,其間王夫之、龔自珍、楊錫紱、洪亮吉等許多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文人志士發表了很多關于價格思想、糧價主張的觀點和言論,為后人研究當時經濟環境和糧食價格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王夫之:寧“傷末”不“傷農”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字而農,號姜齋,又名夕堂,湖南衡陽人,因晚年隱居于湘西石船山,學者又稱他為船山先生。王夫之29歲起義兵抗清入湘,兵敗。32歲便隱居石船山瑤洞中,寫下《春秋世論》《讀通鑒史》《永歷實錄》等百余書籍,與顧炎武、黃宗羲并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是典型的重農主義者,主張以農為本,以糧為本,吃穿為大,生存為大。“婚喪之用,鹽茗之資,親故鄉鄰之相為酬酢,多有非谷帛之可孤行,必需金錢以濟者。”如農民種出的糧食賣不上價格,則無錢生活,無錢置辦農具,連基本的生活保障都解決不了,更談不上繼續耕種了。因此,他說:“粟貴傷末,粟賤傷農,傷末之與傷農,得失何擇焉。”
王夫之的這種思想,也是當時中小地主反對糧食跌價的思想反映。一方面是害怕糧價太低對農民不利,另一方面又反對平抑糧價,主張糧價自由漲落。在王夫之看來,市場價格的客觀作用不是封建王朝的權力所能轉移的。從“歲兇谷乏而減其價……而以拒商賈于千里之外,居盈之豪民益挾持人之死命,以坐收踴貴之利。罷民既自斃,而官又導之以趨于斃。”等話語中,可知王夫之非常反對人為地壓低糧價。
乍看起來,王夫之的糧價思想有自相矛盾之處,他既反對糧食低價,又主張糧價自由漲落,還認為災年糧食減產糧價走低不足以招徠商賈,這說明王夫之思考的依舊是高糧價既利農又利末。
有些情況下,王夫之贊同根據條件,人為地影響市場價格。“賤則官糴買之,而貴則官糶賣之”,說明他既支持市場的價格自由,又對陳舊的價格體系有所留戀。
龔自珍:一切皆可交換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館,又號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詩人、文學家和改良主義的先驅者。
龔自珍若生于當代,必定是個“閑魚”的忠實用戶。他強調財富的實物狀態,認為貨幣的作用只是便于攜帶,如果給他一部手機讓他逛市場,一定是一副“你掃我還是我掃你”的憨態。龔自珍對物物交換似乎十分著迷,他說:“凡民以有易物,使市官平之。皆以稻、麥、百谷、竹、木、陶、鐵……豬、羊、雞、魚、蒲葦、鹽、酒、筆、褚。使相當,其名田者賦于官,亦用是。百家之城,有銀百兩;十家之市,有錢十緡,三家五家之堡,終身毋口富泉貨可也。”
龔自珍的問題在于一是對貨幣認識不健全,對商品交換的認識不明確。“使相當”“使市官平之”指的是物物交換,但物物交換只是簡單的價值形態,而價值形態無變化不能成為價格形態,物物交換的比例無法“使相當”,市場監督管理局沒招,馬云也沒招。二是對商品缺乏等級概念,一切商品都有品質高低,等級高下,無等級,怎交換?龔自珍如此看待比價,說明他對物物交換的本質是沒搞清楚的。
楊錫紱:價格獨占 皇上點贊
1 7 4 7 年,乾隆向各省督撫征詢米價上漲原因。各地反映的原因很多,但片面性較強。湖南巡撫楊錫紱通過對各省奏復的意見綜合分析,認為自然災害及人為抬價只是表面原因,而主要原因則是買食者多。買食之多,由于民貧。民貧的逐漸形成有四個原因,一是人口增長。多個人多張嘴,而土地又開墾得差不多了,谷物生產量上不來,米價自然漲了;二是日子好了。平時節省的農民日子逐漸好了起來,便開始借貸從事其他活動。待土地收獲后,大半糧食用來還貸,可自留的口食不夠吃,就要去市場購買,買的人多了,糧價自然也漲了;三是田歸富戶。還不起債的農民便要把地賣給富人,富人囤積土地不賣,使得富人土地上種出的糧食非高價而不賣,左手右手一個慢動作,牢牢地把糧價的高低掌握在自己手里;四是倉谷采買。倉谷年年采買糧食,農民手中糧食半數被買走,不夠吃又要去買,也引發糧價上漲。
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以上四種原因也不都是壞事:康乾盛世,國泰民安,人口增長是好現象;日子好了同樣也不能采取措施讓老百姓日子過回去,老百姓不答應,皇上也不能答應;富戶手里的土地多確實有問題,但還未到解決的最佳時機;至于谷倉采買,本來也不宜采買太多。鑒于以上形式,楊錫紱認為糧價上漲和人口增長沒有直接關系,主要原因還是在市場供需關系方面,他抓住了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大興水利使糧食生產倍增,從生產方面解決糧價漲價問題。
“夫一物者,一人市之,價不能增也。十人市之,則價一時頓長;十人求售,價不能多也,一人獨售,則任其高勒矣。” 楊錫紱的這段話和近代獨占價格理念相近,“一人市之”“一人獨售”和過去常說的“物以稀為貴”觀點迥異,當自由市場價格出現問題,高瞻遠矚的獨占價格的提出,獲得了乾隆的認可。乾隆二十二年,楊錫紱任漕運總督,興修水利,接連提出屯田取贖,宜寬年限,糧食摻雜潮潤,經手官員一查到底等措施,接連得到乾隆點贊。(上諭曰:“此奏俱可行。”“此奏確有所見。”)乾隆二十五年,提拔楊錫紱為太子少師,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乾隆三十三年,楊錫紱卒,賜祭葬,謚勤愨(愨què:誠實、厚道)。
洪亮吉:憂民論價 思想超前
洪亮吉作為乾嘉時代的進步學者,其提出的人口增長過速之害,實為近代人口學說之先驅。他從人口的相對過剩觀點出發,聯系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的情況,闡述了他的價格思想。他說:“四民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長,傭書授徒以易食者也。”(《生計篇》1793年)農工自食其力,即使具有商品性生產,但大多數產品仍然是自給;而士、商賈均需贏利謀生而易食,貨幣對他們來說至為緊要。人口的增長卻使得“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人民的生計因此困頓。洪亮吉此觀點清晰地指出了當時農民和城鎮普通百姓因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而導致實際收入下降的問題,這種思想和經濟理論水平在當時是極不尋常的。但他只將原因歸結為人口增長,卻忽視了農業生產問題,這恰恰是楊錫紱所發現和重視的問題。
洪亮吉對工農的定義也是超前于當時那個年代的。史書上所謂“農末俱利、農末俱困、谷賤傷農”等,“農”指的是中小地主,“末”指的是工商業主。洪亮吉則將工農定義為雇傭的工農業勞動者,商賈是活躍在市場中的小商販,這與現當代對工農、商賈的定義是一致的。
“倉稟實、天下安”。王夫之、龔自珍、楊錫紱、洪亮吉等活躍在當時的文學家、思想家雖身處封建社會,但心懷天下,心系百姓,以恒遠的目光觀察廣袤的大地,他們經深思熟慮得出的理論雖帶有一定的時代烙印,難免以偏概全,但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想法和做法,卻帶著特有的風骨和深度,甚至還有些浪漫和憧憬,用他們的方式方法關心蔬菜糧食,關注民眾民生,在歷史的長河中,留給我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