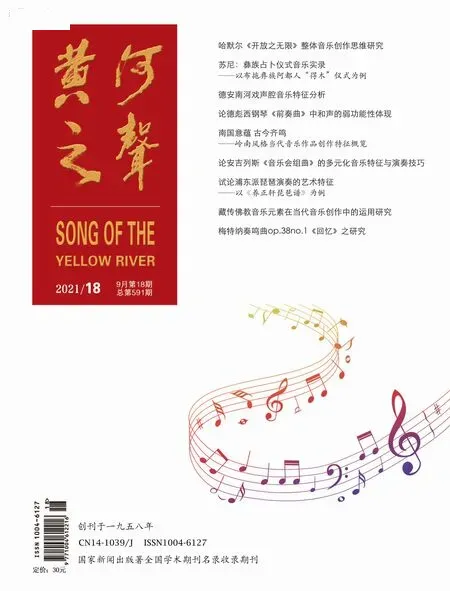論鋼琴曲《童嬉》創作特點與演奏技巧
黃嘉清
引 言
民族音樂文化蘊含了豐富的人類情感,體現了人們豐富多彩的生活。在悠久歷史文化傳統基礎上,哈尼族創造了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音樂,它充分體現了哈尼族文化的內涵和哈尼族的民族精神,哈尼族民歌的種類豐富多樣,其中云南哈尼族童謠“然咕差”是古老的哈尼族兒歌,它曲調的歡快、短小,音域不寬。根據云南哈尼族“然咕差”里的《趕街曲》主題音調由朱踐耳創編而成的鋼琴曲《童嬉》,無論是對原民歌主題音調的繼承、曲式結構的布局安排,還是和聲、復調、織體、調式、調性等音樂材料發展手法的綜合運用等,都體現出了作曲家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創作方法和思想理念。
一、《童嬉》的音樂創作特點
每一首完整的作品都具有不同的曲式結構、調式、調性和各種節奏節拍、織體等音樂特點。正是有了這些要素的組成才能使一首曲子富有靈魂、富于生命力,才能更好地豐富主題,呈現出它原本的美。這些要素的組成也體現出作者高超的寫作水平以及作者對曲子主題的一種獨特的理解。讓演奏者感知到作者的豐富情感。
(一)曲式結構與調式調性的特點
1、曲式結構特點
《童嬉》全曲161小節,是一首帶再現的復三部曲式結構[1],附加引子與尾聲,D商開始的引子部分短小精悍,整個引子部分都是運用了“la、re、mi”三個音組成。用倚音的形式出現,一方面起到了吸引聽眾好奇心的作用,一方面又直截了當得把小孩子頑皮的一面表現出來。接下來又轉換用分解和弦的形式組成,不僅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還巧妙得把小孩子變化迅速,捉摸不透的性格特點體現出來。A部主要是三段體結構,最有意思的是A1段是A段的變化再現,到最后才出現對比段B段。C段采用引子的核心音調發展,低聲部引入長時值音,這首作品從一開始給人的感覺就是激情快樂的,而這一部分就好像給整首曲子起到了一個稍微緩沖的作用,同時也為再現部的出現而蓄滿了能量。讓人忍不住在想是小孩子玩累了稍作歇息的場面。再現部雖然沒有完全一模一樣再現A部的材料,卻也沒有離開過主題旋律以及主干音“la、re、mi”尾聲部分高聲部采用不斷反得相同的音型,低聲部的臨時變化音及不斷的力度變化,把情緒慢慢地推到最高點最終以一個和弦琶音的形式柔和地結束。讓人有種意猶未盡的感受,仿佛還沉浸在歡樂的曲調中。
2、調性與和聲結構的特點
A部開頭以D商調式進入主題,發展到A1段(44小節—57小節)時在原基礎上變化了許多,但已為轉到C商調式作了鋪墊,宮音從之前的C音變為了bB音,這種兩種調式容易產生強烈的對比。給人一種新的聽覺享受,在當時的音樂寫作技法方面是一次大膽的創新。C部的調式變化比較復雜,它的高聲部旋律是D羽調式,低聲部旋律是bE宮調式,bE音同音反復一直持續。到97小節處以一組全音階的形式慢慢下行連接到下一個部分。再現部依然回歸到了D商調式直到了結尾。
《童嬉》的和聲布局則比較簡單,整首曲子的和聲完全都是為了樂曲中的兒童的音樂形象而服務的。和聲中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運用了大量的四度、五度的配置。尤其是在尾聲部分,從140小節到159小節都是如此,開始在140小節是高低聲部旋律相距五度的旋律,然后發展到了旋律聲部之間純四度進行,后面又發展成高低聲部旋律作純四度平行進行。
(二)旋律與織體的特點
1、旋律上的裝飾與加花
《童嬉》這首曲子就是在哈尼族童歌《趕街去》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其中,在《趕街去》的旋律中加上復倚音的點綴,顯得比較華麗且精巧。再加上低聲部旋律的分解和弦織體伴奏以及節拍的變化給這段旋律增添了一絲調皮活潑的氣氛[2]。
2、織體的變化
從第一小節到第42小節的織體形式多以分解織體為主,旋律的主干音“la、re”“mi、la”等以四度上行或者下行的形式分解織體對主旋律進行伴奏。使得旋律更加豐富。43小節到第77小節就改為了柱式織體的伴奏,能夠起到很好地填充主旋律的作用,43小節到56小節運用八度柱式與卡農復調的形式勾勒出一條與主旋律相互呼應的旋律線,同時用這種技法來營造出小孩子相互追逐打鬧的氛圍。61小節到77小節柱式織體級進下行與休止符完美的結合,高低聲部旋律彈奏時不斷拉開的空間感使得情緒逐漸高漲,81小節到107小節的高聲部旋律都是以琶音的形式進行,低聲部旋律都是運用同音反復的方式進行,后面的結尾也是以同音反復的方式慢慢地結束。
(三)節拍與節奏特點
1、變換的拍子
《童嬉》這首曲子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拍子的變換,全曲一共運用了2/4、3/4、4/4、5/4、1/4、5/8、4/8、3/8、2/8等九種拍子。單是這樣還不夠,這九種拍子還得進行頻繁地轉換,甚至一兩個小節就得換一次拍子,這種頻繁地變換拍子使得節奏重音不斷變化,打破了原本節奏的音樂律動,在聽覺上可以起到模仿了小孩子調皮的心性以及喜歡玩鬧的心理特點的作用,同時也給音樂添加了發展的動力[3]。
2、節奏特點
第10小節到第29小節以及第117小節到123小節這兩處明顯運用了復節奏的技法,高聲部旋律與低聲部旋律不一樣的節奏型相互進行,低聲部旋律的節奏型還延續到了下一拍,高聲部旋律不管旋律如何進行,低聲部旋律絲毫不受干擾保持同樣的節奏型進行著,同時復節奏的運用可以達到改變節奏重音,切割節奏的目的,突低高聲部旋律的不同,在體現了演奏者高超的技巧中同時也使得音樂生動有趣,感受到每個音符跳動的美感。用音樂的技法來突出孩子嬉戲打鬧的有趣的特點。在這首曲子中還有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曲子中有多處利用了柱式和弦的織體形式來敲擊節奏,然后由作曲者標上重音記號,也稱為人工重音[4],在57小節到60小節、123小節到128小節、134小節到136小節都運用了這種形式來推動音樂的發展,這種技法多出現在中國的樂曲中,用來模仿中國的打擊樂器,這種技法的使用最大一個特點就是突破了原來的節奏重音。
二、《童嬉》的演奏技巧
一個完美的作品背后必然有許多眾人看不到的努力與汗水。在鋼琴演奏這一領域上也是如此,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蹴而成,這是一個不斷需要積累反復練習的過程。因此,技巧尤為重要[4]。
(一)裝飾音的演奏
《童嬉》的音樂中有許多裝飾音,其中有一種是倚音,這首作品開始的引子就以倚音的形式出現,倚音作為裝飾音的一種又可分為單倚音與復倚音,兩種倚音同時出現在引子中。主要描述兒童活潑的音樂形象。
彈奏這些倚音時既要迅速又要準確。首先要將手和手臂放松,尤其手指更要放松,并且手指的靈活性要好。其次倚音所占的時間非常短,要求短促、輕快、均勻、清晰,不能模糊。要把這一部分單獨抽出來練習。
《童嬉》的音樂中還有另一種裝飾音是琶音,琶音是和弦的另一種形式,也是分解和弦的一種,彈好琶音手指要積極主動彈奏,做到迅速、靈敏、準確。手腕必須靈活地協調配合。要保證每個音落下去的力度要均勻,音樂的線條要連貫,要彈出流暢,不卡頓的感覺。
(二)雙音的彈奏技巧
雙音在鋼琴中是比較常用的一種技巧,它能使音樂飽滿充足,能改善單一旋律帶來的空洞感。并且它還可以使情緒更為強烈,在推動情緒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在《童嬉》的最后一個片段,慢慢地加入雙音的彈奏,使情緒不斷上升到達一個高潮點。彈奏雙音時候要注意避免聲音不整齊,首先要放松手腕和手臂,然后手指要站立好,不要出現塌指的情況,其次彈奏雙音的時候一定要把手指放到琴鍵上,要把著力點放在手指尖上,然后一起落鍵,兩個音同時響起。
(三)踏板的處理
在鋼琴演奏中最常用的就是延音踏板,延音踏板又可分為重音踏板、預備踏板和音后踏板這三類彈奏方法。《童嬉》中運用的是重音踏板,即在強拍上踩下。踏板的使用也是有著一定的技巧的,右踏板用右腳輕輕地放在踏板上,然后不需要把踏板踩到底,差不多踩到二分之一就可以了。如果踩得太重,會容易產生雜音,從而影響到鋼琴的音色。
(四)力度與速度的處理

速度即音樂進行的快慢程度,《童嬉》開始是每分鐘132—138拍的速度,結尾處出現的rit(漸慢),象征在緩緩漸慢的過程中結束。速度要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還有前四小節引子要運用的Moderato(中板)的速度等,中板的速度屬于一種不快不慢的速度,大概是每分鐘88拍的速度,演奏者在訓練的時候搭配節拍器一起訓練,從慢速開始練起,對好節拍器,有序地進行練習。
(五)跳音的處理與表情術語的處理
在80小節處出現了一個表情術語espress(有表現力的)。表情術語在樂曲中也是起著重要的作用。提示演奏者要富有情趣地彈奏這一部分,加入自己對這首曲子的感受,漸漸的與樂曲相融合,把自己最擅長的部分自信地表現出來。彈奏中不能太過于生硬,帶有感情地演奏
結 語
朱踐耳先生以自己優秀的創作能力給中國的音樂創作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在這個多元化的世界里剛好體現了朱踐耳先生兼容并蓄的特點。同時朱踐耳先生對于中國民族音樂的繼承與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本文通過對朱踐耳先生作品《童嬉》從創作特點以及演奏技巧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使得我們更深一層了解《童嬉》以及背后的意義。并通過這一首作品來讓大眾認識民族音樂,證明了民族音樂并不是一個個體獨立的存在,它是可以融合的并且還能保留它原本的魅力。因此作為一名音樂愛好者,我們更有必要去收集大量民歌并且把它們發揚出去,讓更多人,甚至是全世界的人都能了解民族音樂,感受民族音樂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