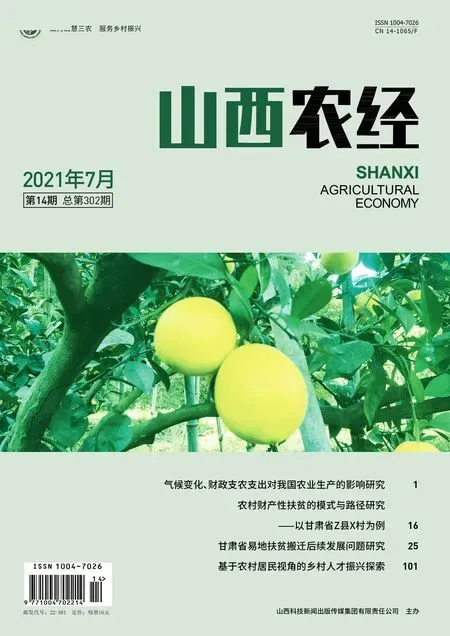耕地與基本農田“非糧化”問題的現狀、成因及對策
□周 霞
(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糧食安全事關國計民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扛穩糧食安全的重任,穩步提升糧食產能。2020 年11 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防止耕地“非糧化”穩定糧食生產的意見》,明確提出“堅持問題導向,堅決防止耕地‘非糧化’傾向、強化激勵約束,落實糧食生產責任”。防止耕地“非糧化”的關鍵舉措是扶持種糧大戶的發展,從根本上解決“誰來種糧”的問題,切實保證“飯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1 耕地與基本農田“非糧化”現狀
據有關部門數據統計,2010 年我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11 695 千hm2,此后播種面積連續6 年增加,2016 年播種面積達到最高峰,共計119 230 千hm2,2016 年后連續3 年糧食播種面積小幅下跌。2018 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17 039 千hm2,2019 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16 064 千hm2,相比2018 年減少了975 千hm2[1],下降0.8%。2020 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116 768 千hm2,比2019 年增加704 千hm2,增長0.6%。
孔祥斌教授通過與11 個省、22 個市、44 個縣的自然資源農業農村主管部門進行座談,并對110 個村鎮372 位農戶進行了深入訪談得出,我國耕地“非糧化”現象呈現逐步擴大趨勢。通過實地調查并結合統計數據可以初步判斷,目前我國耕地“非糧化”率約為27%[2]。
進入新時代以來,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越來越高,我國糧食安全面臨新形勢、新任務以及新挑戰。耕地拋荒、耕地從事非農建設問題日益嚴峻,如何切實有效保障糧食產量、穩定糧食生產面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2 耕地與基本農田“非農化”問題的表現
近年來,一些地區的農民在耕地上栽植了大量楊樹和一些風景樹,嚴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不僅造成耕地被占用,而且在栽樹的農民和不栽樹的農民之間埋下很大的矛盾隱患。
2.1 種糧效益低,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
農民種地積極性不高,是社會關注的焦點。隨著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許多人不再“靠天吃飯”,出現了“70 后不愿種地,80 后不會種地,90 后不談種地”的說法。據實地調查測算,水稻種植凈收益為600~700 元/667 m2,與其他經濟作物相比,收益相對較低,無法激發廣大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農民更傾向于種植其他經濟作物,甚至將耕地改造成魚塘、池塘等,使耕地與基本農田“非糧化”現象更加嚴重[3]。
2.2 違法違規占用耕地,從事非農建設
日前,我國出臺了一系列嚴格保護耕地的政策措施,明確了“守住18 億畝耕地紅線”的意義。“實現糧食基本自給,保持農村社會穩定”是我國實現糧食安全的重要保證,耕地數量是糧食總產量的根本保證。但是仍存在有的地方違規占用永久基本農田綠化造林,有的在高速鐵路、國道省道、河渠兩側違規占用耕地超標準建設綠化帶等比較突出的耕地“非農化”行為。這類行為不僅會對土地資源造成巨大的破壞,當占用耕地達到一定程度時,如果人口持續增長,將會出現“城市病”。我國耕地面積已從1995 年的1.3 億hm2減少到2008 年的1.2 億hm2,人均耕地僅有0.09 hm2,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增地減”已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最突出的矛盾。
2.3 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現象日益嚴峻
近年來,我國城鎮化程度越來越高,民營經濟發展迅速,伴隨著小微企業大量出現,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農村勞動力紛紛涌向城市,人們也更向往城市的生活,越來越多的人更愿意在城市扎根,農村土地拋荒現象顯著,形成了“有地無人種、有人沒地種”的不平衡發展局面。隨著城市化、市場化進程加快,農業發展問題也面臨新的瓶頸,傳統的小農經營無法應對市場的變化,不能適應現代化市場的需求。我國對糧食的需求并未減少,農地流轉中的“非糧化”現象直接影響糧食生產,危及我國糧食安全,甚至引發了一系列經濟、社會、生態問題[4]。
3 耕地與基本農田“非糧化”問題的成因
3.1 糧食生產成本逐年提高,糧經作物利潤差日益拉大
與種植棉花、瓜果、蔬菜、花卉、苗木等經濟作物相比,糧食生產收益較低,農戶種植積極性不高。根據調查,2020 年種稻谷的成本約為800 元/667 m2,水稻產量約為500 kg/667 m2,收購價按2.7 元/kg 計算,加上政府水稻補貼200~300 元/667 m2,農民種植稻谷的凈收入為700~800 元/667 m2,收益較低。
近年來,土地租金、農資價格、勞動力成本均在上漲,糧食生產成本逐年提高,糧經作物利潤差日益拉大。如今縣級市、地級市的工業、第三產業日益發達,民營企業日漸興起,吸引了許多的農村勞動力進城,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現象日益嚴峻。
3.2 城市化進程加快,占用耕地現象日益嚴重
隨著城市現代化進程加快,城市商業用地、工業用地、住宅用地等日益短缺,這就出現了許多占用耕地從事非農建設的現象。人們生活觀念發生變化,許多回鄉的人利用耕地、基本農田修建別墅等,造成大量耕地被占,嚴重制約農業發展,威脅我國的糧食安全。
3.3 農村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誰來種糧”問題日益凸顯
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以來,農民自己承包土地,催生了一大批種糧大戶。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農村的大量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就業,留在農村的老人、婦女、兒童無力承擔種糧的重任,導致農田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影響糧食產量。隨著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農村耕地拋荒問題嚴重,“誰來種糧”這個問題越來越凸顯[5]。無人種糧將直接造成我國現有的糧食產量不能養活日益增長的人口,最終威脅國家糧食安全。更重要的是,隨著鄉村土地流轉日益推進,越來越多的土地被承包商用來建設大棚種植蔬菜或者改造成池塘養魚、蝦等,這對耕地資源造成一定的浪費。
4 遏制耕地與基本農田“非糧化”的對策
4.1 優化惠農補貼政策,提高種糧大戶生產積極性
近年來,國家出臺了許多惠農政策,包括農業機械用具補貼、糧食種子補貼以及小麥玉米等農作物補貼。但這些惠農補貼展現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特點,對提高我國農民種糧積極性沒有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根據對常德市部分村民的調查,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增加補貼,提高種糧大戶生產積極性。
第一,提高育秧補貼。繼續實施早稻集中育秧專項,補助育秧設施建設和種子、農藥、秧盤等物資,并新(改)建標準化育秧基地,推動早稻生產和水稻“擴雙增面”,進一步穩定水稻生產。
第二,積極推廣“十代”種糧模式。湖南省一些地方探索形成了代育秧、代耕整、代插秧、代管理、代防治、代收割、代烘干、代倉儲、代加工、代銷售等“十代”模式,既有效解決了小農戶“誰來服務”的問題,又促進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提高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應對“十代”種糧模式進行宣傳,鼓勵、支持、引導其他地方開展“十代”種糧,形成規模效應。
第三,設置對種糧大戶、種糧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專項補貼。對種糧大戶和種糧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摸底排查,合理規劃布局,形成水稻、小麥、玉米生產片區,減少成本,增加規模效應。
4.2 嚴格監控耕地與基本農田面積,嚴禁違規占用耕地
糧食問題事關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耕地與基本農田是糧食生產的基礎和保障,應始終堅持耕地保護優先、數量質量并重的原則。
第一,不斷完善占用耕地法律法規。嚴格控制違法違規占用耕地情況,一旦出現必須嚴肅處理。
第二,壓實責任、層層推進。建立省、市、縣、鄉、村五級耕地與基本農田監管網絡,對于違法違規占用耕地情況,及時發現、及時制止、及時處理,該拆除的要堅決拆除、該沒收的要沒收、該問責的要問責,對違法違規占用耕地問題做到“零容忍”。
4.3 培養青年骨干種糧大戶
種糧大戶作為保障糧食安全的主力軍,對國家糧食安全至關重要。
第一,加強對種糧大戶的政策宣傳。對種糧大戶補貼政策進行詳細解讀,引導農民知悉種糧的效益。
第二,充分與現有種糧大戶進行溝通,了解他們的需求和面臨的困境,解決存在的現實問題,鼓勵種糧大戶繼續帶領其他農民種糧。
第三,各類高校與種糧大戶合作,開展產學研深度融合教學模式,協調種子企業、農機企業、生物醫藥企業與種糧大戶的合作,推進水稻種植、管理、生產、銷售、研發等服務,重點支持打造糧食功能產區水稻生產社會化服務示范樣板,全面提升糧食生產效益。在培養種糧大戶的過程中注重培養青年種糧大戶,培養一批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骨干種糧大戶隊伍,實現“良種優儲、急種急用、供求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