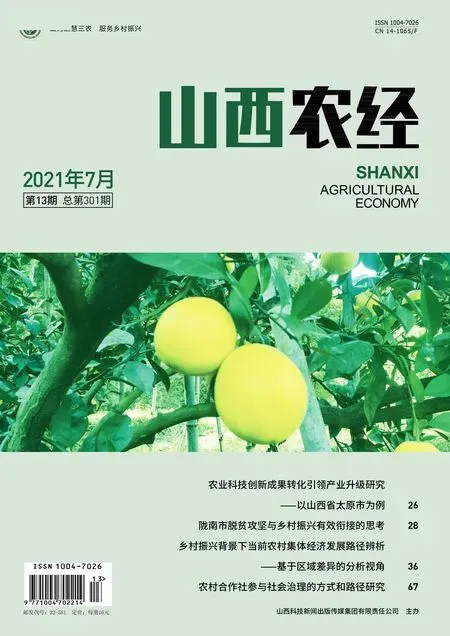賦權與增能:后脫貧時代社會工作參與農民主體性構建研究
□韓明磊
(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的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后脫貧時代,絕對貧困已經被消滅,但可持續脫貧、返貧風險和脫貧戶的茫然成為了扶貧工作新的挑戰[1]。
發揮農民主體作用不僅是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必然要求,也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必然選擇。已有研究主要聚焦農民主體性的重要性和發揮方式,對引入社會力量參與農民主體構建的研究不足。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及其助人自助的理念與農民主體性構建天然契合。
賦權與增能為社會工作參與農民主體性構建提供了新的視角。以此為切入點,探析社會工作介入路徑與措施,從而發掘農民主體認知、提升農民自主性、提高農民能力,使農民主體性在新脫貧階段得到更全面展現。
1 貧困治理中的農民主體性
1.1 農民的脫貧意識
在思想意識層面,貧困農民主體性具體表現為貧困認知的萌發和脫貧意識的覺醒,這既是確保反貧困效果優良穩定的關鍵,也是構建農民主體性的基礎。意識的能動作用是農民自覺發展的助燃劑。
1.2 農民的角色與權利認知
農民的角色與權利認知是主體性的顯要表征,是農民發揮能動作用的外盾。農民不僅需要具備充分的自覺意識,還需在脫貧過程中對自身角色與權利有準確認知,從而承擔相應責任和義務,激活權利意識,合理利用權利,以提高脫貧的穩定性。
1.3 農民的能動創造力
從行動角度出發,農民的能動創造力是主體性建構與發展的引擎。空想是畫餅充饑,實干才是硬道理。農民應以脫貧意識為推動、以權利使用為護盾,借力于自身及外界資源,進而發揮能動作用,創造脫貧發展空間,擺脫貧困現狀。
2 農民主體性面臨的多維困境
2.1 農民脫貧意識消怠
在扶貧工作中,經常存在貧困農民的消怠言論,農民主動或被動把貧困標簽當作默認事實,這是一種自我否定的暗示,加之長期以來農民受文化、經濟、資源等條件的限制,因此農民極易產生習得性無助。懼怕風險、過于追求穩定、安貧的心態使農民在脫貧過程中表現出迷茫困惑的消極狀態,缺乏參與脫貧的積極性。在后脫貧時代,農民的主動脫貧意識仍待深度激活。
2.2 農民主體角色與權利認知偏差
一方面,國家扶持是脫貧的重要舉措,解決了貧困治理中的諸多問題,但部分貧困農民在脫貧過程中逾越道德原則,謀求非合理的政策福利,一味等、靠、要,單向消耗國家資源,增加了自身的惰性。貧困治理是國家的重要戰略,農民作為脫貧對象,應具備社會責任感和自我使命感。另一方面,部分農民在脫貧行動中未準確定位自身角色,不僅對自身責任與義務的認知存在偏差,同時造成主體權利意識缺失,在脫貧行動的計劃、制定、管理、監督等環節主動放棄話語權和參與權,淡化了自身主體性角色,影響了脫貧質量與效果[2]。
2.3 農民主體性能力架構缺失
阿馬蒂亞·森認為,貧困應被看作個體基本可行能力被剝奪,而不僅是收入低下。基于認知之上的行動能力是農民在貧困治理中應具備的關鍵要素。由于個人、家庭和外界等綜合因素,導致農民在脫貧過程中出現能力不足的狀況。在個人層面,農民整體文化程度相對較低、專業技能欠缺、資源利用能力不足。在家庭層面,貧困農民家庭積貧積弱,疾病、教育、家庭文化等因素弱化了貧困家庭的多維功能。在外界層面,農民群體具有同質性,固化了農民的思維與能動性,致使農民群體對周圍可控資源的利用能力不足,缺乏創新創造能力,呈現發展乏力、群體間認同與支持不足的特點[3]。
3 賦權與增能的引入
賦權與增能是社會工作的重要理論之一。拉帕波特認為賦權是指無權、弱權和失權的弱勢群體通過持續性使用外界資源的權利而減少無權感,進而獲取權利以實現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動態、跨層次的改變過程。增能又稱培力、賦能,是指個人在與外界互動的過程中,通過發揮個體自身的自主性,獲取更強的對生活空間的掌控能力和自信心,提升利用資源和機會的效能,進一步助力個體獲得更多能力的過程。
賦權與增能密不可分,二者相互配合,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服務。賦權與增能功效的發揮既需要外部力量的協助,也需要內部優勢的挖掘與潛能的激發,是一個雙向共同發力的作用機制。
在貧困治理中,農民主體性缺失的原因是農民應有的中心角色意識、參與權利、能動能力等發展要素被農民自身忽略或被外界剝奪。農民主體性構建的過程,一定程度上是對農民賦權增能的過程,也是使農民主動參與到改變自身處境的過程。賦權與增能對弱勢群體所處的困境具有針對性,因而賦權與增能的理論作為社會工作的思維,與農民主體性構建自然契合。
4 社會工作參與農民主體性構建的路徑探析
針對農民主體性面臨的困境,引入賦權與增能,結合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以優化農民自覺意識、自主權利、自為能力為目標,探索社會工作參與農民主體性構建的路徑,提升農民脫貧與發展能動性。
4.1 賦權與增能:個案工作的介入
針對個別農民脫貧意識消怠、脫貧動力不足、缺乏自信心的問題,調整農民心理、重構自我認知、激活農民自覺性是關鍵。農民個體情況有差異性,個案工作則可提供個別化的支持與服務,進而對農民個人的意識觀念賦權與增能。一方面,社會工作者通過觀察、訪談等方法,遵循真誠、同理心、接納等原則,與農民建立良好的關系,取得農民信任后,了解農民真實的處境與想法,協助農民探尋角色認知偏差、自我邊緣化問題的根源。另一方面,社會工作者應扮演引導者角色,對農民開展面對面扶貧政策宣傳,引導農民正確看待國家扶貧政策,扭轉其消極態度。社會工作者可借助影音資料對農民進行觀念教育,使農民正確看待其自身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協助農民轉變消極的傳統觀念,提高農民脫貧發展的斗志與自信心,為農民主體性構建奠定精神基礎。
4.2 賦權與增能:小組工作的介入
農民群體具有一定同質性,通過小組工作可對農民群體賦權與增能,從而提高其脫貧技術與動力,幫助農民構建主體自為能力。農民主體能力的強弱,影響著農民參與脫貧發展的強度與深度。一方面,社會工作者可從優勢視角出發,組建互助發展小組,挖掘農民群體及其所處環境的優勢,強化農民群體的自我權能意識。另一方面,針對農民缺乏認同感、發展脆弱性的問題,社會工作者可組建農民支持小組,開展小組活動并指導和鼓勵農民分享自身經歷、脫貧經驗與想法。通過溝通互動,使小組中的農民產生情感共鳴、共享資源信息、學習他人經驗,建立起能夠相互理解的共同體關系,助力農民構建社會支持網絡,從而增強農民脫貧韌性,提升應對困境與風險的抗逆力。
4.3 賦權與增能:社區工作的介入
農民受知識、自主意識、能力所限,在參與貧困治理等公共事務時容易缺失話語權、選擇權、參與權,使農民主體角色處于邊緣化狀態。社區是農民共同生存、發展的主要空間,同時是農民參與公共事務、實現權利的關鍵平臺,因此可運用社區工作為農民賦權與增能。一方面,社會工作者可通過召開宣講會等活動動員農民,激發農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農民在參與社區事務、貧困治理的同時深挖自身潛力,引導農民主動承擔自身脫貧發展的責任與義務,不斷強化農民權利自主性。另一方面,社會工作者還可協助社區建立脫貧發展議事平臺,尊重和維護農民權利,借助多種途徑組織農民參與到貧困治理工作的具體環節中,讓農民在參與中持續提高自身權利意識和使用權利的能力,同時使農民獲得歸屬感和成就感,進而形成農民主動表達利益訴求和主動維護社區發展權益的良性發展體系,在營造共建共享社區的過程中不斷構建農民主體性。
5 結束語
經歷脫貧攻堅后,農村經濟和社會得到了大發展。后脫貧時代的到來推動貧困形式發生新變化。貧困尚未完全終結,經歷脫貧攻堅后的農民應該對自身的角色和責任有更深刻的認識。農民主體性是應對返貧風險、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關鍵。賦權與增能理論、社會工作皆與農民主體性構建存在契合。通過社會工作參與賦權與增能可以提升農民的自覺性、自主性和自為能力。應助推農民大力發展農村產業和經濟,提高農民總收入和可支配收入,防止農村返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