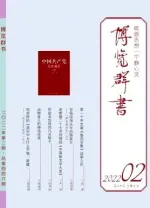我與北大風保系的青蔥歲月
黃雪昀
9月9日是孫老師的生日,而第二天正好是教師節,因此,孫老師常開玩笑說,她是為當老師而生的。忘記了是從哪一年開始,反正是好多年前,在每年的9月9日這一天,孫老師歷年所帶的碩士、博士、博士后和訪問學者們都會盡可能地趕回北大一聚。在這里,不論你是身居高位的司局級領導,還是叱咤商界的企業老板,抑或是還在讀研的北大學生,大家聚在一起只有一個身份,就是孫老師的學生。大家坐在一起都很輕松,就是回來看看老師,見見許久未謀面的同門,聊些家長里短。這一天已儼然成了我們心中的一個節日。當得知今年出于疫情防控的考慮取消了“九九聚會”時,我還情不自禁的哀嘆了一句“太遺憾了!”。幸而《博覽群書》的山峰老師聯系我們幾位同門,就孫老師最新出版的《珍惜——跬步集續》(以下簡稱《珍惜》)寫一點個人感受,就當作以另一種形式慶祝今年的九九聚會吧。
1994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保險系(現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1998年我以班級第一的成績保送成為孫老師的碩士研究生;2021年是我從北大畢業正好20年。這本《珍惜》集中所收錄的孫老師的演講、訪談和隨筆盡管都是在我離開北大之后的,但翻開這本書,字里行間投影在我心中的仍是那位熟悉的恩師,一如往昔。而北大風保系則早已從當年那個被戲稱為“無學生、無教材、無課程”的“三無”專業,發展成為國際一流的風險管理與保險學前沿陣地。
入校以后,我才得知這個專業是1993年才設立的,而我們則是第一批招收的本科生,用今天“時髦”的語言來形容,就是我們一不小心成了北大保險專業的“創一代”。與其他專業都是由系主任與系里的老師一起安排迎新活動不同,我們收到的是孫老師從美國發來的一封歡迎新同學的越洋電報,因為當時孫老師作為新成立的保險系主任還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進修學習。這讓大家既有些新奇,也對這位尚未謀面的系主任有了一絲神秘感。從其他老師那里,我們得知孫老師當年已經是“北京大學首屆優秀中青年學術骨干”、國內經濟學領域炙手可熱的知名中青年經濟學家。1994年第8期《神州學人》雜志上一篇文章甚至稱孫老師為“經濟學界最紅的‘半邊天”。從這樣一個如日中天、前程似錦的位置轉去一個“前途未卜”的新專業,除了心中那份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之外,我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釋。
要將一個新的專業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當時恐怕最棘手的是專業師資力量的匱乏。但這絲毫沒有成為降低學生培養標準的借口。“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是孫老師時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我們當年的專業課程設置借鑒了當時美國一流保險專業院校的最新課程安排,很多專業課的授課老師都是孫老師從校外請來的該領域當時最權威的專家,例如:教授我們風險管理課程的是來自美國的賴志仁教授,教授我們保險法課程的來自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陳欣教授。除了授課老師采用“請進來”的方式,考慮到保險學是一門實用性強的應用學科,孫老師在系里發展初期就力主邀請境內外知名保險機構的資深專家來系里與同學們交流,分享他們在相關領域的真知灼見。與經濟學院其他專業相比,我當年絲毫沒有感受到因為專業老師人手不足所帶來的捉襟見肘,反倒是覺得自己非常有幸能與這么多世界各地優秀的專家交流,開闊視野,增長見識。由此,劣勢反而變成了優勢,使保險專業從一開始就建立在一個很高的起點之上。

一個系能否成功,還離不開他所培養的學生的素質。孫老師總是不遺余力地為同學們創造和爭取各方面的鍛煉機會。我本人感受最深的是我在攻讀孫老師的碩士研究生時發生的兩件事。
那是我剛開始研究生學習不久,有一天孫老師問我,是否愿意給97級的本科生講授《保險學》這門專業基礎課。我原本以為只是作為助教參與一些課堂討論、作業批改等工作。但孫老師說:“不,是從頭到尾整個學期的課程講授都由你一人完成,當然,這個過程中遇到問題可以隨時來找我商量,但你是負責這門課的老師。”這著實讓我有些吃驚,因為在此之前,我還沒有聽說經濟學院有哪位在讀碩士研究生能夠給北大的本科生講授專業課程而且是完整一個學期的課程。我惴惴不安地跟孫老師說:“我自己這門課學習的時間都還不長,怕講不好。” 看到我的忐忑,孫老師語重心長地說:“你來講這門課會有你自己獨特的優勢,那就是你具備學生的視角,你了解站在學生的角度對于第一門保險專業課他們會有哪些疑問,他們希望從這門課學習到什么,他們喜歡什么樣的講課方式。”聽到這句話,我開始回想自己的學習過程,覺得有些道理。為了堅定我的信心,孫老師還給我吃了“定心丸”:“如果你沒講好,這個責任我來擔。”不僅如此,為了讓我在著裝上能與學生有些區別,孫老師還特意帶我到她家中,讓我從她新購置的衣服中隨意挑幾件自己喜歡的。從北大畢業的這20年,當年的衣服早已因為身材變化不再適穿,我也不記得自己搬過多少次家,清理過多少次不用的舊衣物,但當年孫老師送給我的那兩件衣服,還一直保存在我的衣柜里,從來不舍得遺棄。盡管畢業后我沒有選擇從事教師的職業,但孫老師那種不拘一格培養年輕人的勇氣和擔當仍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另一件事則發生在2000年初。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國就是當年去美國舊金山參加風險與保險管理協會(“RIMS”)的年會及Anita Benedetti學生參與項目。2000年的一天,孫老師收到RIMS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RIMS稱每年Anita Benedetti學生參與項目會邀請一些優秀的保險或風險管理專業在校大學生參加協會的年會及相關的系列活動,孫老師可以安排學生提交相關的申請資料。孫老師于是通知我和另外一名研究生著手準備相關資料并發給了RIMS。然而,幾天后,RIMS突然告知孫老師,他們的學生參與項目僅向北美地區的學生開放,他們在收到我們提交的資料后才發現原來我們是在中國,這不符合他們的項目要求,之前那封郵件發錯了。原本以為這個事情肯定就到此為止了,但令我沒萬萬沒想到的是,孫老師對我們說:“我會給RIMS發一封郵件,再盡力替你們爭取一下。”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事情居然真的發生了轉機。幾天后,RIMS回復了郵件。在信中,RIMS提到,他們被孫老師的為了學生據理力爭的精神和“言而有信”的師德風范所感動,因為孫老師在給他們的回信中提到,做老師要為人師表,如果就用一句“搞錯了”來回復學生,那學生們將來還如何相信老師跟他們說的話呢?最終,RIMS表示他們將繼續公正地審核我們提交過去的資料,如果我們的資料符合標準,他們將邀請我們赴美參加相關活動。正是這次難得的赴美學習交流的機會,讓我對保險以及風險管理專業有了全新的認識,增強了我對專業的興趣,進而對于我之后決心在保險領域從業的選擇有很大的影響。
孫老師不僅為了保險專業學科建設殫精竭慮,也非常重視同學們的品格培養。人們常說“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認為孫老師是其中的楷模。我們那一代學生在上高中之后的目標就是單純的好好學習考上最好的大學,對于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教育的重視程度與考試成績相比相形見絀。進入大學后,考試成績的重要性相對降低了,同學們有了更多的時間來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大家對于畢業后的目標又往往非常模糊。在這個“混沌”時期,我們從老師那里聽到、看到的,對于我們未來人生道路的選擇在潛移默化之間便有了非常大的影響。
在《珍惜》所收錄的孫老師的演講中,曾數次提到“要珍惜內心的渴望”。在今天看來,這恐怕是我畢業20年來感觸至深的一句話。與國內絕大多數精算師都是從大學時期開始精算考試并順理成章成為精算師不同,我進入精算領域并非有意為之。我在保險行業最初的工作是在一家再保險公司當客戶經理,為我的客戶,也就是國內的保險公司提供再保險的解決方案。在工作過程中,我越來越發現在與客戶溝通的時候,經常會有一些專業術語,例如:準備金、新業務壓力我不理解。在向公司同事請教時,我了解到一些國外精算考試教材對這些詞語有比較深入的解釋。因為不滿足于對于客戶需求的一知半解,我借來一些精算教材開始自學,最初只是希望在日后的客戶溝通中能夠更加游刃有余,對于成為一位精算師則完全不在我的計劃之內。在自學了前兩門精算課程后,出于檢驗自己自學成果的目的,我試著參加了精算師資格的最初兩門考試。沒想到考試非常順利。隨著自學的深入,我發現自己對于保險業務的理解更加透徹,這更增強了我對精算的興趣。正是這一興趣,使我甘愿在6年漫長的時間里,每天下班之后犧牲掉幾乎所有的個人時間來完成全部的北美精算師職業資格考試,成為北美精算師協會的正會員(“FSA”)(全球平均完成全部考試成為FSA的時間大概是7年)。這些年我經常會遇到一些掙扎于自己是否還要繼續完成艱苦的精算師資格考試的年輕朋友,每當此時,我都會問起他們當初為什么決定要做精算師,他們大多的答復都是“聽說精算師的平均收入高、行業需求大、就業前景好、工作穩定”,這些都是些外在的因素而非發自內心的喜愛。我也許是有些杞人憂天,但我的確不知道他們的精算之路能堅持多久。
100多年前,蔡元培校長為北大塑造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魂。20多年前,孫老師則給風保系賦予了一種獨特的氣質,一種你縱然已離開很久但心底最深處仍保留的一抹暖意。曾經有一位保險業內的資深精算師問我,到目前為止覺得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是什么階段。毫不猶豫地答到,是在北大讀書的7年時光。但當她繼而問我,對北大感觸最深的是什么,我當時卻一時間找不到特別合適的詞語來表達,直到幾年前我在看電影《無問西東》時忽然被其中的一句臺詞深深觸動:“這個時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從自己心底給出的真心、正義、無畏和同情。”感謝北大和孫老師在我心中種下的“真心、正義、無畏和同情”的種子。即使前路曲折,我仍然愿意成為那個努力跟著內心去走,擁抱陽光的人。
(作者系明德豐怡精算咨詢〈上海〉有限公司精算咨詢總監、中國銀保監會償付能力監管專家咨詢委員會咨詢專家,北美精算師協會正會員,中國精算師協會正會員,中國精算師協會委任國際精算師協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