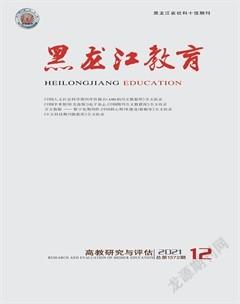后疫情時代大學生育德與育心的耦合策略研究
摘 ? ?要:后疫情時代不僅為高校大學生成長帶來新的挑戰,更為其帶來寶貴的機遇。育德與育心作為實現高校“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重要支柱,既目標一致、相互借助,又邊界模糊、實踐競合。必須從頂層設計并整合兩大支柱的優勢,構建價值導向、良性興趣、尋常態與獲得感高效互動的耦合策略,發揮育德的定向和育心的載體作用,進而在實現學生的自由全面發展中發揮兩者的最大合力。
關鍵詞:后疫情時代;大學生;育德;育心;耦合策略
中圖分類號:G641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文章編號:1002-4107(2021)12-0090-03
回應時代要求,我國高等教育確立了“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不僅為高等教育統一思想、指明方向,也為全員全方位全過程育人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不同于傳統的單打獨斗,后疫情時代高校育人策略要求打破學科桎梏,推進學科深入交融與共同發展,“堅持育心與育德相結合,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1],進而為大思政格局下育德與育心的耦合創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思想與心理:大學生全面發展的內在邏輯
大學生全面發展不僅意味著德、智、體、美、勞的高水平狀態,還包含著知、情、信、意、行的協調性發展過程,從由內而外的體驗感知,到由外而內的規范認同,共同構成了大學生全面發展的內在邏輯。其中,思想與心理便是這一發展邏輯的重要節點,它們相互連接、相輔相成,共同貫穿于大學生全面發展螺旋式上升的全過程。
(一)認知、情緒與行為的發展邏輯
無論是大學生全面發展的結果性狀態還是發展性過程,都必然涉及認知、情緒和行為三大方面,這也是育德和育心的重要切入點和共同連接點。一方面,對客觀事物性質與規律的不同認知,影響著基于個人需要的主觀態度體驗,進而激發個體適應性的身體與情緒反應。另一方面,個人行為的原動力來自本能的需要,而需要的性質、層次與范圍以及滿足需要的時機、條件和方式等,又依賴于認知水平和客觀活動背景。因而,認知、情緒與行為三者之間形成了一個三維矩陣發展態勢,其中任何一端的發展都需要矩陣的聚合與支持,單一的突進或是滯后都會影響矩陣結構的穩定性和個人發展的持續性,乃至造成知行脫節和心理危機等不良后果。
(二)大學生全面發展的關鍵環節及其相互關系
德、智、體、美、勞作為大學生全面發展的階段性目標,其衡量的維度涵蓋了思維、思想、心理、品德、技能、習慣等多個方面,其中思想與心理則是最為關鍵的環節,這也是認知、情緒與行為三維矩陣發揮作用的必然結果。首先,思想是核心,心理是基礎。思想水平決定著大學生心理發展的方向和潛能,而心理狀態也影響著大學生思想成長的動力與效率。其次,思想是內化升華,心理是外化體驗。思想內容主要依賴于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成果,而心理反饋主要表現于對外部世界的主觀體驗。最后,思想是起點,心理是終點。人的本質決定了成長的要義即社會化,需要不斷學習先哲的思想精華,而人的主觀能動性也彰顯了意識體系的創造性建構,以實現“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目標[2]。
(三)育德與育心的辯證關系及其對大學生全面發展的作用
思想與心理在大學生全面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決定了育德與育心成為高校“立德樹人”的重要支柱。育德即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陣地和生命線;育心即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門關注個體身心協調發展、悅納自己、理解他人和適應社會的重要學問。育德與育心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兩者的辯證關系如下:一是既目標一致又邊界模糊,兩者雖關注的側重點不同且部分交叉,但均將促進學生成長作為共同目標;二是既相互借助又理念各異,兩者雖對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的理念差異明顯,但在實際的教育教學過程中又相互支撐;三是既功能互補又實踐競合,兩者雖在育人方法的選擇上有競爭也有合作,但基本上能夠實現主客觀與內外化的統一。因而,育德與育心對大學生全面發展發揮著共同而有區別的關鍵作用,其中,育德借助先進思想價值觀念的核心、內化與起點特質發揮著定向作用;育心憑借健康心理的基礎、外化和終點特質發揮著載體作用,兩者缺一不可。
二、后疫情時代大學生成長中的新現象與新挑戰
后疫情時代鑄就新理念、新精神和新氣象,成長于斯的大學生沐浴著全面深化改革、“互聯網+”、人工智能、5G、云課堂等時代春風,展現出思維活躍、勇于創新以及主動擔當的良好整體風貌。后疫情時代也帶來新挑戰,由傳統向現代、單一向多元、泛化向集中正日益成為大學生的顯著特征。新特征不僅是時代的烙印,更是時代的考卷,面對愈發復雜的社會變革,后疫情時代的考生展現出的部分現象各高校須給予高度重視。
(一)擴大的鴻溝:知識與真知
不同于傳統課堂教學,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在極短的時間內,讓大學課堂迅速“云化”。互聯網的普及極大地拓寬了學生獲取知識信息途徑,同時,知識的更新速度、傳遞效率、來源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因而,機遇與挑戰并存,知識信息數量的指數級增長也為知識的篩選、辨別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后疫情時代大學生在強烈求知欲、好奇心,以及各類實踐活動因防疫受阻的促使下,更多地暢游在各類網絡知識信息的海洋之中。但是往往由于知識獲取的不完整、辯證思維的不成熟和社會體驗、經驗的不足等,可能造成部分學生或是蜻蜓點水、浮于表面,或是碎片化閱讀、快餐式研究,亦或是紙上談兵、理想化偏執化表達,以致無法獲得知識的精髓和真知,而傾向于“杠精”式的表達。誠然,“杠精”的出現有著打破僵化、教條和沉默的一面,但它的另一面卻是沒有對錯、沒有邏輯、沒有權威、沒有意義,只有為反對而反對、為快感而批駁、為逃避而狡辯,往往情緒宣泄多于理性表達。
(二)可能的迷失:無畏與無所謂
追求個性發展或是不走尋常路越來越受到后疫情時代大學生的青睞,但如何處理個性與共性的關系,尤其是區分個性與任性的界線,以及由此演化而來的勇氣與敬畏、自由與責任、權利與使命等涉及大學生成長中的關鍵問題也愈發突出。后疫情時代不僅為大學生提供了更好的物質條件,更為其拓展了選擇性、包容性和人生藍圖,然而,外在客觀條件的改變和優化,在為大學生成長增加可能性的同時,也給其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帶來了更大的考驗。部分學生無論是出于原生家庭教育的偏頗或缺失,亦或是個人的懶散或迷茫,可能會陷入藐視一切、放任自我、逃避責任和亂用權利的歧路。此時,概念化的理論說教和一味的愛護縱容都無法有效應對,而呼喚平等、尊重、有態度、有力度以及有溫度的教育引導,方能真正“解渴”。
(三)艱難的選擇:從容與委屈
建國七十多年來的偉大成就聚焦到后疫情時代大學生身上,某種程度上表現為更加自信和從容,由此也激發了諸如游學、靈活畢業、慢就業以及創新創業等新現象。大部分學生不用再為基本的生存問題而擔憂,不用再為家族的期待而倉促應對,也不用再為未來的不確定性而焦慮不堪。然而,當他們遠離這些曾經的壓力之時,也很容易丟失艱苦奮斗的良好品質和強大精神動力。后疫情時代大學生大部分是從溫室里來到象牙塔,缺少了風雨的洗禮,也就缺乏必要的風險意識和抗挫折的心理準備,厭惡損失、不愿離開自己的“舒適區”等畏難心理較為普遍。據相關調研報告顯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只有50%左右的學生完全不焦慮,30%的學生存在輕微焦慮,5%左右的學生焦慮程度偏高[3]。以至于遇到生活、學習和工作當中的各類事件時,往往表現的極易委屈,尤其是面對社會熱點問題時,情緒的表達超越了理性的審視,最終使問題的性質背離了事件本身。
三、育德與育心在大學生日常教育中的現實困境及原因探析
后疫情時代大學生面臨的成長環境新變化及其所帶來的新現象與新挑戰,使得傳統教育方式的單打獨斗和簡單說教已無法適應,化解育德與育心在大學生日常教育中的現實困境已迫在眉睫。
(一)育德與育心的隔膜和誤解
新中國成立以來,高等學校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基本上確立了育德在意識形態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并伴隨著不同歷史階段的時代背景和主題要求在波動中持續發展。育心雖然在形式上很早就運用于高校教育教學工作中,但嚴格意義上的學科化專業化發展始于改革開放之初。其中,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和2001年教育部《關于加強普通高等學校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見》對于確立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里程碑意義[4]。當前育德與育心之間的主要隔膜在于,一是育德的政治嚴肅性與育心的人文包容性;二是育德的灌輸式與育心的浸潤式;三是育德的價值導向性與育心的價值中立性;四是育德的理性思辨與育心的感性共情。這就導致傳統觀念上育德與育心基本屬于平行的兩條線,或是不容質疑的思想“權威”,或是敬而遠之的心理“問題”等誤解,以至于嚴重削弱了教育的實效性,也容易累積問題。
(二)育德與育心困境的原因探析
育德與育心在大學生日常教育中的困境主要包括單一方法的有限性和交叉方法的阻礙性。究其原因,一是對育德政治屬性的狹隘化理解,政治價值觀的樹立不僅需要外在的灌輸,也需要內化的體驗;二是對異常心理與正常心理的混淆,根據病與非病三原則即主客觀世界的統一性、精神活動內在協調一致性和人格相對穩定性,可初步區分心理治療與育心的主要對象與范圍;三是學科界線與教育理念教條化,教育資源阻塞,無論是傳統育德對育心的不當輕視,還是傳統育心對育德的有意或無意間的忽視乃至抵觸,都無法適應后疫情時代大學生身心發展的新特征與新要求。
四、耦合與升華:引導后疫情時代大學生由本心到向善
后疫情時代新使命亟需高校教育教學模式的創造性變革,促進多學科由統籌發展、一體化建設到融合式創新,成為當前的主流趨勢,以更好地服務于“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積極引導后疫情時代大學生由本心到向善,需要構建育德與育心的耦合策略,其主要環節包括:一是厘清價值邏輯;二是明確規則與途徑;三是優化結構與步驟;四是完善激勵與保障。
(一)夯實統一性與多樣性相協調的價值基石
合理情緒療法作為育心的經典方法,彰顯了認知在由事件傳導至情緒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而認知體系的核心便是價值觀。育德最終的落腳點也是價值觀,因而,如何確立共同的價值基石成為實現育德與育心耦合的關鍵。不同的價值觀將影響后疫情時代大學生,用不同的方式來觀察、解讀并塑造世界,或是空洞乏味、流于瑣碎,或是豐富有趣、充滿意義。就價值觀本身而言,它是內在需要與外在影響相結合的產物,其中,由于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和內在需要的多樣性,往往形成多種類型、多個層次和多個階段的價值觀體系。這就要求在弘揚社會主旋律的同時,關注大學生的個性化訴求;在堅持統一性,傳遞正能量的同時,尊重多樣性,筑牢社會公序良俗等價值底線。無論是育德還是育心,都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共同的價值遵循,同時也應積極關注大學生合理的個性化價值需求,及時矯正錯誤價值觀念,避免宏大說教或忽視縱容。
(二)建構人格典范與日常規范相一致的尋常態
人格典范作為特定時代的先鋒,一般有著高尚的思想覺悟、良好的道德品質和強大的人格魅力等,發揮著引領示范和榜樣激勵的重要作用。日常規范更為接地氣,更為生活化,也更為常態化,起到了維護社會秩序、捍衛社會公德和涵養文明素養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格典范來源于日常規范的升華,又引導著更多人追求真善美;日常規范依賴于人格典范的指引,又不斷夯實社會文明的基石,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割裂。因而,育德與育心應共同為后疫情時代大學生樹立人格典范,并從日常規范入手,腳踏實地;避免絕對化概念、以偏概全和主觀臆測,使大學生在融入社會生活的尋常態,不斷完善自我,最終實現自我價值。
(三)培養階段性與層次性相統一的良性興趣
如果將后疫情時代大學生的學涯化作人生的特殊階段,可將其細分為分離期、和解期和個體化期,學生在不同時期與包括教育在內的客觀外部環境交互方式各異。由于大學與中學階段的學習內容、學習方式、學習環境和社會接觸度等存在巨大差異,大學生面臨著各種“矛盾”的沖擊,形成了短時陣痛的分離期。和解期的大學生開始慢慢嘗試用新的知識和經驗審視周圍的世界,進而逐漸實現身與心、主體與客體之間新的協調。隨著大學生身心的成熟和知識經驗積累的增加,他們便能夠依據自我穩定的性格傾向和思維圖式作出選擇與判斷,即進入到個體化時期。因而,根據三個時期的循序漸進,育德與育心應尊重學生成長規律,針對不同時期的問題癥結,積極培養學生的良性興趣,以筑牢成長之錨。良性興趣如運動、才藝、閱讀、演講等,不僅能夠增強學生的知識與能力儲備以厚積薄發,還可以為學生撥開迷霧以保駕護航,進而更好地化解不同階段的成長困惑,滿足不同層次的成長需求。
(四)增強思維力與感受力相促進的獲得感
獲得感作為育德與育心耦合策略的保障,不僅需要發揮育德的思維力優勢,還需要借助育心的感受力優勢,進而不斷強化獲得感的正向激勵作用。馬克思曾指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5]育德應積極運用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尤其是后疫情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引導學生,既要從宏觀上講哲學、講歷史、講政治、講法治,也要從微觀上講邏輯、講倫理、講美育、講生活,充分發揮思維力優勢,把道理講清講透講完整。“要意識到并且可以欣賞每一個事件,必須要結合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的因素”[6]。育心應在注重真誠、尊重和共情的同時,積極關注客觀環境的限制、要求與倡導,以及主觀和客觀之間的協調與良性互動;在關心愛護學生的同時,也要對學生的健康成長提出嚴格要求,并充分發揮感受力優勢,把用心關心貼心落實落細,積極培養學生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態。
新思政觀引領下的育德和育心,不僅為兩者的優化整合提供了難得的契機,更為兩者耦合策略的構建指明了方向。育德與育心的耦合,不僅主動回應了后疫情時代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所面臨的新環境新挑戰與新要求,更積極適應了課程育人、科研育人、實踐育人和心理育人等十大育人體系新格局,為進一步深化全員全過程全方位育人注入了新動能,進而有助于更好地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參考文獻:
[1]張東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有關情況[EB/OL].(2017-12-06)[2020-11-20].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 xwfb_20171206/sfcl/201712/t20171206_320713.html.
[2]張燕嬰譯注.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14:13.
[3]張人上,顧昭明,邱久睿.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調查[J].中國高等教育,2020(18).
[4]姚本先.心理學(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35.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6][德]阿圖爾·叔本華.人生的智慧(第一版)[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9.
收稿日期:2021-03-20
作者簡介:楊永磊(1990—),男,安徽六安人,揚州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高校學生教育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基金項目:2019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專題項目“新時代大學生政治價值觀協同培育機制研究”
(2019SJB757);揚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基金(學生工作)專項課題“新時代大學生政治價值觀形成機制研究”(xjjxg2019-33);揚州大學2019年度共青團工作重點調研課題“新時代大學生政治價值觀教育長效機制研究”(YDT2019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