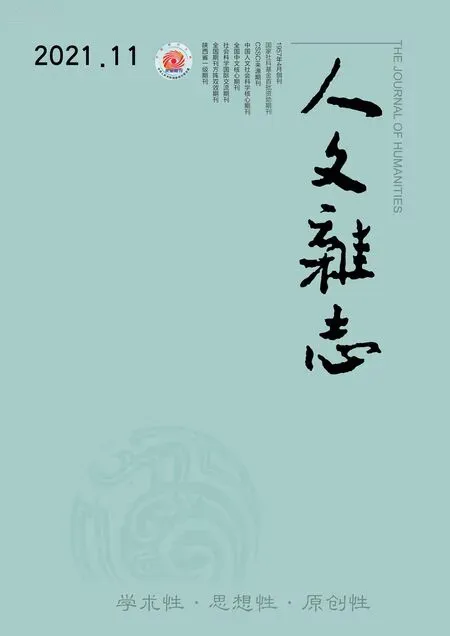經(jīng)史辯證,持世救偏
張城
〔中圖分類號(hào)〕B259.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0447-662X(2021)11-0039-12
引言:思想史脈絡(luò)中之“六經(jīng)皆史”
章學(xué)誠(chéng)思想影響最為深遠(yuǎn)的非“六經(jīng)皆史”莫屬。就經(jīng)史之辯證互動(dòng)關(guān)系而言,此論并非章學(xué)誠(chéng)首創(chuàng),前人早有所涉及與論述。最具代表性的如大儒王陽明曾對(duì)經(jīng)史關(guān)系有如下論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jīng)。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jīng),五經(jīng)亦史。”明末李贄更有六經(jīng)皆史之明確論斷:“經(jīng)史一物也,史而不經(jīng),則為穢史矣,何以垂戒監(jiān)乎?經(jīng)而不史,則為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shí)乎?……故謂《六經(jīng)》皆史可也。”二者對(duì)經(jīng)史辯證關(guān)系雖有所涉及,但皆點(diǎn)到為止,并未形成系統(tǒng)專門之論述。直至浙東史學(xué)殿軍章學(xué)誠(chéng)“六經(jīng)皆史”專論應(yīng)時(shí)而生,對(duì)經(jīng)史關(guān)系作了系統(tǒng)專門之論述,賦予其新內(nèi)涵。正如周予同所評(píng)論:“王通以后,提到‘經(jīng)’、‘史’關(guān)系的,還有南宋陳傅良,明宋濂、王守仁和李贄,但他們說得都較簡(jiǎn)單,有的只是偶爾涉及,并未構(gòu)成一種系統(tǒng)學(xué)說。直到章學(xué)誠(chéng)‘六經(jīng)皆史’,才真正成為一種系統(tǒng)學(xué)說,有其‘經(jīng)世’理論。因此,他的‘六經(jīng)皆史說’顯然是附有新的涵義的。”
凡是在歷史上具有深遠(yuǎn)影響的思想學(xué)說,并非無緣無故,皆淵源有自。如能重回歷史現(xiàn)場(chǎng),從思想史內(nèi)在的發(fā)展脈絡(luò)去觀察分析,即會(huì)發(fā)現(xiàn)章學(xué)誠(chéng)所提“六經(jīng)皆史”論并非拾人牙慧,而是有其深思熟慮。章氏所處之世為乾嘉考據(jù)學(xué)興盛之時(shí),面對(duì)乾嘉經(jīng)學(xué)考證注重字義、名物與制度的嚴(yán)峻挑戰(zhàn),特別是經(jīng)顧炎武至戴震的“經(jīng)學(xué)即理學(xué)”命題,宣稱六經(jīng)為載道之書,道畢具于六經(jīng),訓(xùn)詁考證則是識(shí)解大道的必備功夫。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戴震給段玉裁的信中曾自述道:“仆自十七歲時(shí)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jīng)孔孟不得,非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無由能通其語言。宋儒譏訓(xùn)詁之學(xué),輕語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此即乾嘉考據(jù)學(xué)之核心觀點(diǎn),可謂當(dāng)世之顯學(xué),影響頗大。章學(xué)誠(chéng)對(duì)此頗為惱火,其“六經(jīng)皆史”所破所立,所針砭之對(duì)象實(shí)基于此。“六經(jīng)皆史”論的宗旨即納史入經(jīng),經(jīng)史并重,經(jīng)世致用。“章學(xué)誠(chéng)與經(jīng)學(xué)家們的根本分歧不在義理與考據(jù)的關(guān)系,而在六經(jīng)的位置:在經(jīng)學(xué)家,道自六經(jīng)出,非由文字訓(xùn)詁而不得門徑;在章學(xué)誠(chéng),六經(jīng)不足以盡道,他試圖在史的范疇中另覓義理的途徑。”欲與此甚囂塵上之乾嘉考據(jù)學(xué)針鋒相對(duì),章學(xué)誠(chéng)破立并舉,提出“六經(jīng)皆史”之宏論,自立一套從本體到方法的更為系統(tǒng)徹底之經(jīng)史理論。對(duì)于“六經(jīng)皆史”論,島田虔次給予高度評(píng)價(jià),把它與孔子之仁、孟子之性善……清朝考證學(xué)“實(shí)事求是”相提并論,稱其為“中國(guó)學(xué)術(shù)史上最著名的口號(hào)之一。”余英時(shí)對(duì)此亦十分看重,視之為清代學(xué)術(shù)史上的突破性創(chuàng)見。章學(xué)誠(chéng)“六經(jīng)皆史”論,贊譽(yù)之聲雖然不少,但亦有人將其視為“末世之音”,認(rèn)為“六經(jīng)皆史”論刻意把“經(jīng)”降低為“史”,無形之中逐漸瓦解了人們把“經(jīng)”視為常道的精神信仰。無論對(duì)章學(xué)誠(chéng)“六經(jīng)皆史”是贊譽(yù),抑或批判,的確在章學(xué)誠(chéng)所處之世,經(jīng)學(xué)逐漸走向式微,我們只有重返歷史現(xiàn)場(chǎng),回到思想史發(fā)展脈絡(luò)之中,才能進(jìn)入章學(xué)誠(chéng)的思想世界,真正理解“六經(jīng)皆史”論之要義精髓。
“六經(jīng)皆史”乃章學(xué)誠(chéng)經(jīng)史關(guān)系論之基本理論。“古無經(jīng)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不特《尚書》與《春秋》也。……若六藝本書,即是諸史根源,豈可離哉!”若想對(duì)章學(xué)誠(chéng)之經(jīng)史觀作全面準(zhǔn)確之理解把握,則須對(duì)經(jīng)史概念先釋其義。而在章學(xué)誠(chéng)的思想脈絡(luò)中,何為經(jīng),何又為史?
許慎《說文解字》言:“經(jīng),織也”。即指從絲為經(jīng),衡絲為緯,凡織,經(jīng)靜而緯動(dòng)。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作了訓(xùn)解演繹:“織之從絲謂之經(jīng)。必先有經(jīng)而后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jīng)。”經(jīng)者,常也。即訓(xùn)常道,指常行之義理、準(zhǔn)則。而在三代之后,擬經(jīng)、僭經(jīng)之事屢出不窮,章學(xué)誠(chéng)可謂痛心疾首,力圖針砭時(shí)弊為經(jīng)正名,對(duì)何為經(jīng)章氏做了獨(dú)特訓(xùn)解:“異學(xué)稱經(jīng)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jīng)以擬六藝,妄也。六經(jīng)初不為尊稱,義取經(jīng)綸為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jīng)。”經(jīng)非尊稱,其興起并非要尊經(jīng)顯經(jīng),乃勢(shì)之不得不然。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憂道之不傳,乃取周公典章,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次第編為六藝,與眾徒相與而申明之,但夫子之時(shí)六藝亦不稱經(jīng)。在章學(xué)誠(chéng)看來,為何尊經(jīng),一方面因傳之興而始有經(jīng),“六經(jīng)不言經(jīng),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jīng)而有傳,對(duì)人而有我,是經(jīng)傳人我之名,起于勢(shì)之不得已,而非其質(zhì)本爾也。”一方面因諸子之興而尊經(jīng)。官師政教分離,諸子處士橫議,私家之言脫離典章政教紛然而起,“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jīng),則又不獨(dú)對(duì)傳為名也。……六經(jīng)之名起于孔門弟子亦明矣。”“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經(jīng)之名初始之義既非尊稱,那在章氏看來,何為經(jīng)之本義?“‘《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經(jīng)綸。’經(jīng)綸之言,綱紀(jì)世宙之謂也。”可見,“綱紀(jì)世宙”乃為章學(xué)誠(chéng)所言之經(jīng)綸本義,其引申之意則為治國(guó)理政。顯然,如此定義經(jīng),與“夫六經(jīng),皆先王得位行道,經(jīng)緯世宙之跡,而非托于空言”一脈相承,六經(jīng)非圣人之憑空撰述乃是典章政教,六經(jīng)之跡可依可循,重實(shí)踐而輕空言。
章學(xué)誠(chéng)曾言:“蓋韓子之學(xué),宗經(jīng)而不宗史,經(jīng)之流變必入于史,又韓子之所未喻也。”批評(píng)韓愈知經(jīng)而不懂史。對(duì)于史學(xué),章學(xué)誠(chéng)抱負(fù)極大:“吾于史學(xué),蓋有天授,自信發(fā)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而人乃擬吾于劉知幾。不知?jiǎng)⒀允贩ǎ嵫允芬?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史學(xué)義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biāo)著之名。”由此可見,其不屑于與唐代大史學(xué)家劉知幾相提并論,認(rèn)為對(duì)于史學(xué)義例、校讎心法自有獨(dú)創(chuàng),可知其胸中抱負(fù)。對(duì)當(dāng)時(shí)名噪一時(shí)的經(jīng)學(xué)大師戴震,章學(xué)誠(chéng)更因其不諳史學(xué)卻又盛氣凌人,非常惱火:“戴君經(jīng)術(shù)淹貫,名久著于公卿間,而不解史學(xué)。聞?dòng)嘌允肥拢m盛氣凌之。”在章學(xué)誠(chéng)看來,其心目中之史學(xué),非經(jīng)史子集四部之史部,曾說:“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xué),六經(jīng)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xùn)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于天地之間,別為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此處所言史學(xué)非今日之歷史學(xué),僅指史料耳。他進(jìn)一步指出:“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xué)。”“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shí)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píng)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xué)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píng),古人所為史學(xué),則未之聞矣。”瑏瑠在他看來,史考、史選、史纂、史評(píng)、史例雖都可列于史部,但通常所謂經(jīng)史子集之史部,卻并非其理想之史學(xué)。章學(xué)誠(chéng)所言之史,非后人所謂之史料,而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背景下闡釋先王之道的“撰述”,即為“周代官吏所掌守的實(shí)際的政制典章教化施為的歷史記錄。”他所看重的乃是政典所具之教化功能,而非現(xiàn)代史學(xué)的史料價(jià)值。在章學(xué)誠(chéng)心目中,真史學(xué),須具史德,即“著書者之心術(shù)也。”其實(shí)即孔子所謂之微言大義。“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dú)斷于一心。”《春秋》之所以能成為史之大本大源,即在于其集中體現(xiàn)了圣人心術(shù),而獨(dú)竊取筆削之義,“史之所貴者義也”。而此史學(xué)中所內(nèi)含的筆削之義,并非立基于空言,而是“六經(jīng)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xùn)者耳。”體現(xiàn)圣人心術(shù)之史德,即史家所言之“別識(shí)心裁”,唯有如此,方能成一家之言。在《申鄭》篇中,他對(duì)宋代史家鄭樵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鄭樵生千載而后,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獨(dú)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cè),運(yùn)以別識(shí)心裁,蓋承通史家風(fēng),而自為經(jīng)緯,成一家之言也。”不論圣人之心術(shù),抑或史家之別識(shí)心裁,其目的都在于經(jīng)世,“知史學(xué)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jīng)世……史學(xué)所以經(jīng)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jīng)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當(dāng)時(shí)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xué)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xué)也。”因此,在章學(xué)誠(chéng)心目中,真正能稱之為史學(xué)者,必能垂訓(xùn)古今,必為經(jīng)世之學(xué),“學(xué)問經(jīng)世,文章垂訓(xùn)。”“學(xué)術(shù)固期于經(jīng)世……得一言而致用,愈于通萬言而無用。”學(xué)問之宗旨并非故弄玄虛,空言著述,而是切合人事,經(jīng)世致用。
由此經(jīng)史之訓(xùn)解釋義,便對(duì)《文史通義》開宗明義之言能深切領(lǐng)會(huì):“六經(jīng)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jīng)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學(xué)誠(chéng)認(rèn)為,六經(jīng)皆先王政典,其有圣人心術(shù),筆削之義,亦即有道理在。但又“未嘗離事而言理”,是從治國(guó)理政實(shí)踐中得來之史跡史錄。經(jīng)非空言教訓(xùn),史有筆削之義。在此意義上,經(jīng)史“正以切合當(dāng)時(shí)人事耳”,經(jīng)即史,史亦即經(jīng)。因此,在討論章學(xué)誠(chéng)經(jīng)史觀時(shí),我們要特別注意一種傾向,即認(rèn)為“六經(jīng)皆史”論有尊史抑經(jīng)之傾向,如侯外廬所言:“‘六經(jīng)皆史’論,不但是清初反理學(xué)的發(fā)展,而且更有其進(jìn)步的意義。他大膽地把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所崇拜的六經(jīng)教條,從神圣的寶座拉下來,依據(jù)歷史觀點(diǎn),作為古代的典章制度的源流演進(jìn)來處理。”作為浙東史學(xué)殿軍的章學(xué)誠(chéng),重史之地位毋庸置疑,但他并非疑經(jīng)之人,并未有抑經(jīng)之傾向,對(duì)孔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更推崇備至。在晚年《上朱中堂世叔皀書》中,曾言及自己飽受時(shí)議的經(jīng)史觀:“近刻數(shù)篇呈誨,題似說經(jīng),而文實(shí)論史,議者頗譏小子攻史而強(qiáng)說經(jīng),以為有意爭(zhēng)衡,此不足辨也。……何嘗有爭(zhēng)經(jīng)學(xué)意哉!且古人之于經(jīng)史,何嘗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輕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簡(jiǎn),妄謂史學(xué)不明,經(jīng)師即伏、孔、賈、鄭,只是得半之道。”與其說章氏的基本立場(chǎng)為尊史抑經(jīng),還不如說是在尊經(jīng)之前提下納史入經(jīng),尊史為經(jīng)。章學(xué)誠(chéng)提出“六經(jīng)皆史”,目的是要“為千古史學(xué)辟其蓁蕪”,瑏瑠正如其晚年自辯:“《通義》所爭(zhēng),但求古人大體,初不知有經(jīng)史門戶之見也。”瑏瑡內(nèi)含其高亢之三代復(fù)古理想,即以史學(xué)作為一切經(jīng)典之根柢。正如內(nèi)藤湖南所言:章學(xué)誠(chéng)“認(rèn)為史學(xué)并不是單純記錄事實(shí)的學(xué)問,并對(duì)此從根本上給以了原理、原則的思考。雖然他的思考方式是哲學(xué)的,但是在章學(xué)誠(chéng)看來,作為一切學(xué)問的根本不是哲學(xué)而是史學(xué)。”瑏瑢讓經(jīng)學(xué)不再懸無根基,置于空言,而是有其史學(xué)之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由此,經(jīng)之地位更加鞏固,同時(shí)又把史學(xué)提升到作為經(jīng)之基礎(chǔ)的牢固地位。“章學(xué)誠(chéng)的‘六經(jīng)皆史’說,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恐怕還不是尚存爭(zhēng)議的尊經(jīng)、抑經(jīng)問題,貫穿于其間的一個(gè)中心思想,實(shí)為復(fù)原中國(guó)儒學(xué)的經(jīng)世傳統(tǒng),倡導(dǎo)以史學(xué)去經(jīng)世致用。”因此,經(jīng)以史為基,史亦有經(jīng)訓(xùn),經(jīng)非空言虛懸,史非材料堆砌,經(jīng)即史,史即經(jīng)。就此而言,經(jīng)史并重,經(jīng)史并治,才是章學(xué)誠(chéng)經(jīng)史觀之核心。
討論章學(xué)誠(chéng)的經(jīng)史觀,有一繞不過去的議題,即周孔之關(guān)系。中國(guó)經(jīng)學(xué)史上,一般而言,經(jīng)今文學(xué)宗師孔子,經(jīng)古文學(xué)則祖述周公。章學(xué)誠(chéng)所處之清代中葉,孔子地位明顯高于周公,被歷朝歷代統(tǒng)治者不斷加封。由周孔并稱到以孔孟并稱,看似稱謂之簡(jiǎn)單變化,實(shí)則道出了儒家道統(tǒng)譜系學(xué)中周孔地位之實(shí)質(zhì)變遷。牟宗三曾指出:“唐、宋以前都是周孔并稱。由宋儒開始,才了解孔子的獨(dú)立價(jià)值,了解他在文化發(fā)展中有獨(dú)特的地位,不能簡(jiǎn)單地由他往上溯,而作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驥尾。宋儒的貢獻(xiàn)在此。所以由宋儒開始,不再是周孔并稱,而是孔孟并稱。這很不同,表示這個(gè)時(shí)代前進(jìn)了一步,是個(gè)轉(zhuǎn)折的關(guān)鍵。”章學(xué)誠(chéng)把重新檢討周孔關(guān)系看得非常之重。“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為周、孔。”如要把握往圣先賢所傳之道,知曉周孔之分至為關(guān)鍵,這亦是章學(xué)誠(chéng)經(jīng)史觀一脈相承的內(nèi)在邏輯。《禮記·樂記》云:“作者之謂圣,述者之謂明。”章學(xué)誠(chéng)認(rèn)為,只有德位兼?zhèn)渲ト瞬庞兄谱鞫Y樂刑政、典章政教之權(quán)責(zé),而被儒生視為崇高神圣之六經(jīng)亦不過“先王之政典”,“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經(jīng)。”在他看來,周公即六藝之“作者”,六藝乃周公治國(guó)理政之典章,其切合于當(dāng)時(shí)人事,具有經(jīng)綸為世之效,進(jìn)而才有立為經(jīng)之可能。而孔子僅為六藝之“述者”而非“作者”,“夫子之圣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jīng)者,以其非政典也。”
由此看來,章學(xué)誠(chéng)力圖從重建經(jīng)史關(guān)系之視角,還原“六經(jīng)皆史”論歷史脈絡(luò)中的周孔關(guān)系,給予各自恰當(dāng)位置,各安其位。首先,章學(xué)誠(chéng)把周孔都尊為圣人,而并非如某些學(xué)者所言有故意揚(yáng)周貶孔之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jié)吻合,如出于一人,不復(fù)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周公孔子之圣符節(jié)吻合,如出于一人,“夫子之圣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jīng)者,以其非政典也。”特別針對(duì)后世儒生罔顧事實(shí)不曉真理,想棄周公而獨(dú)尊孔子,“援天與神而為恍惚難憑之說……而盛推孔子,過于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經(jīng)綸,不足當(dāng)儒生之坐論矣。”看似尊孔,實(shí)則背離孔子尊周公之旨意,亦與儒家重經(jīng)世之宗旨不甚相符。其次,章學(xué)誠(chéng)認(rèn)為周孔之分至為關(guān)鍵,關(guān)涉古今學(xué)術(shù)源流。在他看來,周孔雖都為圣人,但亦“自古圣人,其圣雖同,而其所以為圣不必盡同,時(shí)會(huì)使然也。”所處時(shí)代環(huán)境有異,為圣之方必將有別。“必求端于周、孔之分,此實(shí)古今學(xué)術(shù)之要旨,而前人于此,言議或有未盡也。”周孔之分并非只是簡(jiǎn)單的地位之別,而是關(guān)涉古今學(xué)術(shù)之宗旨,不可不明。再次,章學(xué)誠(chéng)分別周孔關(guān)系之核心標(biāo)準(zhǔn)在于德與位。《中庸》曰:“故大德,必得其位”,“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中庸》第二十八章)章學(xué)誠(chéng)深受儒家德位觀影響,認(rèn)為有位無德或有德無位皆不能制作典章禮樂,其制作之權(quán)只能歸于德位皆備之圣人,“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經(jīng)綸治化,一出于道體之適然。”“大抵為典為經(jīng),皆是有德有位,綱紀(jì)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瑏瑡在他看來,周公乃有德有位之圣人,可集千古群圣之大成,“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dāng)?shù)廴鮽洌笠蛳谋O(jiān),至于無可復(fù)加之際,故得藉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則有德卻無位,即無制作之權(quán)。“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制作之權(quán)。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征不信’也。”孔夫子之所以“述而不作”,并非自謙,而是對(duì)圣王德位一體之觀念有高度自覺。同時(shí),章學(xué)誠(chéng)亦特別申明,孔子雖無位但亦為圣人,雖不能列于集大成之域,但孔子之圣非遜于周公,時(shí)會(huì)使然也。最后,章學(xué)誠(chéng)指出周孔分別之歷史功績(jī)與地位。周孔為何有如此之分,其因如上所言即“時(shí)會(huì)使然”,關(guān)鍵在于三代以上君師治教合一,三代以降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由此君師治教之分,而有周孔之別,“周公集治統(tǒng)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異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xué)校并祀周、孔,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蓋言制作之為圣,而立教之為師。”由此,從經(jīng)世之經(jīng)史觀出發(fā),章學(xué)誠(chéng)認(rèn)為周公重于孔子,“集大成者,周公所獨(dú)也。”(但又迫于當(dāng)時(shí)環(huán)境,特強(qiáng)調(diào)乃出于天)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xué)。正如有學(xué)者所言:“章氏置周公的成就于孔子之上,此點(diǎn)不只與絕大多數(shù)儒者大異其趣,而且與清初君主的評(píng)價(jià)亦不符。……但不可否認(rèn)的,章氏的評(píng)估標(biāo)準(zhǔn)卻是取自‘時(shí)代精神’(Zeitgtist)‘理’與‘勢(shì)’的合一。”孔子立教之極亦本于周公之大成,不能出其范圍。但君師既分,又不能盡行周公之道法典章而只能明其教。“孔子學(xué)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用治統(tǒng)、立教分別周孔,顯示了章學(xué)誠(chéng)圣人觀的匠心獨(dú)運(yùn)之處,事功制作當(dāng)為首,制作才能為圣,立教只能為師。后世新儒家牟宗三亦用政教之分以別周孔之地位:“到了孔子,開始政教分離;假定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主,就是以政治事業(yè)為主,以業(yè)績(jī)?yōu)橹鳌?鬃硬]有作皇帝,沒有稱王,有其德而無其位。所以我們可以籠統(tǒng)地說,到了孔子,是政教分離;孔子的地位是‘教’的地位,不是‘政’的地位。所以孔子本身含一傳統(tǒng)。”雖同樣討論政教關(guān)系,但作為新儒家代表的牟宗三宗師孔子,其力圖抬高孔子地位之用意甚為明顯。而章學(xué)誠(chéng)并非儒門中人,并且對(duì)當(dāng)世儒生并無太多好感,對(duì)孔子雖甚為尊重但亦說不上宗師孔子,則其目的在于凸顯周公之地位。同時(shí),章學(xué)誠(chéng)雖認(rèn)為孔子之學(xué)盡為周公之道,但“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至于無可復(fù)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jié)吻合,如出于一人,不復(fù)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在章學(xué)誠(chéng)看來,雖不能有意拔高孔子,但亦不能矮化圣人。而后世儒生欲尊孔子,私立其為儒者宗師,卻不知道反而矮化了孔子,“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為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于立儒道之極也?…… 人道所當(dāng)為者,廣矣,大矣。”孔子立教乃是立普世之人道,而非僅立儒家一派之道。與此同時(shí),章學(xué)誠(chéng)認(rèn)為古無經(jīng)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如沒有三代之后官師政教分離,則私言不會(huì)出于世。孔子乃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經(jīng)以垂教于萬世,此實(shí)為孔子之不得已。“夫子生于東周,有德無位,懼先圣王法積道備,至于成周,無以續(xù)且繼者而至于淪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dú)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而后世之儒非處衰周之世,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誤以為孔子之本志,誤欲師孔子而法六經(jīng)以垂后,豈有不得已者乎?“夫六經(jīng),皆先王得位行道,經(jīng)緯世宙之跡,而非!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因此,章學(xué)誠(chéng)特別鄭重提醒后世儒生:“故學(xué)孔子者,當(dāng)學(xué)孔子之所學(xué),不當(dāng)學(xué)孔子之不得已。”孔子之所學(xué),乃是倡周公之道,存其治化之跡,以明其教,而非空言著述離其宗旨。
為與一時(shí)甚囂塵上的乾嘉考據(jù)學(xué)相抗衡,章學(xué)誠(chéng)發(fā)前人之未言,立基于“六經(jīng)皆史”論,力圖構(gòu)建一套完整系統(tǒng)的從本體到方法之經(jīng)史觀,對(duì)考據(jù)訓(xùn)詁學(xué)進(jìn)行徹底清算。前述的經(jīng)史觀、圣人論屬于本體論視域,這里從方法論視角作進(jìn)一步檢討。“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針對(duì)儒生根深蒂固的六經(jīng)乃載道之書的理論偏見,章學(xué)誠(chéng)“六經(jīng)皆史”要旨即為道正名,何為道,何以求道,又何以明道。
《原道》卷首,章學(xué)誠(chéng)即開宗明義,“道之大原出于天”,接著講“《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認(rèn)為道乃先于人而存在,進(jìn)而從歷史哲學(xué)視角,由“天地生人斯有道”始,一步步實(shí)證“有道而未形”“道形而未著”“部別班分而道著”,而后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起的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最后云:“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shì)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在章學(xué)誠(chéng)看來,道即為社會(huì)發(fā)展本身蘊(yùn)含的歷史規(guī)律與必然趨勢(shì),與任何圣人有意為之的主觀創(chuàng)造無關(guān)。“圣人創(chuàng)制,則猶暑之必須為葛,寒之必須為裘,而非有所容心。”圣人非憑空造作,皆因循道之客觀運(yùn)行規(guī)律而制作。因此,章學(xué)誠(chéng)總結(jié)道:“孰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也。”故道即不知其然而然矣。
章學(xué)誠(chéng)一生以求道明道為志業(yè),時(shí)常感嘆:“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后世之人不曉六經(jīng)非載道之書,而僅為載道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jīng),以謂六經(jīng)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jīng)皆器也。” “六經(jīng)皆器”作為“六經(jīng)皆史”經(jīng)史觀之重要支撐,躍然紙上。對(duì)如何才能求道,章學(xué)誠(chéng)進(jìn)一步提出圣人與眾人的概念:“道無所為而自然,圣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眾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圣人作為體道者,有不得不然而須求其所以然。但道無形而不可見,如何道方可求?如老子所言,“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雖不可見,但道不離器,器不離道,一陰一陽之跡,即為載道之器,“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學(xué)。”圣人可藉道之跡即器以見道。“《六經(jīng)》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shí),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因此,器以載道,求道必于器中,“后人不見先王,當(dāng)據(jù)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
由“道器合一”“六經(jīng)皆器”之本體論,自然便能開出“即器而明道”之認(rèn)識(shí)論。六經(jīng)非載道之書,只是周公之政典,孔子因憂周公之道晦,而表彰六籍立之為經(jīng),“六經(jīng)即其器之可見者也。”經(jīng)本身非道矣,只是載道之器而已。因此,章學(xué)誠(chéng)明確指出:“夫道備于六經(jīng),義蘊(yùn)之匿于前者,章句訓(xùn)詁足以發(fā)明之。事變之出于后者,六經(jīng)不能言,固貴約六經(jīng)之旨而隨時(shí)撰述以究大道也。”道本源自于天,未有斯人而先有斯道,其為宇宙萬物之所以然。正如列寧所言:“人類思維按其本性是能夠給我們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對(duì)真理的總和所構(gòu)成的絕對(duì)真理的。”章學(xué)誠(chéng)所言之道即可理解為列寧所言的絕對(duì)真理,而備于六經(jīng)中之道可理解為列寧所言的相對(duì)真理。道作為總體的絕對(duì)真理,由相對(duì)真理總和而成,歷史發(fā)展永無止境,相對(duì)真理亦不斷發(fā)展。對(duì)章學(xué)誠(chéng)之論斷,余英時(shí)頗有識(shí)見:“實(shí)齋的本意是說六經(jīng)但為某一階段(即古代)之史,而非史之全程。易言之,六經(jīng)皆史而史不盡于六經(jīng)。必須如此下轉(zhuǎn)語,‘六經(jīng)皆史’的全幅涵義始能顯現(xiàn)。…… 實(shí)齋以‘道’在歷史進(jìn)程中不斷展現(xiàn)。六經(jīng)既只是古史,則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發(fā)展的消息。至于‘事變之出于后者,六經(jīng)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有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了。”“義蘊(yùn)之匿于前者”,即言六經(jīng)本身乃周公之政典作為載道之器的六經(jīng)只能明三代以來之道(相對(duì)真理),而三代以來后續(xù)之道則超出作為載道之器的六經(jīng)所能明道之范圍,“事變之出于后者”,必須往后看,“隨時(shí)撰述以究大道”。尤其針對(duì)儒生“求道必于六經(jīng)”之固執(zhí),章學(xué)誠(chéng)甚至指出:“離經(jīng)傳而說大義,雖諸子百家,未嘗無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機(jī)無意而自呈也。”這里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章學(xué)誠(chéng)并非相對(duì)主義者,對(duì)六經(jīng)中所義蘊(yùn)之道并非隨時(shí)代發(fā)展而棄而不顧,相反必須“貴約六經(jīng)之旨”即今日所言之立場(chǎng)、觀點(diǎn)、方法。但章學(xué)誠(chéng)亦非好古之人,并常以孔子所言之“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及其身者也”自警自勉。同時(shí),對(duì)自古及今的經(jīng)世致用之道,章學(xué)誠(chéng)從不敢怠慢,“鄙人不甚好古,往往隨人浮慕而旋置之,以謂古猶今爾。至于古而有用,則幾于身命殉之矣!”“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是則學(xué)之貴于考征者,將以明其義理爾。”“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shí)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得其仿佛者亦即“貴約六經(jīng)之旨”,對(duì)此甚為重視,以至可為其身命殉之。可見章學(xué)誠(chéng)視“六經(jīng)之旨”為指導(dǎo)思想,須闡明其中義理,但又非僅僅墨守經(jīng)訓(xùn),并“隨時(shí)撰述以究大道”,通過可見之跡,與時(shí)俱進(jìn)地深入揭示“道”之恢宏全體。
對(duì)于六經(jīng)不能言,而事變之出于后者隨時(shí)撰述以究之“大道”,章學(xué)誠(chéng)認(rèn)為必須尊重“時(shí)會(huì)使然”即歷史發(fā)展之規(guī)律。六經(jīng)乃周公政典,成于治教無二官師合一之際。“學(xué)者所習(xí),不出官司典守,國(guó)家政教……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但其后“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氣數(shù)之出于天者也。”面對(duì)這種官師治教相分之不得不然,章學(xué)誠(chéng)認(rèn)為不可泥古不化,“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乃世之學(xué)者,喜言墨守,墨守固專家之習(xí)業(yè),然以墨守為至詣,則害于道矣。……于是有志之士,以謂學(xué)當(dāng)求其是,不可泥于古所云矣。”強(qiáng)調(diào)學(xué)者不可舍今而求古,抱守殘缺,“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法圣人之言,以為圣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為之外耳。”由此可見,以時(shí)為大,經(jīng)世為本,這即章學(xué)誠(chéng)“六經(jīng)皆史”之精髓要義。
同時(shí),“六經(jīng)皆史”又潛藏著一個(gè)重要論題,即法先王抑或法時(shí)王。在討論此問題前,須指出章學(xué)誠(chéng)毫無疑問是一位“權(quán)威主義者”,對(duì)于圣人君父,章學(xué)誠(chéng)始終心存敬畏,“夫著書大戒有二:是非謬于圣人,忌諱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茍粗明大義,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瑏瑡同時(shí),他進(jìn)一步以司馬遷、屈原為例:“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于三代之英,而經(jīng)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xué)無識(shí)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shù)何由得正乎?”極力申說司馬遷、屈原等對(duì)在上之君父無絲毫誹謗之意。在章學(xué)誠(chéng)心目中,三代以前官師合一治教無二,六經(jīng)皆先王政典未嘗不以之教人,故學(xué)者所習(xí)不出官司典守國(guó)家政教,“天地之大,可以一言盡。……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xué)周公而已矣。”而后私言私學(xué)之興起,他認(rèn)為乃出于勢(shì)之不得已。由此便知,對(duì)“以吏為師”之古制,章學(xué)誠(chéng)自然推崇備至,“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詩(shī)》、《書》而僅以法律為師耳。三代盛時(shí),天下之學(xué),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xué)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學(xué)術(shù),不盡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為師,始復(fù)古制。而人乃狃于所習(xí),轉(zhuǎn)以秦人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猶有合于古者,以吏為師也。”“以吏為師”乃是秦僅存三代之法的遺跡,章學(xué)誠(chéng)對(duì)秦人恢復(fù)古制卻深以為然,只是指出了秦人“以吏為師”僅以法律為師略顯不足而已。“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shí)為大而動(dòng)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同時(shí),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不能不加辨別地盲目復(fù)古,“以吏為師”有其前提,即必須“禮時(shí)為大”。而對(duì)于法先王還是法時(shí)王,章學(xué)誠(chéng)之選擇毫無疑問在于法時(shí)王,對(duì)其推崇備至。“《傳》曰:‘禮,時(shí)為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shí)王之制度也。學(xué)者但誦先圣遺言而不達(dá)時(shí)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靋?繡之玩而學(xué)為斗奇射覆之資,不復(fù)計(jì)其實(shí)用也。”因此,不能舍今求古,舍器求道,時(shí)王制度乃是求道之根本所在。“故無志于學(xué)則已,君子茍有志于學(xué),則必求當(dāng)代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經(jīng)術(shù)精微,則學(xué)為實(shí)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在章學(xué)誠(chéng)看來,言經(jīng)術(shù)而不通掌故,言好古而不知當(dāng)代,則為射覆之學(xué),靋之文,雖極精能,但不能經(jīng)世致用。對(duì)章學(xué)誠(chéng)貴時(shí)王當(dāng)下之制度實(shí)踐,錢穆深有體悟,認(rèn)為章學(xué)誠(chéng)點(diǎn)出了訓(xùn)詁考據(jù)之學(xué)弊病所在:“我們真要懂得經(jīng)學(xué),也要懂得從自身現(xiàn)代政府的官司掌故中去求,不要專在古經(jīng)書的文字訓(xùn)詁故紙堆中去求。這是章實(shí)齋一番大理論。清代人講經(jīng)學(xué)卻都是講錯(cuò)了路,避去現(xiàn)實(shí)政治不講,專在考據(jù)古經(jīng)典上做工夫,與自己身世渺不相涉,那豈得謂是經(jīng)學(xué)?
因此,求道必求之于政教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而政教典章之跡,即存于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求道,道無可見,即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也。學(xué)于圣人,斯為賢人。學(xué)于賢人,斯為君子。學(xué)于眾人,斯為圣人。非眾可學(xué)也,求道必于一陰一陽之跡也。…… 蓋自古圣人,皆學(xué)于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章學(xué)誠(chéng)方法論之真諦由此可謂和盤托出,看似章氏尊奉以吏為師,是一個(gè)徹頭徹尾主張圣人史觀與英雄史觀的權(quán)威主義者。但事實(shí)并非如此,他極力駁斥傳統(tǒng)“圣人與道同體”謬論。“學(xué)于眾人,斯為圣人”可謂道破玄機(jī),充分彰顯章學(xué)誠(chéng)重視民眾,以民眾為求道之本,圣立基于眾,遵循下層路線,在認(rèn)識(shí)論層面堅(jiān)持民為本,套用今日之政治修辭即群眾路線,是群眾史觀的擁護(hù)者和執(zhí)行者,徹底否認(rèn)了圣人史觀。侯外廬稱這一說法為“乾嘉時(shí)代的光輝的命題。
“學(xué)于眾人,斯為圣人。”其中深蘊(yùn)著章學(xué)誠(chéng)之知行觀。“大道之隱也,不隱于庸愚”。眾人雖不能體道,知曉萬事萬物之所以然,但在章學(xué)誠(chéng)的視域里,眾人作為包含萬事萬物之當(dāng)然的總體性概念,卻包含著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此為道之跡,經(jīng)世之道即蘊(yùn)含于此跡中。同時(shí),他強(qiáng)調(diào)之所以要學(xué)于眾人即在于有“公是成于眾人”,“天下有公是,成于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異也。”圣人必須藉此跡,道才方可見,“非眾可學(xué)也,求道必于一陰一陽之跡也。”同時(shí),在章學(xué)誠(chéng)看來,“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跡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由此,對(duì)眾人日倫常用如此眾多的一陰一陽之跡即道之跡,圣人必須悉心領(lǐng)悟,以經(jīng)世為標(biāo)準(zhǔn),把眾跡之中“窮變通久之理”進(jìn)行“經(jīng)綸制作”,提煉總結(jié)集大成,變成載道之器如六經(jīng)等經(jīng)典文獻(xiàn)以垂訓(xùn)于后世,此即道之器。并且此道之器皆取于國(guó)家政教官司典守,而非空言著述私說爭(zhēng)論,“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xué)校皆見于制度。彼時(shí)從事于學(xué)者,入而申其占畢,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xué)皆信而有征,而非空言相為授受也。”作為載道之器如六經(jīng)等,經(jīng)歷史實(shí)踐之反復(fù)檢驗(yàn),又可對(duì)其進(jìn)行持續(xù)的理論提純,“貴約六經(jīng)之旨”即今日所言立場(chǎng)、觀點(diǎn)、方法,用以指導(dǎo)眾人,即變成道之理。在章氏理論中,錢穆最為看重“圣人學(xué)于眾人”,認(rèn)為此條義理最深,對(duì)之贊譽(yù)有加推崇備至:“儒家的價(jià)值系統(tǒng)并不是幾個(gè)古圣昔賢憑空創(chuàng)造出來而強(qiáng)加于中國(guó)人的身上的。相反的,這套價(jià)值早就潛存在中國(guó)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過由圣人整理成為系統(tǒng)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價(jià)值系統(tǒng)是從中國(guó)人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所以它才能反過來發(fā)生那樣深遠(yuǎn)的影響。”綜上而言,章學(xué)誠(chéng)知行觀的內(nèi)在邏輯已清晰可尋:圣人學(xué)于眾人,從人倫日用中體會(huì)眾人之感性材料即道之跡→經(jīng)由圣人經(jīng)綸之制作即道之作→編輯為經(jīng)典文獻(xiàn)即道之器→上升為指導(dǎo)的思想即道之理,由是一步步伴隨歷史之發(fā)展,隨時(shí)撰述以究大道。這即章學(xué)誠(chéng)知行觀內(nèi)蘊(yùn)之邏輯,實(shí)際上承繼了中國(guó)古典哲學(xué)傳統(tǒng)中的知行合一觀,更為重要的是,它有一種承前啟后的歷史功能。章學(xué)誠(chéng)是浙東史學(xué)殿軍,章太炎是浙東史學(xué)的傳人,而范文瀾曾師從章太炎門人黃侃,這為范文瀾后來轉(zhuǎn)向以實(shí)踐論為基礎(chǔ)的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汪暉即指出章學(xué)誠(chéng)“六經(jīng)皆史”論為重新理解經(jīng)史關(guān)系確立了一種全新的“方法論視野”。
同時(shí)針對(duì)漢學(xué)、宋學(xué)之流弊,章學(xué)誠(chéng)作出針鋒相對(duì)之尖銳批評(píng)。“君子之學(xué)術(shù),為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于調(diào)劑者然也。風(fēng)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xué)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fēng)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shí)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為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為正,必襲其偽者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勢(shì)也。而世之言學(xué)者,不知持風(fēng)氣而惟知徇風(fēng)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yù)焉,則亦弗思而已矣。”所謂持世,就是為當(dāng)時(shí)的典章政教人倫日用服務(wù),用以經(jīng)世;所謂救偏,就是指斥漢學(xué)、宋學(xué)等的各執(zhí)一偏。
首先,對(duì)漢學(xué)誤以器為道之流弊提出批評(píng):“訓(xùn)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漢學(xué)知即器以求之,而其用思致力之途,初不出乎字義、名物、制度、章句、訓(xùn)詁之間,以為所有學(xué)問均在此,而不知這乃明道之器而非道之本體。在章學(xué)誠(chéng)看來,六經(jīng)即器,雖非載道之書,但只有存是器方能識(shí)其道。由此之故,便不能走向另一個(gè)誤以器為道之極端。章句訓(xùn)詁,制度鉆研,義理疏解,名物考求,皆不足以言道。因此,意圖以考據(jù)訓(xùn)詁之學(xué)以通經(jīng),其實(shí)是南轅北轍離道甚遠(yuǎn),實(shí)不可取。“近日考訂之學(xué),正患不求其義,而執(zhí)形跡之末,銖黍較量,小有異同,即囂然紛爭(zhēng),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特別針對(duì)后世經(jīng)學(xué)家固守門戶,范圍狹窄,只陷于“一經(jīng)之隅曲”而不能窺見古人之全體,章學(xué)誠(chéng)認(rèn)為求道須六藝并重而不可止守一經(jīng),即使治一經(jīng)而經(jīng)旨閎深亦不可限于隅曲,故專攻一經(jīng)之隅曲必與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相悖,“訓(xùn)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bǔ)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jīng)師先已不能無癥牾,傳其學(xué)者又復(fù)各分其門戶,…… 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這即針對(duì)以戴震為首的以訓(xùn)詁才能通經(jīng)致道的漢學(xué)之激烈批評(píng),并揶揄此為“猶資舟楫以入都,而謂陸程非京路也。”正因?qū)h學(xué)之反動(dòng),章學(xué)誠(chéng)特別強(qiáng)調(diào)“讀書觀大意”亦未嘗非學(xué)問求道之方,否則一味崇奉考據(jù)訓(xùn)詁,則“學(xué)者風(fēng)氣,征實(shí)太多,發(fā)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騖于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而其最后之結(jié)果只能是道不明而爭(zhēng)于器,實(shí)不足而競(jìng)于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
其次,對(duì)宋學(xué)離器而言道之流弊更為不滿:“世儒言道……以謂圣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為之外耳。”此離器而言道,故宋學(xué)之弊即:“以‘道’名學(xué),而外輕經(jīng)濟(jì)事功,內(nèi)輕學(xué)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xué)也。”在他看來,這些表面終日以誦法圣人之言為志業(yè)的儒生雖汲汲于先王之道,但其實(shí)乃脫離世事而空言道矣,“專于誦讀而言學(xué),世儒之陋也!”如套用今日術(shù)語即為教條主義者。“《詩(shī)》、《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為效法也。”故不能死守教條,須與實(shí)踐結(jié)合,求道既不可盲目復(fù)古,亦不能輕易舍己從人,必須隨時(shí)保持求道者之主體性。“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dāng)其可之準(zhǔn),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 故效法者,必見于行事。”
因此,在章學(xué)誠(chéng)看來,世儒之患在于學(xué)而不思,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學(xué)。“故夫子言學(xué)思偏廢之弊,即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xí)于事者也。”因此,必須學(xué)思結(jié)合,如夫子作《春秋》之原則“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既不能如漢學(xué)式的誤以器為道,更不能像宋學(xué)之流離器而言道,“夫思,亦學(xué)者之事也。而別思于學(xué),若謂思不可以言學(xué)者,蓋謂必習(xí)于事而后可以言學(xué),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在章學(xué)誠(chéng)看來,道不在人倫日用之外,習(xí)于事乃是思之本,學(xué)之原。他針砭時(shí)弊地指出了漢、宋之學(xué)的思想弊端,漢宋之爭(zhēng)究其實(shí)質(zhì)而言,乃爭(zhēng)名而矣也,于事無補(bǔ),于道更是無益。章學(xué)誠(chéng)通過道器合一,學(xué)思合一,知行合一,力圖“持世而救偏”。正如周予同所言:“我們可以說‘六經(jīng)皆史說’是章學(xué)誠(chéng)的‘經(jīng)世’理論,是他的歷史哲學(xué)的核心。‘六經(jīng)皆史說’是在乾嘉時(shí)代漢學(xué)盛行、宋學(xué)仍占優(yōu)勢(shì)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并以之反對(duì)漢學(xué)、宋學(xué)的偏失的。在當(dāng)時(shí),他有所立、有所破。他大膽地提出‘六經(jīng)皆史’的命題,建立道器合一的哲學(xué),反對(duì)風(fēng)靡一時(shí)的漢學(xué)和高據(jù)堂廟的宋學(xué),在中國(guó)思想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作為浙東史學(xué)殿軍秉承經(jīng)世傳統(tǒng)的章學(xué)誠(chéng),在歷經(jīng)漢宋之爭(zhēng)后,特別是面對(duì)所處之世的時(shí)代境遇,他深刻意識(shí)到對(duì)經(jīng)史關(guān)系必須進(jìn)行一次從本體到方法更為徹底的重塑。就此而言,理解章學(xué)誠(chéng)之經(jīng)史觀,核心即六經(jīng)皆史之經(jīng)史觀,周孔之分之圣人觀,即器明道之方法論,學(xué)于眾人之知行觀,宗旨即經(jīng)史并重,經(jīng)世致用。
“史學(xué)所以經(jīng)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在章學(xué)誠(chéng)看來,六經(jīng)皆先王政典,“切合當(dāng)時(shí)人事”,經(jīng)即古史,史即新經(jīng)。章學(xué)誠(chéng)“六經(jīng)皆史”論,表面看似有尊史抑經(jīng)之傾向,但縱觀其一生,其并非疑經(jīng)之人,對(duì)經(jīng)可謂甚為篤信尊奉。“損益雖曰隨時(shí),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章學(xué)誠(chéng)對(duì)堯、舜以來至周公古先圣王所傳之道,始終畢恭畢敬不敢懈怠,對(duì)孔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更是推崇備至,贊譽(yù)有加。章學(xué)誠(chéng)一生尊奉典章政教,對(duì)于圣人君父,更是始終心存敬畏。對(duì)于學(xué)者之著述,他曾立有如下明確之規(guī)矩:“夫著書大戒有二:是非謬于圣人,忌諱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茍粗明大義,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對(duì)于把章學(xué)誠(chéng)的“六經(jīng)皆史”論定格為尊史抑經(jīng),筆者認(rèn)為不符合章學(xué)誠(chéng)之本意,與其說抑經(jīng)尊史,不如說章氏立足大局,在尊經(jīng)前提之下,納史入經(jīng),尊史為經(jīng),經(jīng)史并重。“六經(jīng)皆史”蘊(yùn)含著章學(xué)誠(chéng)的苦心孤詣,即力圖重構(gòu)經(jīng)史關(guān)系,恢復(fù)經(jīng)史關(guān)系的歷史源流與本來面目,以史為經(jīng)之根柢,讓對(duì)經(jīng)之尊崇信仰更為扎實(shí)牢靠。由此,經(jīng)之地位更為鞏固,同時(shí),史中又可凝練出新經(jīng),進(jìn)而又把史之地位抬升。因此,經(jīng)非空言著述,史非材料堆砌,信仰立基于典章政史,歷史中亦有道理經(jīng)訓(xùn)。正如汪暉所言:“從活生生的生活實(shí)踐內(nèi)部來理解世界,從‘自然’之中理解‘不得不然’。這就是章學(xué)誠(chéng)的歷史觀。”由此,經(jīng)立基于源源不斷的制度實(shí)踐之史,史成為經(jīng)牢不可破的堅(jiān)實(shí)地基。有了真實(shí)歷史支撐的信仰便不再空洞,而豐富的歷史過程本身,經(jīng)過“隨時(shí)撰述”,其自身便不斷會(huì)凝練成新的信仰,經(jīng)即古史,史即新經(jīng)。歷史成為經(jīng)典永不枯竭的源頭活水。由此,在豐富的實(shí)踐發(fā)展過程中,歷史提升為一種歷史哲學(xué),歷史化為了信仰。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guó)家行政學(xué)院)文史部
責(zé)任編輯:王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