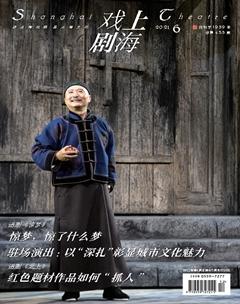紅色題材舞臺美術設計中寫意性的探索
朱嘉君
摘? 要:中國歌劇歷經近百年的發展,從探索期到發展期,存在多種體裁、多種風格。近年來紅色題材不斷涌現,一段段歷史和現在的故事再度呈現在觀眾面前。從走近百姓的寫實手法,到更體現創作者內心情緒解讀的寫意手法,歌劇舞臺美術的風格與樣式也在不斷地探索與發展,豐富了舞臺的表現形式。戲劇是多元化的,需要各種風格、手法、流派并存。只要能把戲劇內容詮釋表達得恰當、完美,都是創作者的一次完美藝術實踐。
關鍵詞:中國歌劇 紅色題材 舞臺美術 寫意
歌劇作為藝術殿堂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是融歌、舞、劇、舞臺美學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被公認為音樂、戲劇藝術領域中的“航空母艦”,也是舞臺藝術總體實力的具體表現。(周英 《 藝苑 》)當我拿到經典歌劇《江姐》的劇本,便希望在這次紅色題材的創作中運用寫意的手法去呈現。“寫意”是一種“縱情、曠達、書寫”的狀態,舞臺美術的“寫意”是創作者胸懷對題材(劇本)的激情,借設計語匯及造景來渲情泄意。以本人創作的歌劇《江姐》舞美設計為例,我從劇本中解讀出整個故事發生在國民黨反動派敵特與江姐等共產黨人的斗爭時期,戲中有國民黨反動派在暗處不停抓捕共產黨人的種種情節,還有“敵特潛伏”的戲份,所以整個舞臺的大基調便定下了——非黑即白,非善即惡。劇本喚起了我強烈的內心感受,深層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大于我所希望的還原當時地理風貌環境。為此,我想呈現的舞臺形式是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體驗”和梅耶荷德的“表現”兩種理念融為一體,“流真實的眼淚,用戲劇的方式讓觀眾看到”,即所謂的“幻想現實主義”,簡言之,就是一種寫意的現實主義。(姜訓祿《寫意——舞臺現實主義的另一種形式》)
(一)
“寫意”是相對“寫實”來說的,是舞臺美術風格樣式中重要的審美取向之一,“似與不似”的形。紅色題材的舞美設計需要蘊涵劇目的革命理想寄寓和共產黨人胸懷的詩思,“寫意”是通過洗煉、變形、提取的手法來承載紅色題材的精神訴訟,“寫意”手段是舞臺藝術審美最具表現力的一種手法。在舞美設計中“寫意”與“寫實”僅是手法上的不同,在將心愿、意愿、意向、意圖、意旨、意趣用造景來營造表演空間方面是相同的。“黑與白”自然是光明正義對抗黑暗罪惡。反動派往往在暗處,在舞臺的暗區活動,在舞臺調度上有一定的展現。比如,第一幕重慶山城,需要抓住山城樓房的特點,重慶首先是大城市,靠山建房是一大特色。房屋下部的支撐在舞臺上特意略做強化,在舞臺調度中房屋下部的陰影中也混雜著支撐桿的影子,在這些暗處,往往就是“開水糙米湯”敵特的活動區域——“黑”。而報童等劇中人物便可以活動在路燈的光照之下——“白”。
我在處理歌劇《江姐》整個舞臺時,強化了素描的線條質感,大平臺、山城、城墻城門、竹林、榕樹、草等,這些景片都以強烈的線條繪出立體感和明暗關系,強化了繪畫風格,并不是單一的灰色調。按照每一幕的環境暗示,線條時而張狂時而隱忍,體現了每一個場景中角色當時內心的微妙變化以及外部的行動,可以說線條就是一種情緒、是人物的內心外化。比如,第四幕城郊,整個場景中榕樹安靜地佇立在舞臺右側,看似平和,但是景片的繪畫風格是硬朗的,線條硬度猶如針刺一般,暗示著一場“截軍火”的秘密行動即將上演。然后,第七幕的舞臺上以黑白灰的主基調展現,時黑時白,暗示著舞臺上敵我關系的激烈狀況。直至尾聲,出現紅梅的紅色,是全劇唯一的紅色,意味著光明的到來。同時,黑白的舞臺環境,讓身著服裝的人物在整個舞臺中更為凸顯,起到了“綠葉”的效果。其實,這就是形象的一種“神似”。“神似”的寫意戲劇觀是我們傳統的美學思想和藝術趣味,在千百年來的藝術實踐中形成的一種藝術觀念的結晶。藝術趣味是活潑的、空靈的、喜歡以獨特的“傳神之筆”別具一格地描繪出事物的靈魂。這種美學觀念和創作手法也是所謂的“寫意性”。(陳靈芝《淺談舞臺美術的寫意性》)
(二)
寫實的現實主義要求觀眾忘記他們是在劇場里,也就是將觀眾的注意力拉到角色所處的環境里,而寫意的現實主義希望觀眾注意的是正在演戲的演員所處的環境,也就是觀眾同樣作為“第三只眼”審視演員如何表演角色。(姜訓祿 《寫意——舞臺現實主義的另一種形式》)在舞美創作中,我使用了貫穿整個舞臺的平臺,并帶有一定的斜度,從左至右、從前至后都有不同斜度,雖會有些不平衡,但還是符合演員表演和演唱的接受度。傾斜的狀態其實暗示著劇情中那種不平衡的狀態。這就是舞臺美術設計的象征性寓意。舞臺美術最講究空靈、自由、寫意,最忌諱太真、太實,這樣是為了給演員留出充分的表演空間,讓演員最大限度地發揮表演才能。(任娜《談舞臺美術的象征性寫意手段》)而大平臺上模擬的中性臺階,在每一幕中可以擔任環境的定位,譬如山城、華鎣山、渣滓洞。功能性上還滿足了歌隊的站位調度,讓聲部可以更好發揮,也滿足了視覺畫面的美感。讓觀眾能夠更好地專注于演員的表演,關注演員如何詮釋角色。
“寫意”要求對舞臺物象的外在逼真性加以提煉、概括,強調不求形同,強化內在的神似,即“似與不似”。北宋蘇軾曾有詩道:“所形似,見與兒童鄰”。這句詩的意思是如果畫畫只能畫得像,這跟小孩的水平差不多。舞臺創作也如此,只能作其形、似其形,那只能是還原了一個當時的環境,而缺少了創作者對劇本的個性解讀和詮釋。
歌劇《江姐》首演于1964年,我作為一個新生代設計師,對于經典紅色題材需要有自己的理解和詮釋。在當下看這個劇本,跟當時人們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不僅要看江姐的故事,同時也要對這個紅色題材經典作品本身再一次解讀。所以我希望用一種有變化的方式去詮釋舞臺。這就是為什么用寫意的手法、用黑白素描的方式去表現的原因。故事中具體的形象已經漸漸被人們淡忘,但江姐的氣質、精神還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素描是一種經過歷史過濾后沉淀下來的感覺,重新解讀這段歷史我認為這是最佳選擇。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審美要求、審美風格、審美趣味,所以我需要形成新的創作風格、尋找獨有的審美認知,這個結果和認知需要經歷一個回顧的過程、需要對每個場景做一個提煉。
(三)
實際上,歌劇《江姐》舞美創作意涵更多的還是紅色主題。今年是慶祝建黨100周年,正好借這一個歷史節點回顧這樣一段歷史,我們能更真切感受到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來之不易的、是付出了巨大代價和犧牲的。歷史帶給我們一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財富,而精神力量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影響著整個作品。比如我在舞臺上會用到比較多的直線造型,去找那種比較硬的形象,找到了一種力量感。原來考慮的是黑白素描,像銅版畫一樣的風格,但是當繪畫風格過于強烈的時候會淹沒掉很多具體的歷史形象,而這些歷史形象本身是很有質感的,所以要往回收一點。
作為一個舞臺藝術工作者應有自己堅持的美學理念、個人風格等,藝術感覺是非常個人的,最可貴的也在這里。這個新經典作品的核心是它的內容,形式上的沖擊力也是構成藝術感染力的核心要素,但如果過于抽象的話就會把時代背景、故事背景削弱。所以說所謂的修正,是在形式之上增強具象的成分。我在創作過程中得到了啟發,用直線造型為主,比如說竹子這個形象,我沒有用具象的畫法去表現,而是用線條組合,這是一種藝術表達方式,這樣就跟總體的線條走向、大結構吻合了、統一了,同時對環境也有了交代,保持了這個戲特有的視覺沖擊。另外,我還對“聯絡站”的處理反復修改了幾次,原來是斜向的構圖,從視覺形式上肯定更加有構圖感,但這里就要考慮人物的形象、身份,所以我最后還是讓它盡量正,不能感覺是一個陰暗的角落。這些舞臺形象都和主題內容有著直接關系。尾聲的紅梅,現在處理得層層疊疊,漫山遍野的梅花不是完全寫實的,以體現氛圍為主,燈光效果加上后就是烘托氣氛的最好方式。
面對紅色題材經典作品的時候,我認為基本的方向、基本的認知不會因為隔代就有根本上的不同,內在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這也是這個作品能夠經受時間檢驗、接受不同時代觀眾考驗而繼續流傳的原因。在眼下多元化的審美中,舞臺美術無疑面臨著各種視覺要求的審視,有普通觀眾的審美需求,有專業觀眾和藝術家的審美要求,但是舞臺形式、流派的融合化發展是必需的。不論最終呈現出來的舞臺是“寫實”還是“寫意”,只要能把戲劇內容本身詮釋表達得恰當、完美,都是創作者的一次完美詮釋。? (作者為上海歌劇院舞美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