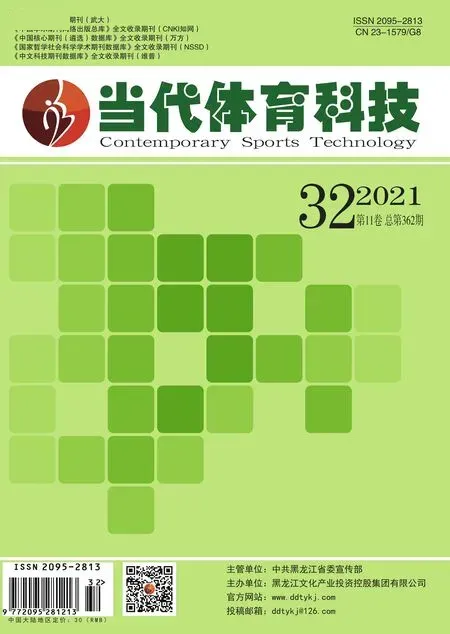腦神經科學視野下的人類動作發展學研究趨勢
褚付成 李繼輝* 張海霞
(1.山東華宇工學院基礎教學部 山東德州 253034;2.沈陽體育學院研究生院 遼寧沈陽 110102)
腦神經科學是研究人和動物神經系統結構和功能的科學,是探索腦的科學,作為生命科學的一個分支,該學科已成為此領域內最重要和最為活躍的學科之一[1]。大腦是思想和行為的源發地,更是人類個各項發展的基礎[2]。人類個體的發展主要涉及身體、動作、情感和認知4 個方面,其中動作是人適應環境的重要途徑,也是一生中最早的發展之一,被認為是個體發展的重要任務[3]。然而,動作不是孤立發展的,研究顯示個體幼年的動作發展水平對認知表現[4,5]、社交能力[6]、身體活動參與度[7,8]、學業水平[9]以及自信心[10]都有正向促進的作用。雖然我國近年來在人類動作發展的描述研究與預測研究上卓有成效,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復雜問題的突顯,研究難度的增加。動作發展領域的研究亟待從一個新的視角進一步推進。基于此,該文梳理了2000—2020年國內外有關動作發展和腦神經科學研究文獻和書籍,探尋動作發展研究的新視角,為我國學者進一步研究人類動作發展提供視角參考。
1 動作發展研究的新困境
關于人類動作發展的研究早在1787年德國學者蒂德曼(Tiedemann)撰寫的《嬰兒行為日記》中就有記載。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理論體系的不斷豐富人類動作發展已發展成一門研究人類一生中動作行為的變化、構成這些變化的過程以及影響因素的科學[3]。人類動作發展的研究成果對個體發展具有許多積極影響,促進其他各項協調發展,為生長發育中的不正常情況提供科學的動作診斷標準,指導人們合理鍛煉等。但是,隨著人類動作發展深入研究和快速發展,出現以下困境。
1.1 研究范式對研究思路的束縛
科學的最終目標是理解世界,科學意義上的理解包括4個遞進的特殊目的:描述、預測、解釋和控制[11]。我國動作發展領域的研究雖然經過了理論解釋、理論本土化、理論創新發展、理論與實踐結合、實踐探索等階段。但從諸多文獻的研究類型上看,當前的兒童動作發展研究類型分為3種:基于動作發展的規律與身體各種能力的關系研究[12-15]、對兒童動作發展進行一般性描述[16-18]和動作發展文獻綜述類研究[19-22]。祝大鵬梳理了國內外44篇文獻,對兒童動作發展的理論方法、測評與發展趨勢進行了綜述性研究,得出國內關于兒童動作發展的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兩種:一種是對國內3~10歲兒童的動作發展進行一般性描述;另一種是對國內外兒童動作發展水平或國內不同地區兒童的動作發展水平的比較研究[21]。焦喜便通過對中外體育學動作發展動態進行可視化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定量研究方法較少;研究內容涉及的主題較少[23]。對兒童動作發展一般性描述或動作發展對兒童全面發展的意義等描述、預測的研究較多。對國外測評工具的信效度驗證,TGMD-2主要內容及其重要作用的研究[24],TGMD-2信度和效度的研究[25],以及TGMD-3 的信、效度的研究[26]。另外,關于動作發展與身體能力的研究,包括幼兒靜態平衡能力特征及粗大動作發展水平[27],移動性動作發展與感知身體能力的相關性[28],兒童感知運動能力與基本動作技能的相關性研究[29]等。以上研究結果反映出我國動作發展領域的研究仍停留在對兒童動作描述及預測的相關性研究階段。我國在動作發展領域初期范式的確定有利于基礎研究的展開,但已經不能適應當下認識的需要,該領域的研究迫切需要多學科交叉融合來解決新的復雜問題。
1.2 動作發展與腦神經科學交叉研究未得到充分重視
動作發展作為人類運動學系(Kinesiology)下動作行為(motor behavior)的一個分支學科進行研究,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人們一生中所體驗到的動作行為的變化[3]。人類動作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5個時期:前導時期(1787—1928)、成熟論時期(1928—1946)、描述時期、過程導向時期(1946—1970)以及2000 年至今即動作神經科學時期(Development Motor Neuroscience Period)[30]。最近20年伴隨著科技的進步,腦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在先進技術的輔助下有了長足的發展,檢測活體腦結構形態新技術——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術(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PET)和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12]基于腦中血流量變化的檢測原理被應用在醫學和科學研究中,為神經學家提供了不同尋常的機會來觀察活體思考中的腦。未來在人類動作發展領域借助計算神經科學家的概念和方法,人們可以采用工程學和神經解剖原理為動作建模[3]。通過對CNKI 學術期刊數據庫檢索,我國近年來未發現有關于動作發展與腦神經科學的交叉研究,腦科學與體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運動對兒童執行功能的腦機制研究,以及運動與腦的可塑性關系的研究,而且類似運動對兒童執行功能影響的實證性研究文獻較少[31],腦的可塑性研究相對較多,周期較長從2006 年至2020 年都在進行研究[32,36]。由上可知,雖然早在2008 年國內外學者認為人類動作發展已經進入動作神經科學研究時期,但動作發展與腦神經科學的理論與實證并未實現融合,交叉研究未得到充分重視。
2 動作發展研究的新方向:動作發展+神經科學
2.1 動作神經科學相關的研究進展
“神經科學”一詞的提出并不久遠,美國神經科學學會直到1970年才成立,國內研究認為大腦是一個復雜動態的系統,在學習、訓練以及經驗等因素的影響下大腦的結構和功能會出現改變和重組[37];并認為這些變化包括腦重的變化、皮層厚度的變化、不同腦區溝回面積的改變等,以及結構上的樹突長度的增加、樹突棘密度的改變、神經元數量的改變及大腦皮層新陳代謝的變化等[38]。
腦神經科學研究論文總量迅速增長,查閱CNKI數據庫,以“腦的可塑性”為主題搜索時間為1985—2020年,共檢索到418 篇研究文獻,如表1 所示。從1985—1995年10間文獻發表量為6篇;從1995—2005年10年間所發文獻量為92篇,從2005—2020年15年間文獻發表量為320篇。表明近些年我國對腦科學的研究有較高的重視程度,隨著腦科學研究的深入和文獻量的增長,神經科學的知識和研究成果增加,可以采用腦神經學理論解釋動作發展規律,將會使動作發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更具實證性。

圖1 總庫1985—2020年腦的可塑性發文量統計圖

表1 我國1985—2020年腦的可塑性論文初步統計
2.5 動作發展與腦神經科學交叉研究
隨著神經科學的快速發展、“神經科學+”時代的到來[39],神經科學與人類動作發展交叉融合成為新的趨勢,成為解決動作發展研究困境的新方向。個體早期動作發展描述、預測研究與腦神經科學的理論研究是解決動作發展的外在和內在的兩大助力。腦神經科學的理論研究為動作發展現象描述提供了理論解釋,動作發展現象的描述為腦神經科學理論提供了驗證途徑。
腦成像技術和計算機科學的革命性進步逐步實現了對腦結構、神經元活動的觀察與監測。最具代表性的新技術包括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彌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FMRI 是基于檢測細胞消耗的能量與血流變化進測量腦部活動;DTI能夠揭示腦不同區域之間的連接,掃描和診斷深層的腦結構變化。利用這些新技術能夠監測個體在一次運動中運動技能的表現與腦血流量變化的關系,還能追蹤觀察動作發展對腦結構以及不同腦區之間的連接效度的影響,為教育決策提供依據。基于以上現代技術的支撐,國外學者進行了諸多關于腦結構和功能與運動技能的相關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運動控制與技能學習領域的研究人員劉展[40]通過對國外小腦的前沿研究的梳理認為:小腦在認知、抽象思維、計劃、情感、記憶和語言等方面有較大的貢獻,顛覆了傳統理論認為的只能控制和調節身體運動的舊觀點,并從神經科學視角下闡述了大腦、小腦和運動之間的相互促進發展的規律。國內學者陳愛國等在腦與運動研究比較有代表性,并已發表了多篇高質量的相關論文,認為體育運動可以通過系統水平、細胞水平、分子水平等多維途徑影響腦的可塑性,進而對兒童的認知功能也產生相應積極改變[41]。體育運動不僅能夠改善兒童的認知功能,另有新的研究顯示體育鍛煉顯著改善了青少年學生的認知能力,并進一步提升了青少年學生的學科成績[42]。有研究認為:影響腦可塑性的因素包括早期經驗與環境、腦損傷和性別;早期經驗與環境不僅會對腦結構、機能發展產生影響,而且豐富的環境刺激還能對腦損傷后的恢復產生積極影響[41]。腦科學研究發現[12]:個體發育早期是運動神經元與肌纖維建立聯系的敏感期,但是受學習、訓練以及經驗等因素的影響。經驗本身也存在區別,利于大腦潛能開發的適宜環境,其對大腦的影響有時是積極的,反之則是消極的[43]。因此,選擇科學性干預計劃的是能否促進兒童正向發展的前提,而干預計劃的科學性則需要深入地對動作發展理論和腦神經科學理論進行研究,只有融合這兩個領域前沿理論,并在其指導下才能充分發揮出運動干預的效能,服務于我國基層的體育教育,切實可行地促進我國兒童身體、動作、情感和認知發展。
由此可以看出,在現代科技的推動下,人類動作發展的研究需要借助科技之力突破當前研究的困境,在“神經科學+”時代背景下,交叉融合多學科知識。
3 結語
兒童是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兒童的健康狀況始終是世界各個國家關注的焦點。近年來,人類動作發展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兒童階段,然而人類個體一生中動作都在不斷發展中,隨著動作發展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范圍也會逐漸覆蓋個體整個人生的各個階段。無論是研究兒童動作發展規律,還是人生各個階段的動作發展規律,都離不開腦神經科學知識進行本質分析。該文通過梳理國內外神經科學知識與人類動作發展現狀發現:腦神經科學與人類動作發展交叉研究對動作發展規律的揭示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未來我國人類動作發展研究理論應更多地融合入神經科學的知識,增加干預實驗研究將研究結果服務切實可行的一線教育。
近年來,腦神經科學研究論文總量增長迅速,但神經科學的知識在人類動作發展研究領域尚未得到應用;國內關于動作發展研究仍處在描述和預測階段,神經科學與人類動作發展交叉融合成為新的趨勢,成為解決動作發展研究困境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