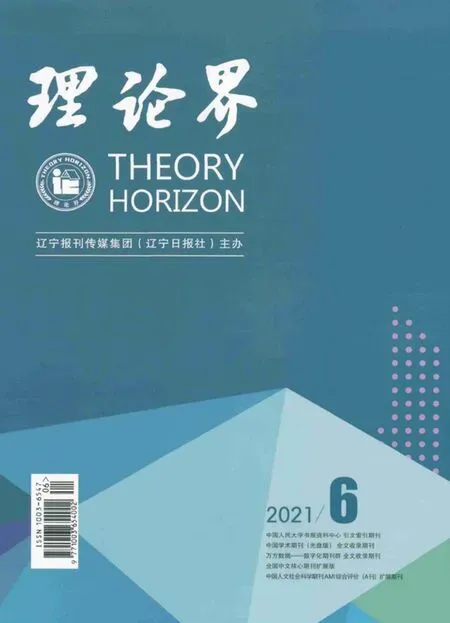葛蘭西實踐性意識形態思想的地位與影響
孫璐楊 伍志燕
葛蘭西的思想不僅對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為歐洲的文化思想研究打開了新的突破口。非洲民族獨立的偉大戰士、第三世界政治思想家弗朗茨·發農(Frantz Fanon)和巴西的人民教育家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在領導被壓迫民眾奮起反抗的時候,他們的思想中總能找到葛蘭西實踐性意識形態思想的基因。英國的文化研究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斯圖亞特·霍爾從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中汲取營養,承認人的能動性的重要性,認為民眾可以通過文化(敘事、圖像、音樂、對象)的創造,建構民眾自己的階級,建構一種新的民族與人民的話語權。拉克勞和墨菲在后現代語境中通過對葛蘭西的領導權的分析,將其改造成為一種話語實踐的理論,而且以此作為激進民主的戰略基礎。葛蘭西對以上思想家的影響,國內外學者已經進行過豐富的探討。但是,葛蘭西實踐性意識形態思想對阿爾都塞、齊澤克以及馬爾庫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影響,卻鮮有學者研究。
一、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實踐的物質保障
阿爾都塞在肯定葛蘭西實踐性意識形態思想的基礎上,繼承并發展了該思想中的“市民社會”理論以及“主體性”理論,將以上兩個要素成功地吸收到自己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思想當中。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必須是實踐的,更是一種物質的現實性的存在。他評價馬克思是階級意識形態斗爭的先驅,正是在意識形態斗爭的實踐中,“迫使馬克思非常早地——從他青年時期的著作開始”,〔1〕就承認意識形態實踐在意識形態斗爭以及政治斗爭中的重要角色。同時,他高度肯定了葛蘭西對現實與實踐問題的觀照。阿爾都塞認為,葛蘭西的意識形態思想是“向人們發出的投入‘實踐’、投入政治活動、投入‘世界改造’的直接呼吁”。〔2〕在馬克思與列寧之后,真正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努力捍衛馬克思主義事業的人,“據我所知只有葛蘭西”。〔3〕
1.“市民社會”的另類詮釋
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已經明確地將國家構想為一種“鎮壓性機器”。阿爾都塞認為,將國家看成資產階級和他的同盟針對無產階級的斗爭的鎮壓性的干預,這觸及了“國家”的本質,也定義了國家的基本“功能”,但這種對“國家性質的表達也仍然是描述性的”。〔1〕阿爾都塞將“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進行了對比,認為無產階級在革命斗爭中必須奪取“國家政權”,并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代之以無產階級“國家機器”。阿爾都塞在對鎮壓性“國家機器”與“國家政權”進行區分的探討中,發現資產階級在對無產階級進行壓制的過程中,有一個“現實”的東西猶如幽靈一樣無處不在,并且對無產階級民眾有著極強的迷惑與統治功能。這個幽靈不同于“國家機器”包含的內容,政府、行政部門、軍隊、警察、法院、監獄這些機器使用的是肉體的暴力,他們并不能完全解釋資本主義存在與運行的原因,而真正能解釋這個原因的是“我們將冒著理論風險把這種現實叫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1〕但是,發現這個奧秘的第一人是葛蘭西,答案應該到葛蘭西的市民社會思想中去尋找。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就是“一個由各種確定的機構、組織和相應的實踐所組成的系統”,〔1〕在這個系統的各種機構、組織和實踐中得以實現,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些機構與組織包括:教育機器、家庭機器、宗教機器、政治機器、工會機器、傳播機器、出版發行機器以及文化機器等。很明顯,被阿爾都塞稱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這些機構和葛蘭西市民社會思想中的豐富要素有多處重合,也正如阿爾都塞所說:“這就是我——追隨葛蘭西——稱之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制度的東西,它指的是一套意識形態的、宗教的、道德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審美的以及諸如此類的機構。”〔4〕阿爾都塞認為,資本主義正是通過對這些機構的運用,維護了自身統治的穩固。
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生產服從的同時,也生產了勞動力,即“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再生產”與“服從”兩者之間又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關系,它們不斷鞏固著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對工人進行“管理”,幫助工人“學會了一些技能,同時還學到了不少別的東西,包括‘科學文化’或‘文學’方面的一些要素”,〔1〕也正是在機構中習得的這些本領,幫助他們成為一個合格的工人。同時,又潛移默化地讓工人學習良好的舉止規范,說到底“就是由階級統治建立起來的秩序的規范”。〔1〕從此,工人就成了資本家的奴仆,并以積極的心態臣服于統治他的階級。
2.意識形態實踐的實質:摒棄“偽主體”
葛蘭西認為,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主體意識以及革命斗爭意識,已經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浸染中近乎消失,無產階級只有通過意識形態實踐斗爭,建構自己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才能重新喚回自己的主體性。葛蘭西意識形態主體性建構功能的思想影響了阿爾都塞。阿爾都塞認為,無產階級之所以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蒙蔽,是因為資產階級給無產階級制造了一個“主體”的幻覺,讓無產者以為自己就是社會的主體,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事實上此處的“主體”是“偽主體”,是資產階級奴役無產階級的工具,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丑陋本質的展現。當無產階級認為自己已經擁有了主體性的時候,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便得到了成功的實踐。阿爾都塞認為,這種“主體性”是非主體性,只有對這種主體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無產階級才能展現“真我”,建構真正的主體地位。
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的存在就是為了主體地位的建構,并且意識形態的存在又必須依靠主體。資本主義憑借對人的主體地位的建構,戰勝了封建專制,也澆筑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堡壘。在主體與意識形態雙重構成的運作中,“存在著所有意識形態的功能的發揮”。〔1〕阿爾都塞認為,“個人——甚至在出生前——總是——已經是主體”,〔1〕人生來是主體這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但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蒙蔽的人們“對此一無所知,卻在勤勉為之”。〔5〕阿爾都塞認為,孩子從降生的那一刻起,家庭便爭取為他創造更好的環境,為他設定好的發展規劃。此時此刻,孩子是占據家庭主體地位的家庭成員。可是,細究便發現孩子是“被主體”,因為從最初的那一刻起他并不擁有主動性。同時,與主體相伴而生的便是意識形態的建構。這個孩子被寄予的期望,其實也就是這個家庭的意識形態,這個家庭的意識形態追根溯源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正是如此,“通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實踐儀式發揮功能”,〔1〕一邊制造虛假的主體,一邊鞏固自己的意識形態。阿爾都塞通過對資產階級構造的主體性的批判,揭示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虛幻性,啟示無產階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被虛假的主體與虛幻的意識形態所迷惑。無產階級只有摧毀這個迷局,才能發現真的自我。
二、“自在自為”的意識形態:實踐性意識形態的黑格爾式嫁接
布哈林站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高度,認為上層建筑是物質世界的反映,上層建筑不能脫離勞動者的勞動而存在,因此,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也是一種物質化的存在,它“凝結為物,并且也在完全是物質的客體中積累起來”。〔6〕布哈林認為,這種物質化的存在以勞動為前提,勞動分為物質勞動與上層建筑的各種勞動,意識形態勞動與物質勞動并行不悖,都具有一定的階級性,并以一定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為前提。盡管布哈林觸及了意識形態物質性的范疇,但是意識形態的本質并沒有改變,依然附庸于經濟基礎,即“這些意識形態的‘生產部門’的分工,歸根到底,決定于社會經濟結構”。〔6〕真正明確提出意識形態物質性范疇的是葛蘭西。葛蘭西認為,市民社會中的印刷工業,它不僅是一種物質工具也是一種上層建筑。印刷行業承載著某個階級的政治、宗教、道德、科學與文學,通過宣傳達到意識形態實踐的效果。除此之外,學校、教堂、研究機構這種市民社會中的物質性要素,也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無產階級在革命實踐中只有掌握這些意識形態的物質性要素,才能把握革命實踐的主動權。阿爾都塞認為,承載著資產階級宗教、道德、法律以及政治、審美、文化、教育的這些機構,都屬于意識形態機器,而意識形態就“存在于這種機器的某種實踐或多種實踐當中,這種存在就是物質的存在”。〔1〕無產階級的生產性行為由資產階級的物質性意識形態機器規定,無產階級的實踐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實踐。齊澤克對葛蘭西所闡明又經阿爾都塞發展的意識形態物質性思想進行了創造。齊澤克認為,意識形態已經成為整個社會,乃至整個人類文明不容或缺的一種實踐性的物質性力量。
1.物質性意識形態:癡迷于實踐的幽靈
葛蘭西將市民社會中眾多的要素看作意識形態的物質性體現,認為資本主義市民社會運轉的過程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實踐的過程,無產階級要對這些物質性要素進行攻克與轉換,占有這些物質性要素從而重獲并鞏固自己的主體地位。阿爾都塞認為,無產階級之所以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蒙蔽,是因為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構造了一個虛偽的主體。因此,無產階級要獲取真正的主體性,首先應該批判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構造的虛假主體。葛蘭西、阿爾都塞之后,齊澤克再次扛起以對主體性的探究為切口的深入剖析意識形態物質性范疇的旗幟。齊澤克認為,意識形態本就是一種物質性的存在,它在任何角落都自在自為地實踐著。無產階級要想獲得身份的反轉,境況不容樂觀。
齊澤克認為,“狗智主義”已經發展成為意識形態的主要形式,傳統的意識形態批判程序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作用已經喪失。布衣百姓不管怎樣用陳詞濫調反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并揭露資產階級鮮艷皮囊下的自利、血腥與暴力,都不能真正動搖狗智主義意識形態。狗智主義是資產階級的幫辦,這些幫辦用狗智智慧(CynicalWisdom)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梳妝打扮。狗智主義“把正直、誠實視為最高形式的欺詐,把品行端正視為最高形式的放蕩不羈,把真理視為最有效的謊言形式”。〔7〕他們的任務就是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做最變態的肯定。在這種情況下,“意識形態不僅是謊言,而且是被視為真理的謊言”,〔7〕它在社會結構層面已經成為社會現實的物質性存在。齊澤克將這種現實稱作“意識形態幻象”。意識形態幻象即無意識幻象,齊澤克把意識形態置入無意識領域。幻覺之所以可以成立,是由于人們已經忽視了幻覺,“幻覺正在結構我們與現實之間的真實、有效的聯系”。〔7〕幻覺讓無產階級肯定自身的價值屬性和行為舉止,肯定自身正處于現實實踐之中,但是無產階級忽略了他們正受到幻覺的引導。幻覺真正的由來是主體的欲望,主體借助幻覺彌補自身的缺失。于是,意識形態便成為主體彌補自身在真實世界中欲望缺失的麻醉劑。意識形態已經不是一種遮蔽人們意識的虛假觀念,而是主體構造自身現實的社會物質性存在。欲望的主體,通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來證明自己的價值與自在存在。“意識形態因素成了結構化的意義網絡(Structured Network of Meaning)的一部分”,〔7〕成為一種物質性力量,治愈無產階級在社會現實實踐中存在的創傷,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正常運行的有力保證。意識形態幫助勞動者撫平現實的缺口與原始沖動。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已經成為無產階級自證其存在的“良藥”,離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無產階級的欲望將無法“彌補”,創傷將無法“縫合”。
2.自發實踐的意識形態
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影響了齊澤克的哲學思想與哲學研究方法,尤其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以及矛盾分析法。拉康的精神分析思想為齊澤克提供了分析問題的術語和概念框架。馬克思的作品為齊澤克提供了著作背后的動機或原因,齊澤克意識形態思想旨在探究商品拜物教背后的奧妙所在。宗教的構成在黑格爾那里主要包含三種要素,即教義、儀式和信仰。齊澤克按照黑格爾對宗教要素的概括,將意識形態分成三個形式:作為觀念復合體的意識形態、客觀形式的意識形態與自發的意識形態。這三種意識形態并不是前后繼承的關系,而是共時的關系。齊澤克認為這三個形式的意識形態,符合黑格爾式的自在、自為、自在自為的三個組合。在此基礎上,齊澤克進一步對葛蘭西以來的意識形態物質性思想進行拓展與創造,豐富了意識形態實踐的內涵。
作為觀念復合體的意識形態,主要通過以下形式實踐,即概念、理論、信仰與論證過程等。作為觀念復合體的意識形態存在的目的是為統治階級的權力服務,讓被統治階級將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作為自己行動的真理。這種意識形態掩藏了統治階級的自利、暴力與丑陋,歌頌的是官方意識形態的自由、正義與平等。這種意識形態缺乏實踐活動的自主性,它自身被規定之后很難再產生新的內容,是一種自在的意識形態。“自為的”意識形態如同宗教里面的儀式一樣,是客觀的物質存在,即“意識形態的物質性,意識形態國家機器”。〔8〕自為的意識形態具有較大的能動性,可以改變自己的狀態并外化為一定的形式,進行自我實踐。自為的意識形態有規定性,可以外化為一種機構,一種客觀存在的意識形態,但“這種規定性不再是有限的規定性,有如某物與別物有區別那樣的規定性,而是包含區別并揚棄區別的無限的規定性”。〔9〕齊澤克認為,自為的意識形態就是葛蘭西市民社會思想中的諸要素,以及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概念所概括的契機”。〔8〕教會作為宗教信仰的載體,是一種物質性機構,它運轉的基礎并不是信仰本身,而是它背后的體制機制。下跪、祈禱、懺悔作為客觀存在的意識形態實踐過程中的儀式,顛覆了信仰的本質。信仰的本質規定是由于信仰才下跪,但是在自為的意識形態中“跪下,那么你就會相信你是因為自己的信仰”。〔8〕正是因為人們要肯定自己對宗教的信仰,他們才接受自為的意識形態中“跪下”這一儀式。民眾自愿接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因為他們要彌補自己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不足。自在自為的意識形態即自發的意識形態,它不同于被規定的刻板的信條與理論,也不同于物質性的意識形態客觀存在,它如同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一樣,可以自足地形成一個意識形態實踐的網絡。齊澤克認為,這種意識形態事實上是一種幻覺,它支撐起主體的整個現實,并結構主體的社會活動。換言之,齊澤克所謂的意識形態幻象是一種社會活動的抽象假定,它決定了主體感知現實的形式,進而支撐著包含“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內的社會物質活動本身。
三、達到“愛欲”的解放:意識形態實踐的最高訴求
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對商品和勞動者物化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并提出物化意識思想。盧卡奇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中,物化意識已經占據了無產者的頭腦,無產階級已經完全失去了階級意識與革命意識。無產階級進行斗爭,首先要消除物化與異化。生產結構轉型時期的意大利,資本家越來越富裕,勞動者卻變得一貧如洗,葛蘭西認為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勞動。阿多諾與霍克海默認為,工業已經失去了它應有的理性,而用它的非理性控制著人。面對異化的工業,只要消費者使用了它,那么它就會將消費者圖畫式。文化工業已經同統治階級的意志完美結合,并轉化成一種意識形態統治著無產階級,欺騙著人民大眾。如果不遵從,將“意味著在經濟上和精神上的軟弱無力,意味著‘受雇于自己’”。〔10〕馬爾庫塞作為阿多諾與霍克海默的同時代人,發現資本主義國家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得到了提升,但是政治與文化思想并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他發現科學技術和政治沆瀣一氣并控制著人們的思想。“一種舒舒服服、平平穩穩、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流行”,〔11〕科學技術成為統治階級的一種意識形態,取得了統治的合理性。馬爾庫塞認為,愛欲是人最本質的特征,科學技術正是通過利用與壓制人的愛欲,使人沉淪在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之下,因此,要解放人的愛欲。由于技術合理性的介入,人類原始作為“快樂原則”的心理機制轉換成“現實原則”。在“現實原則”中被壓抑的人將最后的避難場寄托給藝術,但“藝術異化跟其他否定方式一道屈從于技術合理性的進程”。〔11〕馬爾庫塞認為,藝術異化是當代工業社會異化過程中最高水平的一種異化。藝術不再發揮自身的批判功能,而變得更加和諧,服從統治階級擬定的一種秩序。因此,要實現“愛欲”的解放,必須為藝術松綁,而“愛欲”的解放是人類最終的解放,是人自由的實現。
1.意識形態實踐的“愛欲”解放途徑
在無產階級通過“運動戰”直接去與資產階級政權作斗爭又屢屢失敗的情況下,葛蘭西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應該轉變斗爭戰略。葛蘭西認為,資產階級之所以獲得如此穩定的統治,是因為擁有“市民社會”這一堅固堡壘。無產階級應該以實踐哲學為武器,進行意識形態實踐斗爭,建立總體性的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政權。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成為法蘭克福學派以及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重要思想來源。道格拉斯·凱爾納在《批評理論與文化研究:未能達成的接合》一文中提出,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的誕生為西方文化研究轉向提供了契機,這場文化研究的轉向是一種“葛蘭西轉向”。馬爾庫塞繼承了葛蘭西實踐性意識形態思想中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將文化和藝術的解放作為無產階級解放與人類解放的鑰匙。
20世紀中后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財富變得較為充裕,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到了資本的“紅利”,科學與技術的產物也相應進入尋常無產階級家庭。表面上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相安無事,但馬爾庫塞提醒我們,資產階級時刻都壓迫著無產階級的精神與生活。馬爾庫塞認為,在這樣的環境中,無產階級“獨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對權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會逐漸被剝奪”。〔11〕科學與技術充當著資產階級的爪牙,在高精度的生產儀器面前,生產者已經成為了它的附庸。無產階級不僅失去了勞動的意識,也失去了獨立思考與提出問題的能力。技術已經漸漸喪失了解放的功能,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融為一體,并取得了意識形態合理性。在這種技術理性支配下,人類本能的“快樂原則”服從社會的“現實原則”,技術的壓抑使得勞動者力比多不能實現自我超越,愛欲也得不到釋放。可愛欲是人類生命的本質,是人類發展最高的境界。因此,無產階級要將自己從被壓抑中解放出來。
馬爾庫塞認為,技術理性意識形態不僅滲透進政治、經濟領域,而且滲透進人類的文化思想領域。在技術理性意識形態的作用下,高級文化已經被駁倒,因為文化工業需要建構文化的一致性,“通過把它們全盤并入既定秩序,在大眾規模上再生和展現它們”。〔11〕在技術合理性的支配下,個性思想與獨立思維遭到扼殺,批判性觀念被同化,勞動者變成一個“單向度”的人。當無產階級開口說話的時候,他們表達應用的語言是“他們主人、恩人、廣告商的語言”。〔11〕馬爾庫塞認為,當無產階級已經不具備批判思想與革命思維的時候,便需要開展對他們的思想啟蒙。藝術革命是思想啟蒙的第一步,因為藝術的解放能激起無產者力比多在最大限度的釋放,同樣也是他們愛欲在最大程度上的解放。馬爾庫塞認為,藝術具有革命功能,藝術的革命功能與美學結合在一起,美學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超越現實,通過幻想打破現實的蒙蔽,去構想一種自由,對現實進行公訴。無產階級可以借助藝術表達自己的理想,使自己的壓抑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從而獲得一種鼓舞人心的效果,進一步團結大眾去斗爭。藝術不用服務現實,它的意義在于否定現實,“不斷提出將人從存在的悲慘境地中解放出來的要求”。〔12〕
2.“愛欲”解放的歸宿:人的自由解放
葛蘭西欲通過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實踐,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反領導權,使無產階級重新獲得自己的主體地位。進一步推動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從而將人類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束縛中解放出來。馬爾庫塞將葛蘭西實踐性意識形態思想中的文化內涵挖掘出來,堅持同技術理性意識形態作斗爭。把文化與藝術看作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中的核心,通過藝術喚醒人類最初的欲望,激發民眾的力比多并踴躍同資產階級作斗爭,從而解放自己,解放全人類。
馬爾庫塞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質就是將民眾從“剩余壓抑”中解放出來的一種意識革命,一種追求自由的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實踐旨在創造一種非壓抑的文明,社會主義運動就是為愛欲而戰、為生命而戰,將人的本質從資產階級技術理性的意識形態中釋放出來。關于人的本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13〕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六條中指出,人的本質在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4〕將以上兩種論述加以概括,人的本質就是在社會關系總和中可以自由自覺地從事社會生產勞動。葛蘭西認為,人時刻處在一系列能動的關系之中,這種關系不是機械的,而是“能動的和有意識的”。〔15〕馬爾庫塞直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民眾的勞動是被動的勞動,是受壓抑的勞動。它屬于一種“額外壓抑”,這種壓抑是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強加于民眾的。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民眾不具有自我意識。勞動本來應該是民眾的一種自在、有目的、自由的愛欲活動,但在發達工業社會中,在技術理性的支配下,人的本質已經喪失,人成了“單面人”。為消除這種理性的控制,馬爾庫塞決定建立一種新理性,即批判理性,而這個批判理性的依托就是藝術。藝術具有極強的批判功能,它表達著人們的向往與價值追求。真正的藝術是人把握世界的一種特定的方式,也是人的一種生存方式,并且它集中地表現了人的本質,即愛欲。藝術代表著一種新的價值,這種新的價值推動技術、科學與社會重新結合,“從而實現人和自然的雙重解放,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