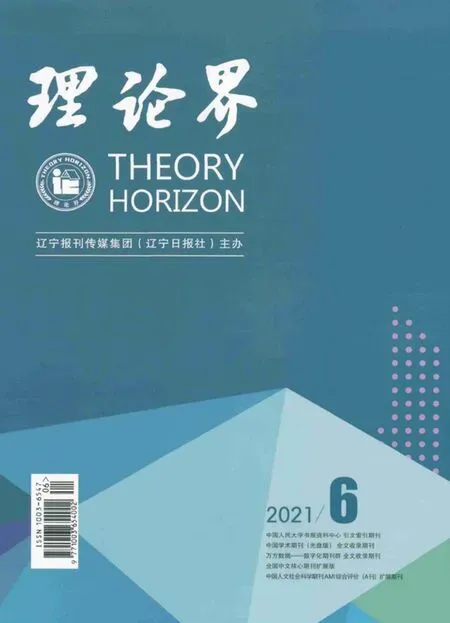《邏輯學(xué)》開(kāi)端問(wèn)題三辯——對(duì)霍爾蓋特導(dǎo)論的補(bǔ)充
劉 宸
英國(guó)哲學(xué)家斯蒂芬·霍爾蓋特(Stephen Houlgate)對(duì)黑格爾哲學(xué)的導(dǎo)讀往往以清晰的論述和深刻的洞見(jiàn)為人稱道。J.M.伯恩斯坦曾將他的導(dǎo)讀稱為“我們能夠讀到的最好的黑格爾哲學(xué)導(dǎo)論”。他認(rèn)為霍爾蓋特耐心地指引我們注意黑格爾思想的深刻性和豐富性,為讀者閱讀黑格爾著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某種程度上說(shuō),這樣的評(píng)價(jià)確實(shí)是實(shí)至名歸,正如我們?cè)凇逗诟駹枴催壿媽W(xué)〉的開(kāi)端:從有到無(wú)限》(TheOpening ofHegel’sLogic:FromBeingtoInfinity)一書(shū)中看到的,霍爾蓋特在第二章用了近25頁(yè)篇幅介紹《邏輯學(xué)》的開(kāi)端問(wèn)題,不僅觀點(diǎn)鮮明、材料翔實(shí),而且兼顧反黑格爾主義者的聲音,可謂明辨是非而又不失公允。但在霍爾蓋特的論述背后,我們?nèi)杂斜匾岱缹?duì)黑格爾理論的簡(jiǎn)化與歪曲。為此,我們不妨回到文本本身,回到理論所生發(fā)的語(yǔ)境去發(fā)掘《邏輯學(xué)》的深刻內(nèi)涵,從而為霍爾蓋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補(bǔ)充。
一、無(wú)預(yù)設(shè)性之辯
在《邏輯學(xué)》的開(kāi)端,開(kāi)端本身成了一個(gè)問(wèn)題,這個(gè)問(wèn)題的核心在于:開(kāi)端有沒(méi)有前提?是間接的還是直接的?按照黑格爾的說(shuō)法,開(kāi)端“不以任何東西為前提,必須不以任何東西為中介,也沒(méi)有根據(jù)……因此,它必須直截了當(dāng)?shù)厥且粋€(gè)直接的東西,或者不如說(shuō),只是直接的東西本身”。〔1〕這就是說(shuō),開(kāi)端是沒(méi)有前提、沒(méi)有中介的開(kāi)端,它不依賴任何外在的、先驗(yàn)的假設(shè)而自我展開(kāi)。霍爾蓋特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diǎn),所以他在分析開(kāi)端問(wèn)題的時(shí)候就把這樣的“無(wú)預(yù)設(shè)性”(Presuppositionlessness)作為第一個(gè)關(guān)鍵詞。這一關(guān)鍵詞意味著“在哲學(xué)的開(kāi)端,任何特定的思維概念及其范疇都不是理所當(dāng)然的”,同時(shí)表明,“我們不能在一開(kāi)始就假定這些原則是明顯正確的并預(yù)先確定什么是合理的”。〔2〕因此,當(dāng)我們把思維本身作為考察對(duì)象的時(shí)候,我們要質(zhì)疑那些已經(jīng)成為思維定式的思維假設(shè)是否正確,更要反思這些假設(shè)是不是思維本身所固有的。從無(wú)預(yù)設(shè)性的角度來(lái)說(shuō),哲學(xué)的開(kāi)端便是它自身,是“a=a”的形式,是單純的直接性。這樣的直接性不包含任何內(nèi)容,因?yàn)椤皟?nèi)容之類(lèi)的東西會(huì)是與不同之物的區(qū)別和相互關(guān)系,從而就會(huì)是一種中介。所以,開(kāi)端就是純有”。〔3〕在黑格爾那里,內(nèi)容代表著一種規(guī)定性,代表著事物自身區(qū)別于其他事物、不與其他事物發(fā)生關(guān)系的屬性,這便是否定的規(guī)定性、一種外在的關(guān)系。所以,開(kāi)端就是要去除這樣的規(guī)定性、外在性而成為“純有”(Pure Being),在無(wú)預(yù)設(shè)的純粹性中,純有自我展開(kāi)。霍爾蓋特認(rèn)為,黑格爾的開(kāi)端是自由的,它“懸置了對(duì)自身的所有預(yù)設(shè),進(jìn)而只剩下它自己的簡(jiǎn)單的有”。〔4〕這種簡(jiǎn)單的“有”要求思維在其內(nèi)部自我批判、自我反思。故此,霍爾蓋特將黑格爾的“純有”比作笛卡爾的“普遍懷疑”,只不過(guò),黑格爾的結(jié)論并非“我思故我在”,而是“在思維中存在”(Thinking, therefore is)。〔5〕
霍爾蓋特對(duì)開(kāi)端的解讀固然是正確的,但是在他清晰的表述背后,更多深層內(nèi)涵沒(méi)有得到關(guān)注與闡發(fā)。首先是“無(wú)預(yù)設(shè)性”以及它和黑格爾整個(gè)哲學(xué)體系之間的關(guān)系。在《必須用什么作科學(xué)的開(kāi)端》中,黑格爾明確表示:“精神現(xiàn)象學(xué)是意識(shí)的科學(xué),是關(guān)于意識(shí)的表述,而意識(shí)所達(dá)到的結(jié)果則是科學(xué)的概念”。〔6〕所以說(shuō),《精神現(xiàn)象學(xué)》應(yīng)當(dāng)作為《邏輯學(xué)》開(kāi)端的開(kāi)端來(lái)閱讀,它是“純有”之為開(kāi)端的前提,也是思維經(jīng)過(guò)漫長(zhǎng)的發(fā)展過(guò)程進(jìn)入邏輯學(xué)階段的重要指引。張世英先生就把《精神現(xiàn)象學(xué)》視為黑格爾思想的“前導(dǎo)”,他認(rèn)為此書(shū)描述了“人的具體意識(shí)由低級(jí)的感性認(rèn)識(shí)一步一步到達(dá)‘絕對(duì)知識(shí)’(即概念)的漫長(zhǎng)過(guò)程”,而《邏輯學(xué)》奠基于這樣的概念,描述的是“概念本身推移轉(zhuǎn)化的過(guò)程”。〔7〕因此,《邏輯學(xué)》發(fā)端于《精神現(xiàn)象學(xué)》的結(jié)論之中,它們是密不可分的。此外,從《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到《邏輯學(xué)》,意識(shí)、思維都處于發(fā)展中的某個(gè)環(huán)節(jié),只有發(fā)展到最后才會(huì)對(duì)自己有完整的意識(shí),所以黑格爾式真理是往返運(yùn)動(dòng)的整體,任何的開(kāi)端只是暫時(shí)的某個(gè)環(huán)節(jié)的開(kāi)端。在文本中,黑格爾常用“圓圈”的形象來(lái)比喻科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科學(xué)的整體本身是一個(gè)圓圈,在這個(gè)圓圈中,最初的也將是最后的東西,最后的也將是最初的東西。”〔8〕換言之,科學(xué)發(fā)展是一環(huán)套一環(huán)、大圓套小圓的循環(huán)過(guò)程,唯有從整個(gè)發(fā)展歷程的角度來(lái)看,開(kāi)端才是其中的某個(gè)環(huán)節(jié),但如果就開(kāi)端而論開(kāi)端,它其實(shí)是不存在的。這樣的開(kāi)端是“后思”的開(kāi)端,即在終結(jié)之時(shí)回溯到根據(jù)的開(kāi)端,它既是開(kāi)端又是終結(jié),既推進(jìn)后續(xù)范疇的發(fā)展又“回溯到根據(jù),回溯到原始和真正的東西”。〔9〕所以,科學(xué)始終處于開(kāi)端與終結(jié)的循環(huán)往復(fù)之中,唯有通過(guò)這種循環(huán),思維的純粹性才會(huì)逐漸澄明。在這個(gè)意義上,開(kāi)端只有從科學(xué)發(fā)展的整體性來(lái)看,只有被視為環(huán)節(jié)中的一環(huán)才能自我顯現(xiàn)。
此外,霍爾蓋特在第二章中片面地強(qiáng)調(diào)了開(kāi)端的“無(wú)預(yù)設(shè)性”,卻沒(méi)有意識(shí)到這樣的“無(wú)預(yù)設(shè)性”本身也帶有“預(yù)設(shè)性”。一方面,黑格爾強(qiáng)調(diào)開(kāi)端的無(wú)中介性、無(wú)規(guī)定性;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認(rèn)開(kāi)端只有在被規(guī)定的情況下才會(huì)使后續(xù)的諸多范疇向前發(fā)展:“從開(kāi)端而前進(jìn),應(yīng)當(dāng)看作只不過(guò)是開(kāi)端的進(jìn)一步規(guī)定,所以開(kāi)端的東西仍然是一切后繼者的基礎(chǔ)。”〔10〕在此,開(kāi)端雖然將自身表現(xiàn)為純?nèi)粺o(wú)規(guī)定、無(wú)中介的“有”,但是這種無(wú)規(guī)定性只有和規(guī)定性結(jié)合在一起的時(shí)候才能引發(fā)自身的發(fā)展。所以說(shuō),無(wú)規(guī)定性中同時(shí)蘊(yùn)含了規(guī)定性,或者也可以說(shuō),無(wú)規(guī)定性本身就是一種規(guī)定性。正如鄧曉芒所認(rèn)為的,黑格爾所謂的“無(wú)規(guī)定性”實(shí)際上“已經(jīng)對(duì)‘有’作了一種規(guī)定……把這個(gè)‘沒(méi)有任何進(jìn)一步規(guī)定’當(dāng)作了‘有’的外在限制”。〔11〕因此,“無(wú)規(guī)定性”其實(shí)是一種特殊的規(guī)定,它揭示了開(kāi)端作為肯定與否定的一體兩面。從肯定的一面講,開(kāi)端是對(duì)直接性的肯定,它意味著思維是自我發(fā)展而沒(méi)有先驗(yàn)預(yù)設(shè)的;而從否定的一面講,開(kāi)端就是一種間接性、中介性的規(guī)定,它意味著開(kāi)端只有通過(guò)規(guī)定才體現(xiàn)為無(wú)規(guī)定,只有通過(guò)遮蔽才能自我呈現(xiàn)。在這個(gè)意義上,開(kāi)端既是肯定的否定又是否定的肯定,當(dāng)我們?cè)谘哉f(shuō)、反思開(kāi)端的時(shí)候,它已經(jīng)被我們所規(guī)定,而這種規(guī)定又要求開(kāi)端是無(wú)規(guī)定的。故此,黑格爾認(rèn)為“純有”只有“進(jìn)入思維的知和這種知的表述中,才能加以考慮”,通過(guò)表述、中介,開(kāi)端“只能是一個(gè)最初的、直接的、單純的規(guī)定”。〔12〕所以說(shuō),在科學(xué)的開(kāi)端之處,“有”既是無(wú)規(guī)定的又是有規(guī)定的,既是直接的又是間接的。雖然霍爾蓋特在第三章中補(bǔ)充論述了思維的預(yù)設(shè)性,但當(dāng)他在開(kāi)端之處強(qiáng)調(diào)無(wú)預(yù)設(shè)性的同時(shí),其對(duì)立面也應(yīng)該得到相應(yīng)的評(píng)述。
二、揚(yáng)棄之辯
闡述了開(kāi)端的無(wú)預(yù)設(shè)性之后,霍爾蓋特順?biāo)浦鄣靥岢隽朔椒ㄕ摰臒o(wú)預(yù)設(shè)性。按照開(kāi)端的特征,黑格爾在《邏輯學(xué)》中的范疇推演也應(yīng)當(dāng)是無(wú)預(yù)設(shè)、任其自由展開(kāi)的。但是在某些批評(píng)家看來(lái),黑格爾明顯是以辯證法的方式敘述范疇的發(fā)展的,這種方式“探討一個(gè)范疇如何推進(jìn)、如何超越或包含它的對(duì)立面、如何與對(duì)立面統(tǒng)一而合成第三個(gè)范疇”。〔13〕固然,辯證法的思維模式一直被人們視為黑格爾的標(biāo)志性方法論,但是霍爾蓋特認(rèn)為,黑格爾在《邏輯學(xué)》中并沒(méi)有如此明確的方法論意識(shí),因?yàn)椴还苁情_(kāi)端還是范疇的演進(jìn),黑格爾始終追求一種無(wú)規(guī)定的純粹性,這種純粹性“不能被任何演算、規(guī)則、三段論、發(fā)現(xiàn)的邏輯、語(yǔ)義分析或意向性的教條指導(dǎo)或規(guī)定”。〔14〕所以,并不是說(shuō)黑格爾有意識(shí)地將辯證法“應(yīng)用”于范疇的推演之中,而是“無(wú)規(guī)定的有的概念,經(jīng)過(guò)進(jìn)一步考察被證明是辯證的”。〔15〕“應(yīng)用”代表了方法論工具的外在性,而在《邏輯學(xué)》的內(nèi)在發(fā)展空間中,外在性正是黑格爾所要杜絕的。霍爾蓋特認(rèn)同威廉·梅克(William Maker)的說(shuō)法:“只要一個(gè)人在傳統(tǒng)哲學(xué)意義上使用‘方法’一詞,這就意味著這套規(guī)則是先于特定內(nèi)容的。”〔16〕所以,從純粹性、無(wú)預(yù)設(shè)性的角度來(lái)看,黑格爾沒(méi)有外在的方法。但是霍爾蓋特同時(shí)指出,這并不是說(shuō)黑格爾“應(yīng)當(dāng)在《邏輯學(xué)》中放棄任何方法”,而是說(shuō)這種方法“只能用在考察無(wú)規(guī)定性本身”。〔17〕所以,霍爾蓋特承認(rèn)黑格爾的方法應(yīng)當(dāng)是內(nèi)在的方法。
為強(qiáng)調(diào)黑格爾方法論的內(nèi)在性,霍爾蓋特特意批判了邁克爾·福斯特(Michael Forster)對(duì)黑格爾的評(píng)價(jià)。福斯特堅(jiān)定地認(rèn)為黑格爾在范疇的推演過(guò)程中“設(shè)計(jì)了某種一般的哲學(xué)方法”,這種方法表明“范疇A包含了一個(gè)相反的范疇B”,而通過(guò)一個(gè)新的范疇C,“范疇A和B統(tǒng)一起來(lái)”。〔18〕但是,福斯特同時(shí)指出,《邏輯學(xué)》中的黑格爾或多或少地“背離”了這種方法,因?yàn)樵凇白儭保˙ecoming) 向“實(shí) 有”(Determinate Being)的轉(zhuǎn)換過(guò)程中,黑格爾“沒(méi)有展示‘變’這個(gè)范疇如何與它矛盾的范疇雙向蘊(yùn)含,也沒(méi)有展示它們?nèi)绾谓y(tǒng)一為‘實(shí)有’,而是嘗試在‘變’中找到兩個(gè)相互矛盾的組成部分,然后論證這兩個(gè)部分統(tǒng)一在了‘實(shí)有’之中”。〔19〕很不幸的是,霍爾蓋特尖銳地指出福斯特的評(píng)價(jià)是完全不合理的,他將福斯特歸為那類(lèi)“堅(jiān)持批判哲學(xué)傳統(tǒng)”的學(xué)者,認(rèn)為反倒是這類(lèi)學(xué)者在批判黑格爾之前業(yè)已假設(shè)了某種先驗(yàn)方法論和一以貫之的總體性方法。換言之,福斯特這類(lèi)學(xué)者對(duì)黑格爾的解讀是抱有“前理解”的,當(dāng)他們發(fā)現(xiàn)黑格爾的矛盾之處時(shí),這種“背離”的矛盾性恰好驗(yàn)證了他們批判方法中的預(yù)設(shè)性。所以,霍爾蓋特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說(shuō),黑格爾表面上的辯證法“僅僅是因?yàn)樵诟拍畹囊龑?dǎo)下思維必須成為辯證的思維,而不是因?yàn)檗q證法被預(yù)先假定為一種‘更高’的思維方式”。〔20〕故此,辯證法內(nèi)在于思維范疇,它是概念自身發(fā)展的方式,絕非外在附加的推演方式。
從結(jié)論來(lái)看,霍爾蓋特對(duì)福斯特的批判和他所強(qiáng)調(diào)的無(wú)預(yù)設(shè)性思維相互契合,他的反駁也就因此而自圓其說(shuō)。但我們無(wú)法滿足的一點(diǎn)是,霍爾蓋特并沒(méi)有針?shù)h相對(duì)地解釋為何從“變”到“實(shí)有”的推進(jìn)不是方法論的“背離”,而是內(nèi)在于開(kāi)端的自我發(fā)展本身的規(guī)定性運(yùn)動(dòng)。在這個(gè)意義上,我們可以從“揚(yáng)棄”概念入手為霍爾蓋特做一個(gè)補(bǔ)充式的辯護(hù)。
在《邏輯學(xué)》中,黑格爾對(duì)“變”和“實(shí)有”的關(guān)系有過(guò)明確的表述:“實(shí)有從變發(fā)生。實(shí)有是有與無(wú)單純地合而為一。實(shí)有由于這種單純性而有了一個(gè)直接物的形式。它的中介,即變,已被留在它的后面;中介揚(yáng)棄了自身,因此,實(shí)有便好像是最初的、可以作開(kāi)始的東西。”〔21〕這句話首先強(qiáng)調(diào)了黑格爾的開(kāi)端是個(gè)雙重的開(kāi)端(既是有,又是無(wú)),因?yàn)楫?dāng)我們把“純有”作為開(kāi)端的時(shí)候,我們強(qiáng)調(diào)的只是它對(duì)自身的肯定的一面,而如果從它對(duì)自身的否定的一面來(lái)看,開(kāi)端又是“無(wú)”(Nothing)。所以,開(kāi)端在自我揭示(作為有)的時(shí)候又有所遮蔽(作為無(wú)),既是無(wú)中介的呈現(xiàn)又是中介化的規(guī)定。此外,這句話還表明,有與無(wú)統(tǒng)一為變(不穩(wěn)定狀態(tài)),變又推出為實(shí)有,只不過(guò)當(dāng)我們把實(shí)有視為有與無(wú)的單純的、直接的結(jié)合的時(shí)候,變的中介性被揚(yáng)棄了。換言之,當(dāng)變(作為中介)過(guò)渡到實(shí)有的時(shí)候,它自身又被規(guī)定為一個(gè)靜止的東西,從而把自己“揚(yáng)棄”了,這就使得“實(shí)有”直接折射出有與無(wú)的單純性。在黑格爾的文本中,“揚(yáng)棄”始終是個(gè)關(guān)鍵概念,它并不是福斯特所認(rèn)為的簡(jiǎn)單的“統(tǒng)一”,而是一種超越式的保存。在《邏輯學(xué)》中,黑格爾認(rèn)為揚(yáng)棄“意謂保存、保持,又意謂停止、終結(jié)。保存自身已包括否定,因?yàn)橐3制湮铮晚毴サ羲闹苯有裕瑥亩毴サ羲目梢允芡鈦?lái)影響的實(shí)有”。〔22〕姜丕之對(duì)這一段作出了清晰的解釋,即“保存就意味著要去掉原有的直接性(或獨(dú)立性)……被揚(yáng)棄的東西并不因此而成為無(wú),而是在新的東西中有所保存”。〔23〕所以說(shuō),揚(yáng)棄并不是消滅舊的、推出新的,也不是用一個(gè)更新的范疇來(lái)統(tǒng)一兩個(gè)彼此矛盾的范疇,而是對(duì)于“有”之直接性的否定,是一種“非有”、一種“否定之否定”。在這個(gè)意義上,被揚(yáng)棄意味著被保留,只不過(guò)是被中介化地保留,被揚(yáng)棄之物會(huì)在新的范疇中獲得自身演進(jìn)的必然性。這樣的揚(yáng)棄表明,福斯特對(duì)于辯證法的預(yù)設(shè)是片面的,他將揚(yáng)棄的作用簡(jiǎn)化為“統(tǒng)一”而忽略了它的保留之義。事實(shí)上,正是在揚(yáng)棄的保留作用之中,變(作為一個(gè)中介)揚(yáng)棄了自身,同時(shí)保留了有的形態(tài)與無(wú)的內(nèi)涵,進(jìn)而統(tǒng)一為實(shí)有。相反,福斯特把變?cè)O(shè)想為一個(gè)穩(wěn)固的范疇,把揚(yáng)棄理解為“統(tǒng)一”,進(jìn)而導(dǎo)致他僵化地批評(píng)黑格爾沒(méi)有為變找到矛盾的范疇以展現(xiàn)它如何統(tǒng)一為實(shí)有。所以說(shuō),這種理解上的偏差和簡(jiǎn)化才是導(dǎo)致誤讀的罪魁禍?zhǔn)祝@些都是霍爾蓋特在反駁福斯特的時(shí)候沒(méi)有來(lái)得及澄清的。
三、內(nèi)在性之辯
既然黑格爾的《邏輯學(xué)》沒(méi)有先行預(yù)設(shè)的開(kāi)端,也沒(méi)有外在的、一以貫之的方法論,那么,我們要以怎樣的立場(chǎng)去評(píng)價(jià)《邏輯學(xué)》?或者說(shuō),如何公允地評(píng)價(jià)黑格爾的內(nèi)在體系?這些問(wèn)題呼之欲出。
霍爾蓋特首先明確,黑格爾拒絕所有的“外在批評(píng)”,他認(rèn)為這些批評(píng)是“基于形式邏輯或批判傳統(tǒng)而提出的”,因而“無(wú)法展示無(wú)預(yù)設(shè)性思維自身的發(fā)展”。〔24〕但是,黑格爾對(duì)于外在性的拒絕也被許多當(dāng)代哲學(xué)家視為他對(duì)“內(nèi)在思維”的先行預(yù)設(shè),例如邁克爾·羅森(Michael Rosen)就認(rèn)為黑格爾“預(yù)先假定了某種規(guī)定的否定”,哈貝馬斯聲稱黑格爾“已經(jīng)準(zhǔn)確地預(yù)設(shè)了絕對(duì)的知”,〔25〕德里達(dá)堅(jiān)信黑格爾的揚(yáng)棄始終局限于話語(yǔ)內(nèi)部,因而難免帶有規(guī)定性與限制性。在霍爾蓋特看來(lái),羅森等人的批評(píng)是錯(cuò)誤的,因?yàn)樵谒麄兣泻诟駹柌蛔杂X(jué)地預(yù)設(shè)了內(nèi)在性的時(shí)候,他們自己就是有所預(yù)設(shè)地去批評(píng)黑格爾的。霍爾蓋特認(rèn)為,黑格爾的思維體系是徹底自我批判的,而任何反對(duì)這種體系的思維都“源于一種比無(wú)預(yù)設(shè)性思維本身更缺乏自我批判、更教條的思維”。〔26〕所以說(shuō),批判者之所以會(huì)認(rèn)為黑格爾預(yù)設(shè)了這樣的內(nèi)在性,這恰恰是因?yàn)樗麄冏约喊堰@種預(yù)設(shè)強(qiáng)加在了黑格爾身上,而非黑格爾刻意為之。換言之,外在批評(píng)是教條的,它本身就是黑格爾所要批判的對(duì)象,現(xiàn)在反而成為人們批判黑格爾的理由,這是不合理的。無(wú)獨(dú)有偶,與黑格爾同時(shí)代的理論家也對(duì)他的內(nèi)在思維作出過(guò)同樣的批評(píng),而在《邏輯學(xué)》中,黑格爾自己回應(yīng)了這些批評(píng),他認(rèn)為批評(píng)者“不能夠作單純的思考”,“他們的攻擊和責(zé)難所包含的范疇,往往只是些假定”,他甚至用“顢頇無(wú)知”〔27〕來(lái)形容這些批評(píng)。可見(jiàn),批判一種哲學(xué)的根本任務(wù)是在不加預(yù)設(shè)的基礎(chǔ)上發(fā)現(xiàn)這套哲學(xué)是如何構(gòu)思自身的,而不是抱有思維預(yù)設(shè)進(jìn)而假定什么是正確的。因此,霍爾蓋特認(rèn)為,對(duì)于黑格爾的批判需要一種完全開(kāi)放的思維,它在開(kāi)放的同時(shí)尊重思維的內(nèi)在性并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數(shù)黑格爾的批評(píng)者仍舊秉持著預(yù)設(shè)性思維,這種思維屬于“前黑格爾哲學(xué)”,〔28〕故而被排除在現(xiàn)代哲學(xué)所要求的自我反思之外。當(dāng)然,這也不是說(shuō)黑格爾的思維體系完全超越了所有的批評(píng)而陷入了價(jià)值相對(duì)主義的境地。霍爾蓋特同時(shí)也承認(rèn),黑格爾仍然“容易受到來(lái)自無(wú)預(yù)設(shè)性思維本身的批評(píng),即內(nèi)在批評(píng)”。〔29〕這種內(nèi)在批評(píng)并不要求批評(píng)者有特殊的直覺(jué)或洞察力,而是理解一個(gè)范疇的內(nèi)涵并發(fā)現(xiàn)其中包含什么即可。換言之,重要的是理解而非批判,黑格爾認(rèn)為這是每個(gè)具有理性的人都能擁有的能力,并非少數(shù)人的特權(quán)。所以說(shuō),黑格爾所接受的內(nèi)在批評(píng)要求我們“跟隨每一范疇內(nèi)在的東西一起前進(jìn)”,〔30〕進(jìn)而確保它們嚴(yán)格遵守?zé)o預(yù)設(shè)性的思維。這既是一種德意志式的傲慢,也是一種對(duì)于他者的邀約,唯有在黑格爾思維體系內(nèi)在的根據(jù)之中,我們才有可能與之照面。
霍爾蓋特的論述無(wú)疑是中肯而又準(zhǔn)確的,他對(duì)內(nèi)在批評(píng)的闡發(fā)也與之前對(duì)于開(kāi)端和方法論的無(wú)預(yù)設(shè)性論述一脈相承。其實(shí),不管是方法論的內(nèi)在性還是批評(píng)的內(nèi)在性,都折射出了黑格爾對(duì)內(nèi)在性與純粹性的追求。這種追求同樣也體現(xiàn)在某物的“自在之有”中,通過(guò)這種自在之有,我們或許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邏輯學(xué)》體系的內(nèi)在價(jià)值。
在黑格爾看來(lái),有發(fā)展到實(shí)有之后仍未呈現(xiàn)為具體的某物,因?yàn)閷?shí)有僅僅是內(nèi)容的“標(biāo)識(shí)”,就像一個(gè)容器中的容積一樣,并不等同于容器本身。這種非具體的抽象性表明,實(shí)有只是一種“空有”,它不是具體事物,也不具有自身和他物的區(qū)別性特征。但是,為了讓實(shí)有進(jìn)一步發(fā)展為某物,實(shí)有必須具有內(nèi)在的規(guī)定性、一種否定,唯有如此,它才能被內(nèi)容所充實(shí),成為具體的事物。這一規(guī)定性的否定,便是“質(zhì)”。這個(gè)質(zhì)包含在實(shí)有自身之中,正如黑格爾所認(rèn)為的,“質(zhì)不與實(shí)有分離,實(shí)有只是規(guī)定了的、質(zhì)的有”。〔31〕故此,實(shí)有和質(zhì)(否定)處于糾纏之中,而當(dāng)實(shí)有再次強(qiáng)調(diào)自己肯定的一面,實(shí)有就否定了質(zhì),走出了抽象的共相,從而成為某物。在此,質(zhì)的揚(yáng)棄被黑格爾稱為“第一個(gè)否定之否定”,〔32〕實(shí)有不再像開(kāi)端那樣沒(méi)有區(qū)別,而是在揚(yáng)棄之后保留了區(qū)別,重新與自身同一。所以說(shuō),“實(shí)有的單純性由于這種揚(yáng)棄而有了中介”。〔33〕某物作為否定之否定以自身為中介,這樣的自我中介便昭示著某物的自我關(guān)系。黑格爾認(rèn)為,自我關(guān)系對(duì)某物來(lái)說(shuō)是極為重要的,因?yàn)槟澄锸紫取爸皇窃谧陨黻P(guān)系中單純地保持自身”,〔34〕之后才和它的對(duì)立物(他物)產(chǎn)生外在的關(guān)系。換言之,某物與他物的關(guān)系首先是某物的自我關(guān)系,某物“在他物中只不過(guò)是與自身融合為一罷了”。〔35〕因此,某物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先于它的外在關(guān)系,而且這種內(nèi)在的自我關(guān)系需要從他物的視角進(jìn)行一次回返式的“顛倒”才能確立自身。在此基礎(chǔ)上,黑格爾進(jìn)一步為某物細(xì)分出“為他之有”和“自在之有”的兩個(gè)環(huán)節(jié)。當(dāng)實(shí)有經(jīng)過(guò)質(zhì)的揚(yáng)棄發(fā)展為某物的時(shí)候,他有“既同時(shí)被包括在某物之內(nèi),又同時(shí)與某物分離”,這種實(shí)有自身的相異性揭示了某物與自身的間接關(guān)系,這樣的有就是“為他之有”;而“自在之有”則是“作為與對(duì)他物的關(guān)系相對(duì)立的自身關(guān)系”,它在“非實(shí)有中仍舊保持了自己”,〔36〕這是某物與自身的直接關(guān)系。因此,某物的自在之有相比于為他之有更加澄明、更加直接,這種澄明而直接的狀態(tài)便是黑格爾在開(kāi)端之處就想達(dá)到的無(wú)預(yù)設(shè)性,也是意識(shí)在自身之中尋找自身的“真無(wú)限”模式。當(dāng)然,黑格爾同時(shí)提醒我們不能把某物僅僅視為自在的東西,因?yàn)檫@樣的假設(shè)會(huì)在純粹直接性的預(yù)設(shè)中遮蔽中介的存在,從而落入抽象而外在的規(guī)定之中。所以,自在之有只是某物的肯定的一面,它始終和為他之有(作為否定的一面)相互糾纏,唯有如此才能成為真實(shí)的某物。可見(jiàn),黑格爾并沒(méi)有片面地強(qiáng)調(diào)某物的內(nèi)在性與純粹性,而是始終對(duì)它保持警覺(jué),并試圖在直接的自我關(guān)系背后發(fā)掘出中介的痕跡和揚(yáng)棄的痕跡,最終避免內(nèi)在性成為某種新的外在規(guī)定。由此反觀霍爾蓋特的導(dǎo)論我們便會(huì)發(fā)現(xiàn),在他反對(duì)外在批評(píng)而一味強(qiáng)調(diào)內(nèi)在批評(píng)的同時(shí),自我關(guān)系的深刻內(nèi)涵便在無(wú)形之中被遮蔽了。
四、結(jié)語(yǔ)
在霍爾蓋特看來(lái),黑格爾《邏輯學(xué)》的開(kāi)端是無(wú)預(yù)設(shè)性的“純有”,這種無(wú)預(yù)設(shè)性表明,黑格爾沒(méi)有自覺(jué)地使用任何外在的、現(xiàn)成的方法論,而是任由概念自我發(fā)展、自行推進(jìn)。此外,內(nèi)在的視角決定了我們不能用外在的標(biāo)準(zhǔn)批評(píng)黑格爾的哲學(xué)體系,因?yàn)槿魏蔚耐庠谂u(píng)都不是自我批判,它們錯(cuò)失了黑格爾《邏輯學(xué)》的精粹。無(wú)疑,霍爾蓋特的論述對(duì)我們理解《邏輯學(xué)》具有重要的啟發(fā)價(jià)值,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那清晰的論述遮蔽了黑格爾思想中更為深刻的內(nèi)涵。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他將“純有”作為無(wú)預(yù)設(shè)性之開(kāi)端的時(shí)候淡化了《精神現(xiàn)象學(xué)》的前導(dǎo)作用以及“無(wú)預(yù)設(shè)性”自身的“預(yù)設(shè)性”;他在批評(píng)邁克爾·福斯特對(duì)黑格爾的質(zhì)疑時(shí)沒(méi)有切中對(duì)方的要害,錯(cuò)失了重點(diǎn),而當(dāng)我們從“揚(yáng)棄”(作為一種保留)的視角來(lái)看待福斯特的問(wèn)題的,錯(cuò)誤便昭然若揭了。此外,霍爾蓋特對(duì)內(nèi)在批評(píng)的強(qiáng)調(diào)也可以從某物的“自在之有”與“為他之有”那里得到印證,自我關(guān)系的優(yōu)先性體現(xiàn)了內(nèi)在批評(píng)所強(qiáng)調(diào)的自我批判,彰顯了黑格爾對(duì)于純粹性與自明性的追求。當(dāng)然,霍爾蓋特的解讀最終還是瑕不掩瑜的,正如我們?cè)诤诟駹柕摹哆壿媽W(xué)》中所看到的,優(yōu)秀的文本總會(huì)將自己開(kāi)放給讀者,召喚多元的解讀與勇敢的質(zhì)疑。或許在霍爾蓋特那里,帶領(lǐng)讀者走入黑格爾的文本語(yǔ)境并能獲得啟發(fā),導(dǎo)讀的任務(wù)便可稱得上功德圓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