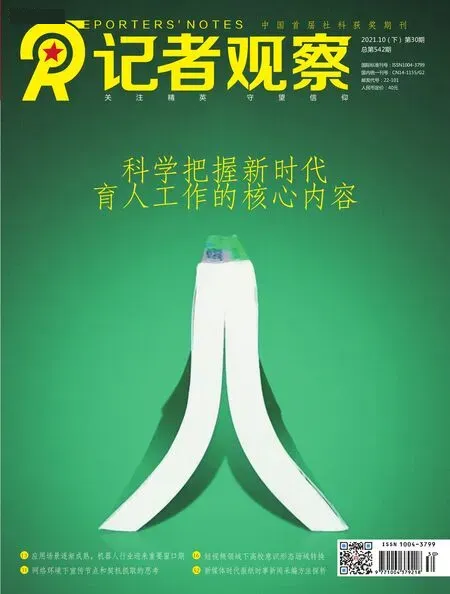電視新聞記者在微博和微信中的新聞專業(yè)把關行為探究
——基于內容分析和半結構化訪談
文 劉宇昕 Anais Auge
社交媒體改變了傳統(tǒng)記者的新聞接收方式,并且對日常新聞生產過程中的傳遞和選取行為模式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本研究著力探討電視記者在使用個人微博和微信賬號進行新聞實踐中的“把關”行為在“輸出”和“輸入”階段的轉換,以及記者如何堅持“把關”行為以在個人社交媒體賬號和傳統(tǒng)電視媒體節(jié)目中實現(xiàn)新聞職業(yè)行為的延伸。本項研究對新聞記者個人微博、微信賬號進行了內容分析,結合半結構化訪談分析法,揭示了微博和微信對電視新聞記者的不同用途,并闡釋了微博和微信是記者在進行新聞把關時分享信息、搜索新聞素材和檢查事實的有效工具。電視新聞記者在個人賬號上的不同表現(xiàn),表明他們無論在線上線下均扮演著新聞信息傳遞者、收集者和驗證者的角色。他們不斷完善自己對社交媒體的使用行為,以適應和符合傳統(tǒng)的新聞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同時,他們也持續(xù)調整這些行為規(guī)范以適應社交媒體平臺的運營邏輯。本研究將探索比較記者在微博和微信中不同的新聞專業(yè)實踐活動,全面反映記者對社交媒體的不同使用方式,以及在社交媒體把關過程中呈現(xiàn)出的不同角色,這將有助于補充和拓展關于新聞把關中的記者行為規(guī)范的實證分析研究。
“把關”理論是新聞研究領域中文獻記載最多的理論之一,它與記者的個人偏好和集體職業(yè)價值觀有關。“把關”理論強調傳播者在新聞傳遞過程中負責搜集、整理、篩選、處理、加工與傳播信息。因此記者被稱為“把關人”,而他們的行為被稱為“把關”。如今,新的通訊技術和社交媒體改變了人們接收新聞的方式。記者自身的新聞實踐活動通過新興社交媒體上的個人賬戶加以拓展,這改變了信息在線的“把關”過程,以及觀眾接收高度交互式信息的方式。在中國,關于偏離和保持“把關人”的角色話題一直存在爭議。這有助于新聞研究的去西方化,并有助于解釋社交媒體賬戶中新聞“把關”活動與社會背景之間的相互作用。本文通過探索中國電視新聞記者對社交媒體的使用情況,旨在揭示記者在微博和微信個人賬號中的新聞“把關”實踐活動的變化,并探討記者在社交媒體中“把關”行為的延伸。
文獻綜述
從20世紀開始,新聞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和實踐活動被廣泛研究。盡管不同的國家有其特定的新聞規(guī)范,不同類型的媒體以及不同的媒介體制都會或多或少地援引相同的思想價值體系和新聞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其規(guī)范都會反映在記者的日常工作中。記者將自己視為“把關人”,來選擇他們需要的社會中重要的信息。他們行使著獨有的特權:決定著信息的可發(fā)性和擴散性。懷特首先將把關概念應用到新聞領域。之后,休梅克等學者在2010年的文獻中指出“門先生”會根據(jù)他們個人的信仰,以及個人的知識體系和習慣來選擇新聞素材,故他們會經(jīng)常核查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和平衡性。
華萊士在2018年的文章中重新建立了一套在線信息流把關模型。他認為記者、個人、算法和新聞機構都嵌入到了網(wǎng)絡把關的演變中,他將把關劃分為三個階段:信息獲取階段(信息輸入)、選擇信息階段(信息生產)以及信息發(fā)布階段(信息輸出)。本研究正是建立在這種新型把關模式的基礎之上。
社交媒體改變了傳統(tǒng)新聞業(yè)的面貌:它提高了信息傳播的速度,同時也提供了共享信息的開放平臺。社交媒體成為了記者工作中的一部分。大部分記者使用社交媒體搜尋新聞素材或者追蹤社會事件。因此社交媒體的海量信息有助于記者發(fā)現(xiàn)新聞線索和挖掘新聞事實。一種新的新聞形式由于集體協(xié)作環(huán)境模式而形成,將社交媒體和記者的實踐活動聯(lián)系起來。在這種集體環(huán)境中,記者可以運用群眾的智慧從他們通常無法找到或接觸到的平臺來源快速收集信息。因此,互動性被認為是社交媒體的一大特色,因其推進了記者與受眾之間的直接對話。
對于傳統(tǒng)的新聞業(yè)來說,互聯(lián)網(wǎng)的出現(xiàn)既是挑戰(zhàn)也是機遇。受眾的參與以及網(wǎng)絡自身的開放性和及時性,改變了記者的傳統(tǒng)角色及其職業(yè)規(guī)范。由于網(wǎng)絡信息的海量和受眾發(fā)布信息的自主性增大,記者在網(wǎng)絡中無法像傳統(tǒng)媒體一樣決定受眾閱讀的內容,因此,傳統(tǒng)記者在網(wǎng)絡中的角色由“把關人”轉變?yōu)椤笆亻T人”。
網(wǎng)絡上的信息魚龍混雜,需要記者擁有更強的新聞專業(yè)素養(yǎng)來辨識有價值的信息。另外,受眾在一定程度上更喜歡閱讀專業(yè)新聞媒體的信息,并信任擁有專業(yè)技能的傳統(tǒng)記者。因此,他們把關的力度會增強而不是減弱。

電視記者在微博中的信息轉發(fā)活動表1

電視記者在微信中的信息轉發(fā)活動表2

微博中信息轉發(fā)的來源表3
辛格認為社交媒體延伸了記者“把關人”的角色。由于網(wǎng)絡新聞的協(xié)作和交互式特征,收集和發(fā)布信息不再是記者的專屬。因此記者與受眾在社交媒體中“共享”了把關人的角色。記者規(guī)范他們在社交媒體中的行為來符合傳統(tǒng)的新聞職業(yè)道德要求,同時,他們也調整自己的行為來適應社交媒體不斷發(fā)展的大環(huán)境。社交媒體中的“把關”行為已經(jīng)從新聞的選擇擴展到了新聞的解讀、新聞的判斷和新聞的核實。
中國新聞研究應結合中國特有的新聞體系和情景進行展開。我們必須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一系列的思想意識形態(tài)予以高度重視,并將這些思想作為指導,融合在新聞實踐活動中。記者應提高對黨的忠誠度,且堅持群眾路線。在我國,微博和微信被電視記者廣泛使用。社會技術發(fā)展導致新聞范式的轉變。因此記者如何與受眾“共享”“把關”這一行為,以及“把關”在社交媒體中的演變仍沒有定論。因此,本研究主要對電視記者在工作過程中對微博和微信在輸出(新聞傳遞)和輸入(新聞選擇)階段的“把關”行為進行探究。
方法論:內容分析法與半結構式訪談法
本研究采用了定量和定性兩種研究方法。這種混合方法可以發(fā)揮兩種方法各自的優(yōu)勢,彌補單一方法的不足,保證研究結果的互補性和有效性。通過對微博和微信中記者個人賬戶信息的內容分析,可以了解中國電視新聞記者在社交媒體中的“把關”角色變化。為了進一步得到深入補充數(shù)據(jù),本項研究采用訪談法,對電視新聞記者和編輯進行了采訪,來揭示電視記者在社交媒體中傳遞和搜尋信息時,如何感知“把關”的角色轉變。由于通過記者社交媒體中的信息較難捕捉到記者對事物的深層次理解,因此本項研究采用半結構化的采訪方式,以便于進一步探討記者的看法,以及不同力量對記者行為規(guī)范的影響。
本項研究設計了一套編碼流程手冊,并選擇了從2019年7月1日至8月30日的全職電視新聞記者個人微博和微信賬號中的信息內容進行編碼。本項研究從微博的“名人堂”大型數(shù)據(jù)庫中隨機抽取了電視記者的賬號。最終,選擇了27個電視記者賬號的177個樣本進行系統(tǒng)抽樣,對每一個賬號中所有符合時間區(qū)間的動態(tài)信息,每5個抽取1個作為樣本,并采用隨機選擇的方式抽取第一條動態(tài)信息,最終從每個賬戶中選出了3至8條動態(tài)信息進行分析。由于微信隱私性較強,記者必須與研究者互為微信“好友”,且記者必須對研究者授予朋友圈查看權限,研究者才能看到記者的動態(tài)信息。因此,本項研究只能分析那些愿意開放朋友圈的25位電視記者的微信賬號。故本研究中的微信樣本數(shù)量小于微博樣本數(shù)量。通過系統(tǒng)抽樣,本項研究選擇了 123 條動態(tài)信息作為微信賬戶樣本。與微博的取樣相同,從每5條動態(tài)信息中抽取1條作為樣本。
最終,本研究從微博和微信中選擇了300條動態(tài)信息,并將所有樣本復制粘貼到word文檔中,建立了一個用于內容分析的編碼檔案。在研究中首先設立了主問題:記者所發(fā)布的動態(tài)信息是否轉載自他人,如果記者轉載了他人的動態(tài)信息,即證明記者與原動態(tài)信息的發(fā)出者共享了“把關人”這一角色。隨后又基于動態(tài)信息的轉發(fā)來源等不同變量設計了多項子問題。
本研究在獲得英國東英吉利大學倫理道德協(xié)會的批準以及記者的同意后,使用目的性抽樣和滾雪球式抽樣方法,選取了35名來自中國不同地區(qū)的全職電視新聞記者進行采訪。本次訪談采取匿名的形式,使用編號來代替受訪者的姓名和工作單位,從2018年1月持續(xù)至2019年1月,其中包括29次面對面采訪和6次遠程電話采訪。
研究結論分析:新聞“把關”實踐活動的演變與專業(yè)新聞“把關”活動中的社交媒體使用情況分析
新聞“把關”行為的轉變分析
研究結果表明,記者“把關人”的傳統(tǒng)角色仍然沒有受到挑戰(zhàn),他們很少在其個人賬戶上轉發(fā)公民記者和受眾的作品,也很少使用個人賬戶與受眾交流。數(shù)據(jù)顯示,在微博中有54.2%的帖子包含轉發(fā)內容,微信中有47.2%的帖子包含轉載內容(見表1和表2)。因此,可推斷記者個人賬戶中信息的轉載率較高。
雖然記者經(jīng)常從其他賬號轉載信息,但仍無法判斷他們是否與觀眾“分享”了“把關人”這一角色。如表3所示,在微博上的記者個人賬戶中,大多數(shù)轉載來自非主流媒體(如自媒體或網(wǎng)絡新聞網(wǎng)站,但非個人賬戶)、記者任職的新聞機構和其他專業(yè)記者的個人賬號分別占比36.5 %、19.8% 和15.6% 。在微信上的記者個人賬戶中,有43.1%的轉載信息來自國內新聞機構,36.2%和3.4%的轉載信息來自于非主流媒體機構和其他傳統(tǒng)專業(yè)記者(見表4)。 如表3和表4所示,很少有記者轉發(fā)受眾的信息,在微博上的記者個人賬戶中僅有6.3%的轉載信息來自于受眾,在微信中則僅有1.7%。這表明記者很少通過轉載信息與受眾互動交流,所以電視新聞記者的網(wǎng)絡“把關人”角色基本上保持不變。

微信中信息轉發(fā)的來源表4
采訪數(shù)據(jù)表明,大多數(shù)記者很少與受眾就新聞報道進行公開的交流。記者與受眾只在“私信”和“評論區(qū)”進行私下一對一的互動。他們在微博和微信中只與朋友、家人和同事交談,而不喜歡與陌生受眾交談。因此,研究表明記者和觀眾在微博和微信上的關系并不密切。
在微博中,記者會偶爾轉發(fā)來自受眾的內容,同時附加其自己的評論。由于技術設置原因,記者在微信中的新聞“把關”比在微博中的更加嚴格,在微信的個人賬號中,互動僅可發(fā)生在“評論區(qū)域”,受眾不能直接參與到新聞的發(fā)布環(huán)節(jié),他們只有在新聞發(fā)布后才能與記者討論新聞內容。
記者在個人賬戶中的信息輸出階段依然保持其傳統(tǒng)的“把關人”角色,他們不愿與觀眾互動或分享內部資料。但在某些情況下,其也會扮演普通用戶的角色。因此,記者的不同行為是受不同國家的既定慣例和特定社交媒體平臺的設置所影響的。
記者微博與微信個人賬戶的使用狀況以及“把關”行為的延伸現(xiàn)象分析
信息傳輸者角色的扮演
信息傳遞是記者在微博和微信個人賬號中履行“把關”行為的一項新聞實踐活動。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經(jīng)常轉載或改編來自其所任職的新聞單位和其他傳統(tǒng)主流媒體(例如報紙、通訊社和電視節(jié)目)的新聞信息。記者還偶爾轉發(fā)其他社交媒體用戶的信息。
記者使用微博和微信個人賬戶的方式有所不同。由于微信的隱私設置,記者可以將朋友劃分到不同的群組,這使得記者使用微信比使用微博時更加靈活。雖然微博的個人賬號也有“僅好友可見”功能,但是本研究卻發(fā)現(xiàn)記者很少提及和使用該功能。因此,與微博相比,微信同時滿足了記者的職業(yè)行為和個人行為,也可以說,微信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記者的職業(yè)行為和個人行為。
新聞信息采集者與核實者角色的扮演
電視記者在發(fā)布信息前(信息輸入階段)需要搜索新聞素材并驗證信息的準確性。微博和微信中所呈現(xiàn)的頻繁更新的新聞、網(wǎng)絡評論和直播視頻,已經(jīng)成為記者搜索信息的便捷渠道和有效來源。
微博是記者尋找新聞線索的重要渠道。獲取信息對記者來說至關重要,而由于微博具有公開性,記者可以很容易地閱覽每個用戶的主頁并通過微博個人賬號搜尋和驗證新聞線索。
微博個人賬戶可用于監(jiān)測趨勢、搜索可報道的新聞,它促進了記者與專家、名人以及同行的交流。微博沉浸式的環(huán)境有助于記者快速理解正在發(fā)生的事件并及時做出反應。但記者卻不常使用微信來搜集新聞。超過半數(shù)的記者表示,微信個人賬戶的隱私設置,制約了他們利用微信來搜索新聞資源,故他們不將微信作為其搜索新聞資源的工具。在微信中,由于信息可視范圍有限且信息流動較為緩慢,因此記者僅僅可以從他們的朋友或他們的微信忠實觀眾那里獲得資源,但這只是偶爾才會發(fā)生。
微博和微信是新聞線索的重要聚合器,但卻不是記者搜尋新聞線索的主要陣地。一般而言,記者經(jīng)常從相關政府或行業(yè)部門獲取新聞消息。電視臺的記者一般有著不同的分工,不同的記者負責采編報道不同類型的新聞,因此其一般與這些相應部門中為其提供消息來源的人保持著良好的關系,而熱線則是記者獲取信息的另一種重要方式。
本研究的重點是電視新聞記者的網(wǎng)絡“把關”過程和新聞實踐的規(guī)范化,揭示了記者在微博和微信個人賬戶中發(fā)揮“把關”作用的異同,有助于相關領域研究人員理解微博和微信個人賬號中“把關”行為的發(fā)展變化。
本研究對媒體格局和社交媒體上的新聞實踐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微博和微信對于電視記者來說是非常有用的工具,為他們提供了傳播信息、搜索消息來源和核實事實的前所未有的機會。微博和微信個人賬號也促使記者重新規(guī)范他們的職業(yè)行為。記者不僅在社交媒體中規(guī)范自己的職業(yè)行為,同時也在不斷調整自己的新聞行為以適應社交媒體的規(guī)范。微博和微信個人賬號是衍生平臺,促使記者在社交媒體上 更好地扮演新聞傳播者、采集者和核實者——“把關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