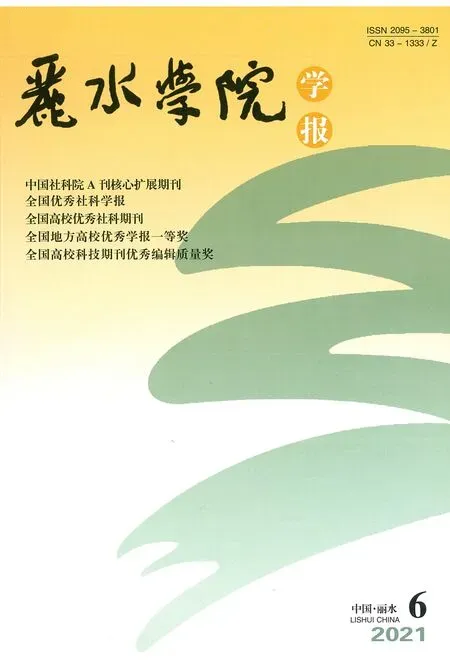論陳學昭《延安訪問記》中的人民性書寫
白玉華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陜西西安710119)
20 世紀30 年代至40 年代的延安是一個復雜的文化場域,以1942 年為界,可以分為前期和后期,前期的延安廣納賢才,吸引著一大批青年才俊,“延安文人是個較為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奔赴延安的個人背景和動機是復雜的,但大致可歸納為:叛逆者、逃亡者與追求者”[1]。他們進入延安后,流淌在他們內心的五四個人主義、革命集體主義與延安黨的意識形態之間多有對抗、交流、磨合,這在他們的文本創作中多有體現。本文特以陳學昭的報告文學《延安訪問記》為中心,討論她在多元文化身份的加持下如何界定人民內涵,在個人現實批判立場與人民至上的集體主義立場間如何自洽。
一、人民內涵的界定
陳學昭是延安的“追求者”。她追求個性解放與自由,早期曾以叛逆、解放女性的立場登上五四的舞臺,發表一系列深具女性意識的散文,隨后遠赴法國深造,接受了西方現代教育。1935 年她放棄法國優越的生活回到中國,但國內復雜的形勢與多變的局面讓她感到郁悶彷徨。1937 年盧溝橋事變拉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國共兩黨達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識,共同抵御外敵。但國統區專制的政治以及腐敗的經濟讓許多人感到失望,消極抗戰更是讓人大為不滿,而關于延安的新聞時不時地傳到國統區。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主張堅決抗戰,一時間延安成為廣大知識分子、愛國青年心目中的圣地。此時的中國,抗戰已然成為主旋律,五四提倡的個性解放、反叛精神由于民族危機的爆發而被民族解放所代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愛國青年與知識分子追求革命、向往延安,紛紛奔赴“紅色圣地”。陳學昭在國統區讀到范長江和斯諾對延安進行訪問的報道,也被延安所吸引,她下決心去延安尋求新生活。
陳學昭是以國統區《國訊》周刊特約記者的身份進入延安的,她在書中多次提到自己外來者的身份,這為她相對自由地出入各種場合對延安做全面的觀察提供了便利,也為她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個性提供了保障。但更為重要的是,陳學昭外來者身份所暗含的張力。首先,陳學昭由國統區到解放區,見證了國人在不同政黨制度下不同的生活狀態。國統區高層將領們消極抗戰,大后方有閑階級“隔江猶唱后庭花”,“高等流氓”悠閑地遛鳥,百姓生活艱苦又麻木冷漠……這與解放區青年朋友熱情洋溢的學習生活、民眾揮汗如雨的大開荒生產運動、高級領導人嚴肅又緊張的工作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次,陳學昭前期持個人主義的現實批判立場,進入延安后,面對延安革命集體的強勢話語,她內心的天平失衡,曾經奉行的個人主義與革命集體主義開始糾纏拉扯,“沖在這樣一個人潮里,我有點著急,不曾習慣,而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有點害怕被它卷了去”[2]105。這從她對延安的書寫中便可見一二。比如,延安民主集中制建設成效與問題并存,商業市場既自由又失序,文化教育的普及契合了革命任務但封閉單一,技術人員得不到足夠重視,等等,陳學昭一方面對革命集體主義給予了贊揚與支持,另一方面又尖銳地指出了革命建設中所存在的問題。
在戰時文化語境與延安意識形態的規約、以及個人文化身份的多元與立場嬗變的糾葛等因素的合力之下,陳學昭在歷時一年的訪問中構建了自己對人民內涵的理解。
從20 世紀20 年代開始,就有知識分子陸續探討人民的內涵。人民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它是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基本成員,是一個集合概念,它的具體內涵在不同時期不同形勢下有著不同的解讀。從數量、類、主體、本質特征等四個方面看來,李大釗在《庶民的勝利》中僅僅把工人視為人民,陳獨秀在《中國勞動者可憐的要求》中也強調工人(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核心,農民因為屬于有產階級不能進入人民的核心范疇[3]。相比李大釗和陳獨秀,陳學昭受當時戰爭與革命的影響,將人民的范圍擴大了許多。她筆下的人民以勞動群眾為主,包括了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各個年齡段的人們,人民在數量上占國家人口的絕大多數。具體有工人、農民、軍人,參與不同黨派的工作人員,也包括體制外的無黨派人士。
1942 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中指出:“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的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4]在這里,毛澤東把人民主體明確闡釋為工農兵。對比毛澤東,陳的解讀更加注重公民視野下的人民。公民是一個個體概念①公民也是法律概念。這里借助公民來說明陳學昭人民觀中的個人主體。,陳學昭從彰顯個性、強調啟蒙的五四文化中成長起來,又受到西方公民教育的影響,很重視公民的權利,即個人權利與義務。“中國人的社會關系就是說公民與公民間的正常交際,在封建社會是沒有的,隨著幾次革命而轉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還是極冷酷的。”[2]240“我想該努力建立起男女之間正常的公民的友誼,提高公民教育與公民道德,也就是提高同志之愛。”[2]270公民視野下的人民彰顯了陳學昭對個人主體意識的重視,她的人民觀、人民內涵是個人與集體的結合,這與她外來者的多元文化身份相契合,既浸透著民族戰爭時期革命文化對集體的重視,也彰顯了她作為一名沐浴過五四個人主義春風并受西方現代民主制度熏陶的精英知識分子對自我主體的堅持。
二、個人與人民的磨合
五四時期,彰顯個性、思想啟蒙一度成為焦點。五四落潮之后,“革命文學”代“文學革命”而后來者居上,左翼文化成為新的焦點。20 世紀30 年代戰時背景下,集體主義話語和個人主義話語更是暗流涌動。民族危機的解決離不開集體的力量,深受五四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進入延安后,從五四個人主義的狹小空間走向民族解放的廣闊天地,在文化創作領域也用革命理性和戰時文化來規范統攝。值得注意的是,在戰時文化語境中,知識分子開始主動追求集體主義話語,反思并克服個人主義話語,以達到個人主義立場的祛魅。
陳學昭既是五四傳統知識分子的代表,又是一個向往革命、憧憬延安的愛國志士。在延安文化場域內,她所秉承著的個人主義、啟蒙意識在現實中不知該如何立足,短暫的惶惑與不安過后,她選擇用集體主義話語統攝個人主義話語。布萊恩·特納說,“一個社會的主要政治與個人問題都集中在身體上并通過身體得以表現”[5]。陳學昭實現集體主義話語對個人主義話語的超越具體表現在身體特征的變化上。在國統區,陳學昭時常穿西裝,但在和八路軍以及同行之人的接觸中,她發現在延安人們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工褲襯衫打扮,她的穿著混在一群人中顯得格格不入,最終她也認為這么穿是不合適的,并換上了工褲與襯衫。她還把自己喜愛的寒暑表送給別人,“為著不愿太過文明人的生活”[2]102,還學會了洗床單、紡線,凡事親力親為。西裝、寒暑表等等是她個人的喜好,代表她的個性風格,但在延安她主動剝除這些裝飾,遠離這些東西帶給她的歸屬感和自我認知,以此積極向群眾靠攏。
初入延安的陳學昭對革命集體的想象是充滿烏托邦色彩的,隨著長時間的訪問,她對延安的現實情形有了深入了解,也認識到延安革命集體的建設面臨諸多困境。比如人們身上還殘存著封建落后的毛病:他們愛好打探別人隱私,借集體的名義隨意破壞他人個人財產,造謠男女之間的正常交往。延安集體主義建設的艱難也體現出來:一味遷就導致了養懶和吃公家的問題;有的商人胡亂要價擾亂了市場秩序;有的百姓自私自利、好吃懶做,目光短淺,只知道向公家索取卻不自覺盡義務;體制內一定程度上官僚主義盛行,行政體系不甚健全等等。她逐漸認識到人民至上并不代表國民的劣根性就得以消除,國民素質的提高仍是一個艱難而持久的過程,個人和集體的關系也需要維持平衡。在最初的興奮過后,她恢復了理性,時刻警醒自己“我該快快離開延安了,我正在漸漸地習慣于一切,而對于這地方的一切,正在漸漸地消失敏感性。這是很不好的”[2]356。陳學昭試圖融入集體,又謹慎地維持著外來者的身份,始終以獨立、自由、理性的立場游離在集體主義的洪流之外。
作為一名女性,陳學昭非常自覺地從女性角度來觀照延安。革命語域中,男性占盡了革命優勢,也由此確立了以男性為中心的革命集體,這個革命集體以己為標準對女性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在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這樣宏大的主題之下,女性開始有意無意地壓抑自身的性別意識以配合戰爭和革命建設的需要。
陳學昭筆下對延安女性的描寫呈現出 “無性化”和“雄性化”的特點,女性性別特征被遮蔽。延安女性的身材多是高大強壯,腳步大、走得快,抗大的女學生非常胖等等,女性性格多是豪爽直率,在穿著方面多是穿軍裝或是工褲襯衫,很少有鮮艷或個性的裝飾品。在這里,傳統女性的纖弱之美幾乎不見了,代之以男性的力量之美,身體和外表都以男性特質為標準,有意遮蔽女性的性別特質。抗戰的興起使“民族化”“大眾化” 的集體想象高揚,女性紛紛以高度的政治自覺向主流靠攏。陳學昭因天熱換上了艷麗的西服出街,馬上就會招來大家的不滿。戰時的延安男女都主動追求性別平等,在這樣的號召下,女性為突顯政治覺悟高紛紛爭著搶著上戰場、搞政治,最適合女性自身特點的保育、教育工作卻無人問津,一些人甚至以此為恥。抗戰時期高揚的集體意識使得女性將自身的解放與民族國家解放融為一體,女性的性別特質被壓抑或忽視,女性意識和女性倫理關懷被拋在腦后。
女性以自身的異化即女性“雄性化”“無性化”為前提加入革命集體,這是“以女性特征的淡化甚至消解為代價而形成的對國家意志與階級意志的高揚,實際上是對女性作為女人而存在的生命意義的漠視”[6]。解放區女性地位雖然有所提升,但并不代表女性已經完全解放,她們仍處于集體的邊緣位置。更令陳學昭憂心的是延安女性對自我回歸和找尋的主動放棄,“婦女自身如果不去從事與自身利害有關的事業,那么到頭來還是自己吃虧”[2]156。大部分延安女性為了向主流靠攏,主動淡化甚至壓抑自身的性別意識和立場,殊不知,這正是對自身獨特特征的親手扼殺。
革命話語的統攝形成對女性性別特征的遮蔽是較為顯性的層面,革命話語本身對女性生存狀態和精神困境造成的遮蔽則更為隱秘。革命理性的高揚使得女性解放被置于民族解放之下,但實際上女性解放還面臨男尊女卑的傳統道德倫理的障礙。陳學昭作為五四新女性的代表,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在《兩性與戀愛》這一節,她提到:“我們,中國女子的斗爭,是兩方面并進的:在民族、社會的利益方面,我們女子的利益就是勞動者的利益,要勞動者得著解放,我們女子也方能得著解放。……在兩性方面,我們要同這些謀民族解放的共同友人,但卻是統治慣了的,背上負著重重歷史的,封建的歧視女子的惡習慣,這樣的男子斗爭。這個雙方并進的斗爭是同樣的艱苦。”[2]234一方面她認為民族解放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另一方面也認識到女性自身的解放和民族解放是齊頭并進的關系,兩者一樣艱難。在生活中女性承受了更多的壓力,比如女性生育問題,后代撫養與教育問題等,在戀愛方面有男性干部對女性的褻瀆,男性戀愛心理的卑劣等,女性解放的障礙不僅來自革命男權文化的壓制,還來自傳統道德倫理的桎梏。陳學昭以女性細膩的視角、批判的眼光對兩性之間的問題進行了尖銳的揭露,直面造成女性悲劇命運的雙重原因。
在20 世紀30 年代戰爭語境和延安意識形態的規約下,陳學昭在革命光輝的照耀之下,短暫地以高揚的革命理性統攝創作,經過沉潛之后,她恢復理性立場,重新審視人民、審視集體。她既看到人民本位觀的必要性,人民至上政策對人民的社會政治地位的確認和對人民幸福生活愿望的重視,認識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7]。同時,她也看到,在某個階段人民集體話語具有相對的封閉性和單一性,一定程度上有對集體的過度闡釋和對個人的忽視。受五四個人話語和西方現代啟蒙的影響,陳學昭強調個人話語對人民集體話語的補充,人民本位觀的最終目的是要每一個人都能全面自由發展,她以敏銳的眼光捕捉到了人民與個人的辯證關系。她意識到了延安革命建設面臨的困境,但也明白建設中國必然是一個長久的過程,她對延安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它是天天改進的,還有希望……有許多事情他們已經努力在做,或者正在開始努力做,還沒有發生期待的效果,可是,他們并沒有把需要做的事情漏過”[2]131。
三、文藝大眾化與人民性書寫
戰時共產主義訴求的是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它所倡導的必然是大眾文化,而文學是個體化的事業,大眾文藝與個人書寫如何平衡是20 世紀30 年代延安文化場域中亟待解決的難題。延安文藝提倡“人民本位文學觀”,“‘人民性’又與‘階級性’直接相關,其目的都是讓文藝實踐積極參與當代社會進程,完成如下歷史任務,即‘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8]46,人民性書寫為文學參與社會實踐與發展提供了合理依據,體現了勞動人民的精神面貌、政治意識,充分發揮了文學的社會功能。它“對現代中國革命的貢獻、對中國的社會改造所起的巨大作用而論,幾乎可以說古今中外無與倫比,而它加諸文藝的規定、限制、磨折以至傷害,也可以說是前無先例后無過者”[9]。究其原因,“黨的文學”是為革命、“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一定程度上它會忽視“小我”的書寫。20 世紀30 年代延安的文化環境較為寬松,文壇也涌現出一批“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的作品,但是文藝自由仍是有限度的自由,陳學昭在訪問期間看過、聽過多種形式的文藝表演和報告,敏銳地感受到了延安文藝大眾化的這一特點。
陳學昭在延安參加的最多的文藝匯報形式有兩個:一是報告;二是文藝表演。其中報告是將文藝大眾化、文藝為革命為人民服務發揮到極致的形式。報告分為聲音媒介和紙質媒介兩種,以聲音為傳播媒介的報告即是報告人為聽眾口述內容,報告人多是軍隊的高級將領、各行政機關的領導人,通過這樣的形式打破了民眾與領袖的壁壘。報告內容涉及前線戰事、政策講解、科學普及等等各個方面,深入淺出、聲情并茂的講解方便了文化水平有限的民眾通過這種方式獲取信息,這有效地將上層與大眾對接起來,實現信息的有效傳達與反饋。陳學昭在延安聽過周總理長達五個小時的報告,總理將敵我形勢、前線的戰況講述得十分清楚,同時和現場聽眾互動。一場報告結束,民眾對戰爭的激烈與形勢的緊迫有了生動的認識,民眾的戰斗熱情與抗戰決心也被點燃。邊區許多高級將領和領導人都通過這種方式與群眾交流,拉近與群眾的距離。以紙質為傳播媒介的報告最重要的是保留信息給沒時間到現場聽報告的人。兩種傳播媒介的結合充分照顧到了不同的受眾,盡可能地做到了全民參與革命和建設。
另一個重要的文藝形式便是創作與表演。文藝表演的演出類型有話劇、歌曲、京戲、秦腔等,作品內容融合了娛樂性、革命性、鼓動性、教育性。陳學昭發現文藝創作與表演為了遷就民眾而放低藝術追求的現象很常見,比如,話劇為了照顧大眾的口味變成了大雜燴,突兀地加入了大鼓、雜耍……創作者被邊緣化,民間技師則被追捧為大師。除此之外,一些話劇作品脫離現實生活,程式化地表達抗戰主題,機械地宣揚抗戰高于一切,刻意回避人的正常情感,對此陳學昭提出質疑:“中國的青年現在是不是不戀愛呢?恐怕有些老年人,也還不能避免。”[2]284
文藝創作傾向于娛樂性、鼓動性甚至是程式性而藝術性欠缺,對此,陳學昭認為延安文藝界重視宣傳革命、鼓動大眾確有其必要性,但不能以藝術性的缺失為代價,藝術性和娛樂性要相互補充。同時,創作者與受眾也要相互磨合。陳學昭明確提出“不要太遷就民間”[2]197,在延安大概有200 多個詩人,文化界負責人直言“培植那些小說家,不是我們的職責,我們只要是能夠接近群眾……”[2]200,文藝大眾化直接等于大眾的文藝,那提高的空間就不存在了。陳學昭在看過多場文藝匯演后,對文藝的發展提出相對中肯的意見。一方面她立足于當下,為團結群眾和抗戰勝利,民族集體話語的表達和人民性書寫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極為重要的。另一方面,她又將眼光放長遠,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注重培養多樣化的人才,在提高創作水平的同時也提高民眾的普遍審美能力。
延安在人才培養、教育方面有著一切以抗戰為先的特點。在陳學昭看來,在延安有這樣一種風氣——“不學軍事,就學政治,不學政治,就學文學”[2]199,學習等級森嚴,教學內容也有高低之分——國防教育比自然科學重要。單一的教育造成人才比例的失衡,政治軍事領域人員冗雜,其他普通技術工人卻長期匱乏。在革命理性的統攝之下,人人涌向革命政治隊伍,自身的獨特性被忽視,造成了教育的單一與人才的失衡。陳學昭的眼光是長遠的,她認為未來的建設發展最需要的就是各領域的專業技術人員,抗戰與建設要同時進行,光抗戰不建設、先抗戰后建設都是不可取的。
陳學昭從現實出發,以一個普通人的視角、外來者的立場觀察、書寫人民在邊區政權下的生存與生活,反映了抗戰初期“赤都”延安的面貌。在訪問延安期間,她從最初的對集體主義充滿烏托邦式的想象到逐漸回歸現實恢復理性。她看到了傳統封建倫理制度對人民的遺害,革命集體主義話語統攝下個人意識和女性意識的壓抑和淡化、文藝大眾化對個人書寫的忽視,這些在革命建設過程中的困境讓她意識到革命的勝利和國家的建設是十分艱難的。她深知革命的勝利要依靠人民的力量,革命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國家集體精神是以具體的社會的‘個人’為前提,國家集體主義也是以每個社會個人的發展和幸福為最后目的”[8]48。在五四新文化和西方現代教育的沐浴下,她試圖在人民主體性的確立和個人主體性的實現之間找到平衡。陳學昭以一個精英知識分子的自覺,清醒地認識到延安要走的路還很長,她對人民的復雜思考形成了她在《延安訪問記》中復雜的人民性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