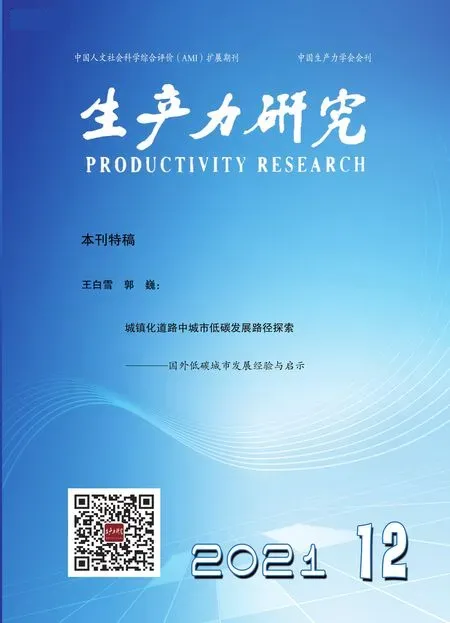超額商譽、研發投入與企業創新績效
任仕強,李本光
(1.貴州大學 管理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2.貴州大學 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一、引言
上市公司掀起并購浪潮始于2012 年,共有1 018家公司參與并購重組活動,商譽總值1 670 億元。到2017 年并購活動達到巔峰,共1 949 家公司參與并購活動,商譽總額超過1.3 萬億元(董竹和張欣,2021)[1]。雖然,企業參與并購重組活動有助于整合資源優勢、發揮并購協同效應、增強企業競爭力,但并購的對象不符合企業未來成長以及過高估值并購公司的價值會造成超額商譽(張新民等,2018)[2]。而過高的商譽也意味著購買方的高預期和高風險,過高估值標的公司的價值可能會削弱企業核心競爭力而成為企業的經營負擔,具體表現為超額商譽擠占了公司的稀缺資源(魏志華和朱彩云,2019)[3]。因此,合理的并購行為應著眼于加強產業整合和提升企業生產能力。但由于上市公司并購原因撲朔迷離,存在著部分并購活動屬于管理層非理性行為。如果,企業的并購目的不在于追求并購協同效應,而是出于管理層私利行為,那么過高的并購商譽將會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和擠占公司的稀缺資源,削弱企業未來可持續盈利的創新能力。
企業創新活動是保持產品市場競爭優勢以及未來可持續盈利的重要動力,也是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然而,創新活動具有回報周期長、高投入、高難度、高風險、信息不對稱等特點,導致企業的研發活動相比其他投資活動更容易受到融資約束(張旋等,2017)[4]。那么高溢價并購商譽是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為此,本文通過理論分析并實證檢驗高溢價并購對企業當期和未來一期創新績效的作用機制。
二、文獻回顧和研究假設
(一)超額商譽與企業創新績效
現有超額商譽的文獻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財務審計方面的研究,超額商譽提高了審計收費(趙彥鋒,2021)[5]、高審計質量能抑制企業的超額商譽(郭照蕊和黃俊,2020)[6]、超額商譽加劇了企業的商譽減值程度(張萍和周昕雨,2020)[7];二是企業績效方面的研究,超額商譽影響了企業未來三年的經營績效(魏志華和朱彩云,2019)[3]、超額商譽持續影響并購后兩年的并購績效(張臘鳳和張蓉,2021)[8];三是創新方面的研究,超額商譽抑制了企業創新,內部控制緩解了兩者之間的關系(王蓉,2020)[9]。超額商譽對企業創新效率有顯著的負面的影響,其作用機制為債務融資成本的上升和分析師樂觀偏差程度導致的(董竹和張欣,2021)[1]。企業的并購動機在于通過整合雙方資源結構以提升綜合實力,合理的并購商譽可以通過協同效應為企業帶來超額盈利,而過高的商譽則會成為企業經營的負擔(魏志華和朱彩云,2019)[3]。企業過高的商譽是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績效呢?
企業的研發屬于高風險、高投入、高不確定性的探索活動,因此,企業的研發創新相較于其他投資活動更容易受到企業可用資金的限制。董竹和張欣(2021)[1]研究發現,當企業內部可用資金有限時,外部籌資是企業研發資金的重要來源。并購過程中產生的過高商譽并未給企業帶來超額盈利能力和并購協同效應,卻向外界傳遞了企業不當并購行為的消極信號。投資者會將企業的超額商譽視為管理者的私利行為而非未來經濟利益流入和可持續的履約能力(李健等,2021)[10]。高溢價并購背后是為了簽訂高業績承諾還是通過未來的商譽減值扭曲經營利潤,投資者并不能準確評估超額商譽的收益與風險。因此,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活動時,會提高資金使用成本或放棄投資,以規避超額商譽帶來的風險,導致企業的融資成本上升。另外,企業并購重組多以現金方式支付(葛結根,2015)[11],過高的商譽耗費了企業內部現金流,降低了企業的償債能力,銀行等機構將會收緊信貸供給,加劇了企業融資約束,從而影響企業的創新活動。魏志華和朱彩云(2019)[3]研究發現,企業發生并購后,并購商譽會影響企業未來三年的經營績效。本文考慮到創新產出具有滯后性,故考慮企業當期和未來一期的創新績效。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
H1: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超額商譽負向影響企業當期和未來一期的創新績效。
(二)超額商譽與研發投入強度
企業并購過程中產生的超額商譽是由于標的資產公允價值被高估以及并購方高估雙方資源整合的協同效應。從資源擠占效應視角看,過高的并購溢價不僅沒能提升企業核心能力,反而侵占公司資源以及增加并購整合成本,這無疑減少了企業的可用資金。企業將過多的資源用于并購協同效應上,導致可用于產品生產、研發創新、固定資產投資、設備更新升級等活動的資金減少了(魏志華和朱彩云,2019)[3]。朱郭一鳴等(2021)[12]研究發現,過高的并購商譽降低了企業資產周轉率,表明超額商譽占用了上市公司的內部資金,加劇了公司融資約束。沈棟昌和謝會麗(2017)[13]研究發現,融資約束降低了企業研發活動的積極性,削弱了研發投入強度。因此,超額商譽擠占了原本用于企業研發活動的資源,負向影響企業研發投入強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
H2: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超額商譽與企業研發投入強度呈負相關。
(三)研發投入強度在超額商譽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存在中介效應
企業研發投入目的在于獲得發明專利、新產品、新技術等能為企業未來帶來經濟利益流入的創新活動。現有研究表明,企業的研發活動提高了創新績效。如林筠和張瑤(2017)[14]通過2011—2015 年創業板面板數據研究發現,科研經費和人員的投入促進了企業的創新產出。曾德明等(2015)[15]選取汽車產業為樣本實證檢驗了企業研發活動促進了創新效率。結合上文分析的假設1 和假設2,本文認為超額商譽對企業創新的影響路徑:超額商譽—占用創新資源(資源擠占機制)—降低企業創新績效。因此,超額商譽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可能是通過研發投入強度這條路徑進行傳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3:
H3: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研發投入強度在超額商譽與企業創新績效發揮著中介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從2007 年執行新《企業會計準則》,要求上市公司報告并購商譽信息;現有專利數據庫已更新至2017 年。故而,選取2007—2017 年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來源:CSMAR 和WIND)。根據本文研究脈絡,對研究樣本做了如下篩選:(1)剔除金融、保險類企業;(2)剔除樣本中缺失的數據;(3)剔除上市公司被ST、PT 和退市的樣本;(4)采用Winsorize 對連續變量進行首尾1%的異常值處理。經數據篩選處理后,共收集6 481 個公司年度面板數據。
(二)定義變量
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企業創新績效(Innovation)參考李東紅等(2020)[16]、黃遠浙等(2021)[17]的做法,以企業獲得的授權專利總數和申請的專利總數衡量創新績效。
2.解釋變量。超額商譽的衡量方式參考魏志華和朱彩云(2019)[3]的做法,以實際商譽與期望商譽的差額衡量超額商譽。回歸模型中的變量如表1 所示,計算方式如下:


表1 超額商譽計算變量定義
3.中介變量。參考劉鑫和薛有志(2015)[18]的研究,選取企業研發投入強度作為資源擠占效應的代理變量,研發投入強度(Rda):研發投入在總資產中的占比進行度量。
4.控制變量。控制變量的選取參考朱郭一鳴等(2021)[12]、董竹和張欣(2021)[1]的做法,控制變量選取如表2 所示。
(三)模型構建
為了研究企業過高的商譽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本文參考董竹和張欣(2021)[1]的做法,采用控制行業和時間的多元回歸模型。構建回歸方程如模型(1)、模型(2)、模型(3)所示。

其中,j=0/1,因變量為企業創新績效(Innovation)和研發投入強度(Rda);自變量GW_ex為過高的商譽即超額商譽;Controls代表本文選取的九個控制變量,ε為隨機擾動項。模型(1)~模型(3)為參考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19]的中介效應逐步檢驗法構造,分別檢驗假設1~ 假設3。如果,回歸模型(1)的系數β1顯著為負,即可驗證超額商譽對企業當期和未來一期的創新績效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因此,假設1 得到實證支持。如果模型(2)中的GW_ex的回歸系數Γ1顯著為負,表明企業過高的商譽削弱了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即假設2 通過了實證檢驗。如果模型(3)中的回歸系數λ2大于零,則λ2×Γ1系數乘積為負,表明企業過高的商譽通過削弱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而降低企業創新績效,即假設3 通過了中介效應檢驗。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由表3 可知,創新績效1(Innovation1)平均值:3.007,標準差:1.286。創新績效2(Innovation2)平均值:3.336,標準差:1.317,表明不同企業之間創新績效差異比較大。超額商譽(GW_ex)均值為-0.000,標準差0.076,這與學者董竹和張欣(2021)[1]的超額商譽均值:-0.000 4,標準差:0.056,大致相近。其余變量與以往研究相近,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表3 描述性統計分析
(二)相關性分析
根據表4 Pearson 相關系數矩陣可知,無論是以商譽期望回歸模型計算的超額商譽還是經過行業均值調整計算得出的超額商譽與企業創新績效均呈負相關的關系,這與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1 吻合。超額商譽與企業研發投入強度呈負相關,且在1%水平上顯著,與本文假設2 吻合。由于此結論是尚未考慮其他因素而得出的,具體兩者之間的關系有待進一步實證檢驗。其中未報告部分,獨立董事比例(Independ)與董事會規模(Board)之間的相關系數大于0.5,但模型通過多重共線性檢驗,所有變量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2,最大值為1.63,故排除多重共線性問題。限于篇幅,此部分未作報告。

表4 主要變量相關性分析
(三)回歸分析
1.超額商譽與企業創新績效的回歸結果
表5 列示了過高的商譽與企業創新績效的多元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和第(3)列匯報了僅使用超額商譽(GW_ex)和行業年度虛擬變量對當期和未來一期企業創新績效(Innovation1 和Innovation2)的實證結果。第(2)列和第(4)列匯報了控制盈利能力(Roa)、固定資產水平(Ppe)等九個變量的回歸結果。由表5 可知,超額商譽(GW_ex)的回歸系數均小于零,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過高的商譽對企業當期和未來的創新績效均有負向影響。由此驗證本文的假設1,即超額商譽與企業當期和未來一期的創新績效呈負相關關系。

表5 假設一回歸結果
2.超額商譽與研發投入強度的回歸結果
由表6 第(1)和(3)列匯報了超額商譽與研發投入強度的回歸結果。其中,因變量為當期(Rda)和未來一期研發投入(Rdat+1)。超額商譽(GW_ex)對當期和未來一期的研發投入強度回歸系數分別為-0.023、-0.013,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超額商譽(GW_ex)顯著降低了企業當期和未來一期的研發投入強度。因此,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2 通過了實證檢驗。

表6 研發投入強度的中介效應
3.研發投入強度的中介效應
表6 為中介檢驗結果。其中,第(2)列和第(4)列為當期和未來一期的研發投入強度(Rda、Rdat+1)的回歸系數分別為15.952、13.504,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研發投入強度顯著提升了企業創新績效。而由第(1)列和第(3)列的回歸結果可知,過高的商譽與研發投入強度之間的關系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超額商譽顯著削弱了研發投入強度。因此,綜合第(1)列~(4)列的回歸結果可知,中介效應λ2×Γ1顯著為負,研發投入強度在超額商譽與企業創新發揮著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本文的假設3 得到支持。
五、穩健性檢驗
(一)替換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
表7 為替換變量回歸結果,被解釋變量的替換參考黃遠浙等(2021)[17]的做法,以企業申請專利總數衡量企業創新績效(Innovation2)。解釋變量的替換參考魏志華和朱彩云(2019)[3]的做法,將并購商譽凈額標準化后與行業均值之差衡量超額商譽。替換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分別是表7第(1)列、(2)列和(3)列、(4)兩列,結果顯示超額商譽對當期和未來一期的創新績效均在1%的顯著水平上呈負相關關系。表明替換變量后結論依舊成立,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結論的穩定性。

表7 穩健性檢驗
(二)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檢驗
表8 為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檢驗。由表8 的中介檢驗結果顯示,企業過高的商譽通過研發投入強度對企業當期和未來一期創新績效的間接中介效應分別為-0.548 5、-0.327 7,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置信區間分別為[-0.656 3,-0.440 8]、[-0.447 8,-0.207 6]。由此可知,在95%的置信區間都不包括零。因此,通過Bootstrap 中介效應檢驗得出的結論與本文研究假設3 一致,即研發投入強度在超額商譽與企業創新績效發揮著中介作用。

表8 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檢驗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共收集6 481 個上市公司年度非平衡面板數據,實證檢驗超額商譽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研究發現,超額商譽對企業當期和未來一期的創新績效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進一步研究影響機制分析發現,研發投入強度(資源擠占效應)在超額商譽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存在部分中介效應。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果,提出三點建議。(1)對于投資者,應當謹慎評估上市公司并購行為,深入了解超額商譽對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理性做出投資決策;(2)對于上市公司,選擇縱向、橫向和多元混合并購應當根據企業經營現狀以及未來戰略規劃,合理估值標的資產價值以及并購產生的協同效應。否則,過高的商譽將會占用公司的稀缺資源,加劇企業研發活動面臨的融資約束,削弱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最終影響企業的創新績效和經營業績;(3)對于監管機構,完善企業并購重組市場制度和法律法規,制定嚴格的并購信息披露制度以保護相關者的利益,從源頭治理企業過高的商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