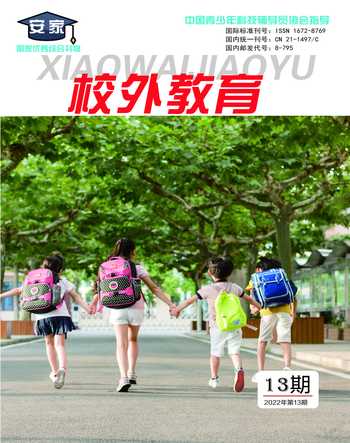從中國畫的觀看到創作
沈舍非
摘要:中國是特殊而又不特殊的一類藝術,特殊在于他有最獨特的觀看方式,手卷等藝術形式是絕無僅有的;不特殊在于它符合藝術創作的一般規律,先有創作沖動,再尋求合適的技法,最后完成作品。兩個“非傳統”水墨藝術家的例子,說明理解中國畫的觀看方式會幫助藝術家更好地去創作。
關鍵詞:中國畫 水墨 徐龍森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藝術是并非完全抽象,而是依賴于物質,所以任何藝術品都具有自己的物質屬性,中國畫也不例外。在畫家所畫的內容之外,作品的裝裱,作品目標的對象,展示的方式時間地點都是作品的一部分,因此,山水畫的創作離不開研究誰在看山水畫,以及怎么樣看山水畫。關于交互藝術的本質有很多說法,廣義上任何涉及到觀看者和藝術家,藝術品互動的作品都可以叫做交互藝術,因此,某種程度上,中國畫甚至可以說屬于交互藝術的一種的。
筆者把中國畫分為兩大類。第一類,一種相對動態的展示方式,手卷和冊頁,前者要邊卷邊看,后者要邊翻邊看,參與性較強,觀看者可自行決定每段景致的停留時間。因為冊頁本身也是起源于手卷,因此在后文就不對冊頁多做闡釋。手卷由于方便攜帶,常常被文人在雅集時觀賞傳閱。內容上分為兩種,第一種山水手卷,并非是地圖式地展現山水的全貌,他更像是觀看者附身畫家,身臨其境,因為畫家本人在創作過程中也是不能看見畫面全貌的。證據是:在明式家具收藏界,大多數畫案的長度在100cm左右,除去筆墨硯臺筆洗等繪畫工具,可做畫的面積十分有限,因此筆者推測,有些長卷作品甚至在創作的階段就是一段段進行的,創作者和觀賞者所面對的都是一個移動的畫面。第二種:敘事性,將一個事件按照從右至左的順序連續表現,例如《韓熙載夜宴圖》《洛神賦圖》,類似于定格動畫,意在展現一個有劇情的故事,以時間為軸安排順序,超越了物理空間安排的限制。手卷就是藝術家安排的一個沒有后臺的、永不休息的劇場,相對的,觀看者就是劇場的觀眾。
第二類:相對靜止的展示方式,立軸式繪畫和屏風畫,壁畫都在這個范疇,即觀看者不用有動作即可窺見全貌,許多兩宋紀念碑式山水最早都是以屏風畫和障壁畫形式存在,后來才被重新裝裱成為卷軸畫。其目的在于拓展室內空間層次,足不出戶,臥游即可欣賞山水風光。這種“展現”更像是一種地圖式的解釋,因為其本身特性決定的一覽無余,一目了然。
當然無論是哪種表現形式,古代山水畫的觀賞有很強的階級性,作品的流傳和觀賞都僅限于比較高的社會階級(或宗教系統),就連后來以算卦賣卜為生的黃公望,。都曾經官至中臺察院掾吏,相當于中央檢察系統輔佐官,地位不能說不高。甚至在明末商品畫盛行的時候,藝術品也不是一般勞動人民接觸得到的。藝術品的欣賞有一定的門檻,尤其到了董其昌以后的“文人畫”,山水畫提倡筆墨先行,寫實程度并不高,沒有經過訓練就不會真正地理解。正如在談及書法藝術時提到的:文化意味著訓練和選擇,當你不理解某種內容的時候,傳播就無從談起,因為傳播需要輸出,輸出意味著理解和內化,僅僅“看到”并不代表“看懂”或者“欣賞到。這個角度來講,藝術家是自己選擇了觀眾。
所以,在此基礎上的“交互”“參與”還是“公共”都需要打個引號。沉溺于小圈子的自娛自樂,所謂的圈子就是比較廣的場域,只在固定圈子內尋求心理認同,無意和大眾交流,你必須使用程式畫的筆墨才能被圈子所認可,格式化山水承載不了大自然的氣象。過度提倡擬古必然會導致程式畫的語言糾結于筆墨而喪失了創作的真諦“沖動的表達”,俗話說起來就是“看起來一個樣”,內行津津樂道的各種精妙,外行看起來就是不知所云莫名其妙,這也是我認為文人畫最終窮途末路的原因:將中國畫從一般藝術的門類中分出去,簡而言之就是要搞特殊。舉個例子:要欣賞畢加索你無需習得安格爾,但是要看懂清代四王你不去了解元四家就是不行的。如果那些已存在的筆墨語言不存在了,那想必不少山水畫家就失去了創作的能力。
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當代水墨畫家徐龍森就有個很好的解答。他的巨幅山水跳脫出了一般手卷手中把玩的格局,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在他的畫中,你看不見具體的石,具體的樹,但卻仿佛置身于山中。他說要割舍的是“昏聵瑣碎的技法論”,他的畫面中“孤峰”的精神氣質,與古人遙相呼應。世界上沒有萬金油式的技法,筆墨是伴隨對象產生的敘事工具。
今年到目前為止看過讓我印象最深的山水畫作品叫《麒麟山》,是一個名叫張東輝的藝術家,把全景山水畫到了自家住的29層大樓墻壁上,順著樓梯結構布置景色,而他的創作出發點也很簡單,僅僅是因為疫情期間不方便出門,而他自己又非常想爬山。他不是專業學山水畫的,所以筆墨比較幼稚,甚至有點呆板,但是我覺得這是很多同齡山水畫家所沒有的,發自本心的創作沖動。很多山水畫家,他的筆墨技巧非常豐富,模仿能力很強,但是從他的畫面我看不出創作的沖動,就是一種“我學到的畫山的方法”“我學到的畫樹的方法”的圖像堆疊。
舉個具體的例子,七八十年代的山上植被是很稀少的,隨著綠化的普及,山水的面貌有了巨大的改變,意味著即使是同是近代,我們也要面對和前輩畫家大相徑庭的風景,固有的方法不一定是適用的。
最后我的總結是,中國畫自然有特殊的之處,手卷的時空和互動屬性是比較罕見的,但是實際上,我們視若珍寶的藝術在世界眼光審視下可能和阿茲特克人的文字沒什么兩樣,因此抱殘守缺墨守成規只會讓中國畫的發展道路越來越窄。要認識到中國畫先是藝術,再是中國的,即先有創作沖動,再有功能的技法積累,依賴物質的自然,再到新的視覺境界。吳昌碩有詩:“一拳打破古來今”,筆者認為藝術家應該貫徹這樣的創作態度,擺脫技法語言的束縛,在畫面上肆意展現自我審美觀,投射個人與自然的關系。
參考文獻
[1]巫鴻:[M]《重屏,中國繪畫中的媒材與再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