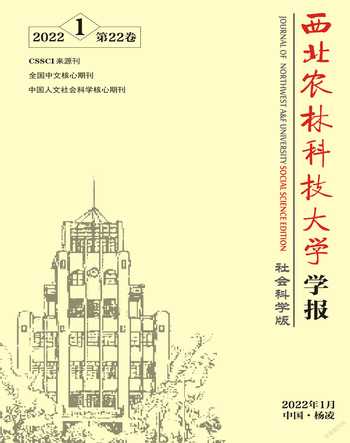社會資本、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







摘要:基于草場流轉市場轉型背景,利用內蒙古自治區和甘肅省820個牧戶調查數據,實證檢驗了社會資本、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及二者間的作用關系,并進一步探討了交易費用的中介效應和代際差異的調節效應。結果表明:(1)轉型市場下,社會資本仍能促進牧戶草場轉入,但作用方式發生變化,表現為關鍵網絡節點和牧戶主動利用社會網絡能力的作用凸顯,社會資本總量和被動依賴社會網絡信息資源流入的作用式微。(2)網絡信息渠道促進了牧戶草場轉入,但尚未對社會資本形成替代,社會資本與網絡信息渠道并行不悖。(3)社會互動通過降低草場流轉的交易費用促進了牧戶草場轉入,而關鍵網絡節點、網絡信息渠道不存在相應機制。(4)社會資本、網絡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存在顯著的代際差異,表現為新生代牧戶轉入草場更加依賴網絡信息渠道,中生代、老生代牧戶轉入草場僅依賴社會資本。據此,建議在建立和完善網絡和實體草場流轉交易平臺等方面完善草場流轉市場。
關鍵詞:社會資本;信息渠道;草場轉入;交易費用;代際差異
中圖分類號:F30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1-0115-14
引言
草場流轉制度是草原承包經營制度的補充和完善,草場流轉具有降低草場細碎化、改善牧業效率、促進生態恢復和提高牧戶收入等諸多功能[1-4]。通過草場流轉促進牧業要素合理流動,實現牧業資源優化配置,既是微觀牧戶的現實需求,也是政府宏觀層面的政策導向。然而目前我國草場流轉市場并不完善,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潛在違約風險(尤其是轉入戶過度利用草場)和交易成本成為阻礙牧戶參與市場的瓶頸[5]。特別是北方草原高度生態恢復壓力下,草場流轉還承擔著維護草畜平衡的生態功能。生產、生態雙重需求強化了流轉市場的賣方特性[6],使得交易成本呈現非對稱性,轉入戶面臨更高的交易門檻[7]。如何進一步降低牧戶草場轉入難度,提高草場轉入效率,對改善牧業要素配置和增進牧戶福利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受限于研究數據可得性,有關草場流轉的研究十分匱乏[8],僅有的少數研究重點從改善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出發,強調了社會資本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5-6,9]。其內在邏輯是:交易成本是制約草場流轉的關鍵[10],具體表現為草場流轉交易搜尋難、簽約難和監督難;草場流轉市場基于“差序格局”的鄉土社會,因此嵌入在牧區關系網絡中的社會資本,在降低搜尋費用、提高契約執行、化解交易風險等方面具有諸多優勢,有利于草場交易的實現。例如,劉博等基于2011-2015年內蒙古牧區牧戶調查的混合截面數據分析發現,社會資本提高了牧戶草場轉入概率[5,9]。
不容忽視的是,近年來牧區正在發生深度轉型,社會資本對草場流轉的作用也在隨之發生變化。首先,草場流轉市場正從傳統以熟人交易和口頭承諾為特征的“關系型”市場向以半熟人、陌生人交易和契約關系為特征的“要素型”市場轉型。即便是發生在熟人間的交易,市場化特征也愈發明顯,價格機制發揮了重要作用[11-12]。例如,2015年以來,內蒙古自治區先后出臺了《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農村牧區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建設的實施意見》《內蒙古自治區農村牧區土地草原經營權流轉交易市場運行規范(試行)》。數據顯示,到2020年8月,僅錫林郭勒就已規范流轉草場2 129萬畝,涉及牧戶8 948戶,達到全盟草場面積的12.46% 。其次,傳統草場流轉市場上社會資本賴以發揮作用的社會環境逐步演化。一方面,市場交易主體呈現代際差異。一些80后、90后牧民返鄉創業或繼承祖業,成長為新一代牧民[9],同時老一代牧民并未完全退出畜牧業,形成老中青三代畜牧業經營主體并存的格局,交易主體的代際差異可能對傳統草場流轉市場的交易習慣產生沖擊。另一方面,牧區社會關系發生嬗變。受牧民定居、分散經營以及市場化的影響,牧民逐漸呈現“原子化”特征,個體間的互惠關系向經濟利益關系轉變,傳統熟人交易間依賴的信任和互惠機制逐漸消解[13]。
與此同時,市場主體的社會交往模式以及信息來源渠道也在發生深刻變革。一方面,隨著牧區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完善、智能手機的普及以及網絡社交軟件的廣泛應用,牧戶間的溝通由線下向線上轉變,網絡社交的作用愈發凸顯。另一方面,網絡社交平臺和網上草場流轉服務交易平臺為牧戶提供了新的信息渠道 。“互聯網+”的新型草場流轉市場上,網絡信息渠道加速了信息的傳遞速率,擴展了信息傳播距離,很可能對社會資本在交易實現中的作用形成部分替代,從而弱化社會資本的影響。這意味著,忽略草場流轉市場的新變化,既可能夸大社會資本的作用,也可能忽視新興市場要素對改善草場轉入效率的影響,不利于草場流轉市場的建設和發展。
基于上述梳理,本文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在草場流轉市場轉型背景下,社會資本和信息渠道在牧戶草場轉入中各自作用如何?二者是替代關系還是互補關系,又是否是通過降低交易費用作用于草場轉入?此外,多個代際市場主體并存的格局下,社會資本和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是否存在代際差異?如存在,呈現何種差異?對于上述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助于重新檢視社會資本在轉型市場上的作用效果,還有利于挖掘改善草場流轉效率的新型因素,對于調整現階段草場流轉政策以及進一步完善草場流轉市場的建設思路具有重要作用。為此,本文利用2020年內蒙古自治區和甘肅省牧區820戶牧戶微觀調查數據,實證檢驗社會資本、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及二者間的作用關系,并進一步討論其是否通過降低交易費用作用于牧戶草場轉入,以及牧業經營主體的代際差異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影響中的調節作用。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轉型市場下社會資本與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機理
隨著草場流轉市場從“關系型”市場向“要素型”市場轉型,社會資本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可能發生如下變化:
1.牧區差序格局關系下的熟人交易內含的信任機制和聲譽機制逐步被契約關系和價格機制所取代[14],社會資本作用逐漸弱化。社會資本可以降低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緩解道德風險,從而增加互信[15]。傳統草場流轉市場上,基于血緣、地緣形成的親鄰關系相較于完全陌生的外來交易者更為牧戶所信任,能夠降低草場轉出者對于承租者轉入草場后出現違約行為的擔憂,轉出者往往傾向于與社會資本豐富的熟人交易;與此同時,熟人社會中社會網絡越豐富的牧戶,其違約付出的聲譽成本越大[16],為流轉契約的執行提供了一種內在履約激勵[14,17],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執行,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雙方的合作意愿。但是,隨著市場化的沖擊,價格機制將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人情機制[12],理性的草場轉出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將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將草場流轉至出價高的牧戶;同時,隨著產權交易市場的完善、牧戶契約理念逐步樹立,以及政府草場流轉辦法的規制作用,傳統熟人交易依托的非正式制度的隱性保障逐漸被正式契約憑借的法律保障所替代,社會資本的作用被進一步削弱。
2.社會網絡擴充了信息來源但降低信息搜尋費用的作用被弱化,主動進行社會互動的作用更加凸顯。中國草場流轉市場發育不完善,存在較高的信息搜尋成本,供需雙方常常難以實現有效匹配,導致潛在流轉交易流產[7]。通常,牧戶社會網絡越豐富,其信息來源的覆蓋面越廣,了解到草場流轉的相關信息就越豐富,越易促進交易的達成[18-19]。同時,相對社會網絡匱乏的個體,社會網絡豐富的牧戶能夠更為低成本、高效率地向外界傳遞其轉入草場的交易信號,促進交易匹配。但是,隨著草原生態保護壓力的增大以及年輕牧戶群體的擴張,草場流轉市場的賣方特性愈發突出,牧戶對草場資源的競相獲取更加激烈,彼此間可能存在嚴重的信息隱匿情況,從而導致社會網絡的信息傳遞功能衰減。在信息隱匿的情況下,社會互動的作用更加凸顯。正如Lin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動中攝取或動員的資源”[20],社會資本的作用不僅依賴于社會網絡的大小,還取決于行動者如何利用。社會互動對于個體影響的重要機制之一是通過與周邊群體口頭信息交流,獲得并傳遞有利于個體決策和行動的關鍵信息[21]。社會互動頻率越高的牧戶,打破草場信息流轉障礙的可能性越大。其內在邏輯至少包含以下兩點:其一,“社會互動-面子效應-草場轉入”。市場化的沖擊雖不容忽視,但牧區仍然是一個熟人社會[18],面子觀念依舊在某種程度上發揮著非正式制度的約束作用[22]。在牧戶與周邊親友頻繁咨詢草場流轉信息情況下,礙于面子關系,對方仍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透露草場資源的獲取信息,從而有利于意愿轉入戶轉入草場。其二,“社會互動-信號傳遞-草場轉入”。頻繁互動既有利于牧戶提前獲悉周邊牧戶的草場轉出信息,在競爭市場占得先機,也有利于向周邊牧戶密集傳遞交易信號,并借助非競爭者擴大信號的傳播速率和距離,促進草場轉入實現。
3.擴大市場交易半徑的作用更加依賴于關鍵網絡節點。在通訊手段落后的情境下,通常社會網絡越豐富的牧戶,越有可能將草場流轉的交易半徑向外延展,從而擴充草場轉入來源,彌補村域草場流轉市場內供需錯配的缺陷,提高草場轉入幾率。然而,由于草場流轉主要發生在牧戶之間,交易對象的限制很可能導致牧戶間社會網絡的同質化,弱化社會網絡的作用。在上述情形下,關系網絡中一些重要的網絡節點可能發揮重要作用。網絡節點被認為是資源或利益的來源[23-24],是否擁有某些網絡節點可以反映牧戶社會網絡的異質性。一些關鍵網絡節點占據著結構洞的位置,聯通著重要的草場資源,尤其是村域外的關鍵節點,可以幫助部分牧戶捕獲他人難以獲取的草場信息或資源,實現供需匹配。但是,關鍵網絡節點與社會網絡規模并不對等,即使一些牧戶的社會網絡規模不大,也可能擁有部分關鍵節點。總體而言,隨著流轉市場的轉型,社會資本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正在弱化,但是仍然具有正向影響。
隨著草場流轉市場的轉型,網絡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產生影響逐漸成為可能,并對社會資本的部分作用形成替代。首先,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網絡信息渠道能夠通過降低信息費用,促進牧戶草場轉入[25]。相比于社會資本,網絡信息渠道在拓寬信息傳播范圍和提高信息傳播速率方面更具優勢,可以顯著降低草場轉入者的信息搜尋成本[26]。其次,網絡信息渠道有利于降低轉入者與轉出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轉出者通過網上草場流轉服務平臺發布草場流轉信息需要接受行政部門或交易平臺的監管,其對于交易信息的披露更加真實準確,提高了轉入者對草場資源的信心,有利于促進交易實現;轉入者同樣可以通過互聯網傳遞自身的交易信號,并向交易平臺提供準確的資質信息,降低轉出者對于交易風險的顧慮,從而提高自身轉入草場的成功率。最后,網絡信息渠道有利于延展牧戶草場流轉的交易半徑,拓寬草場流轉市場范圍。一方面,傳統草場流轉市場交易多發生在村域熟人內部,而互聯網使用使草場交易信息流動突破了傳統草場流轉市場的地域限制。理論上,當牧戶自身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本不受約束時,更大范圍內的交易信息獲取可以使牧戶參與到更為廣闊的草場流轉市場,在任意地理空間上實現草場轉入。另一方面,網絡信息渠道可以使草場流轉的價格更為公開透明,有助于草場流轉契約達成的同時實現流轉交易價格逐步市場化,從而打破草場流轉主要發生在熟人之間的局限性[25]。根據Dixit的研究,當熟人網絡中的主體獲得外部機會,傳統的人格化交易將被市場交易所取代[27]。需要考慮的是,雖然牧區信息化在過去一段時間快速發展,草場流轉網絡服務平臺也逐步建立,但是“互聯網+”草場流轉市場仍然處于起步階段,其作用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牧區網民基數及其網絡使用熟練程度。盡管年輕牧戶群體逐漸成長并成為畜牧業經營參與主體之一,但中老年牧戶仍然是畜牧業經營最主要的參與主體。因此,網絡信息渠道的作用可能初步顯現,其對社會資本的替代作用有限。
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1,社會資本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有正向影響;
H1-2,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有正向影響;
H1-3,信息渠道對社會資本存在弱替代效應。
H2-1,社會資本通過降低草場轉入的交易費用促進牧戶草場轉入;
H2-2,信息渠道通過降低草場轉入的交易費用促進牧戶草場轉入。
(二)代際差異對社會資本、信息渠道影響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調節作用
牧業經營主體的多個代際并存是草場流轉市場轉型的典型特征之一。與牧業經營主體多代際并存相對應的是,社會資本和網絡信息渠道均具有明顯的代際差異特征,這可能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產生差異化的影響。就社會資本而言,代際之間社會資本水平和結構均存在明顯區別。從水平上看,通常年長牧戶的社會資本積累更豐富,社會資本總量更大。從結構上看,新生代牧戶生于改革開放之后,處于牧區社會劇烈轉型時期,生活環境、成長經歷、價值觀念等均與年長牧民具有較大差異,其對于社會資本的建構與年長牧民不同[28]。新生代牧民多基于自身活動范圍和興趣愛好選擇性地構建社會網絡和人脈關系[9];同時,其在構建人脈關系時多以同齡人為主[29]。與之對應的是,草原承包到戶主要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多數80后牧戶未能趕上草場承包,因此新生代牧戶社會網絡中的同齡人同樣面臨草場缺乏的窘境,建構于此的社會資本對于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作用很可能弱于中老年牧戶。
就網絡信息渠道而言,年輕牧戶的互聯網使用更為普遍、熟練和深入。互聯網在20世紀90年代后進入中國,并在2010年后在中國農村加速普及。在互聯網普及的浪潮中,70后、80后和90后成為互聯網使用的主力軍。即便如此,70后在互聯網信息獲取、社會交往等多個網絡使用場景參與上全方面弱于80后和90后[30]。相較于城市和農區,牧區信息化建設更加滯后,中老年牧民接觸互聯網更晚;相對于新生代牧民而言,中老年牧民使用互聯網進行搜尋、獲取和傳遞信息的能力更弱,其作用效果也會大打折扣。由于社交習慣的差異,新老牧民對于社會資本和信息渠道的依賴程度也存在較大差異。此外,牧區網絡草場流轉服務平臺的建設始于2015年之后,建設周期尚短,進一步拉大了新老牧戶在網絡信息渠道使用上的頻率和熟練度差距,擴大了互聯網使用對草場轉入的效果差異。因此,網絡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很可能存在代際差異。
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1,社會資本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存在代際差異;
H3-2,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存在代際差異。
二、數據、變量與模型
(一)數據說明
本文研究數據源于課題組2020年8月、10月在內蒙古自治區和甘肅省牧區開展的入戶調查。內蒙古牧區和甘肅牧區均屬中國五大牧區之一,畜牧業正從傳統粗放型向現代集約型轉型,草場仍然是畜牧業發展的重要依賴。兩地樣本區均存在嚴重的超載過牧情況,草場流轉是牧戶實現草畜平衡和規模擴張的重要手段,流轉發生率較高,研究草場流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調查采取典型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式。首先,將調研區域劃分為典型草原區、荒漠化草原區和高寒草原區,并綜合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牧業生產規模、人均草場面積和區域人口密度,選取6個牧業旗(縣);其次,根據每個牧業鄉鎮政府距縣政府距離的遠近,隨機選取典型牧業鄉鎮;再次,根據村委會距離鄉鎮政府的遠近,隨機選取典型牧業村;最后,在每個村隨機選取受訪牧戶,并由調研員對家中主要畜牧業勞動力進行2~3小時面對面訪談,訪談內容主要包括牧戶家庭基本信息、草場流轉信息、草場經營情況以及畜牧業養殖情況等;同時,在每個村選取一名村干部面訪,獲取村級社會經濟信息。調查共在6個旗(縣)19個鄉鎮65個村完成牧戶訪談問卷857份,最終獲得符合本文研究的有效問卷820份,有效率為95.68%。有效樣本在三大草原類型的比例分別為32.93%、34.27%和32.80%,分布較為均衡。
從受訪者個體特征看:受訪對象主要為男性(74.51%)、少數民族(74.15%)和中老年牧戶(45歲以上占61.37%),受訪者受教育程度總體不高(初中及以下學歷占77.56%),受訪者特征與牧區當前現實情況較為符合,與褚力其等學者的調查情況類似[33]。從樣本牧戶特征看:牧戶家庭規模以3~6人為主(占比達到82.31%),家庭人口規模較小;2019年家庭純收入在20萬元以下的牧戶占樣本總數的63.42%,平均家庭純收入達到19.5萬元,總體收入較高。除樣本牧戶收入高于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外可能的原因是:統計公報中的收入數據包含了大量非牧戶,拉低了農牧戶人均純收入。本文中的家庭純收入核算中包括了長期在外打工的子女。畜牧業成本核算時,當年新增固定資產以折舊價值計算而非購買價格。,其他樣本特征均與政府統計年鑒相近。總體上,樣本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參照學界對土地流轉行為的界定,本文選取牧戶是否轉入草場來表征其草場轉入行為。當草場轉入面積大于0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2.核心解釋變量。(1)社會資本。基于Lin的社會資本定義,從個體的社會網絡資源和網絡資源利用能力兩方面衡量牧戶的社會資本,并將其表征為社會網絡和社會互動。參照Granovetter關于社會網絡中強連帶和弱連帶的劃分[32],以及國內外學者的社會網絡的測度方式[33-34],用“牧戶手機通訊錄中聯系人數量”測度牧戶關系網絡,分別用“牧戶經常走動的親戚數量”和“關系較好的朋友數量”來測度親緣網絡和友緣網絡;基于牧戶草場流轉的現實需要,通過詢問“牧戶是否在草原監管部門和農牧推廣部門有關系好的親友”來表征牧戶社會網絡中的關鍵網絡節點原因在于:在調研地區,草原監管部門和農牧推廣部門承擔了主要的草原監管和草原生態保護政策任務,同時匯集了縣域范圍內最為全面的牧戶承包草場情況和畜牧業經營情況,很可能為牧戶草場流轉提供關鍵信息。。個體與周邊人的社會交往頻率是現有研究用來表征社會互動的主要方式之一,結合草場流轉這一目標性活動,通過“牧戶與周邊親友交流有關草場流轉信息的頻率”來測度牧戶的社會互動。(2)信息渠道。本文的信息渠道是指網絡信息渠道,即牧戶是否通過使用互聯網來獲得草場流轉的相關信息,用“互聯網使用”來表征,并通過問卷中“牧戶是否通過互聯網開展與草場流轉相關的信息搜索、新聞瀏覽等活動”來測度。
3.中介變量與調節變量。參照羅必良等的研究,用“牧戶的交易費用感知”來表征交易費用[16]。具體的,按照牧戶通常的草場轉入流程,在事前信息搜尋、事中簽約以及事后監督違約等方面設置8個題項,并通過因子分析提取了3個公因子,分別命名為“事前交易費用”“事中交易費用”和“事后交易費用”(見表1)。統計檢驗顯示原始測量題目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參照國內新生代農民的主流劃分標準[35],將2020年戶主年齡小于等于40歲的牧戶群體定義為“新生代”牧戶,將戶主年齡大于40歲且小于等于60歲的牧民定義為“中生代”牧戶,并將年齡大于60歲的牧民定義為“老生代”牧戶。
4.控制變量。參照現有研究[8],本文還引入了草場稟賦、人力資本特征、牧業經營特征、家庭經濟特征以及村莊社會經濟特征、地區虛擬變量等一系列可能影響牧戶草場轉入的變量,從而降低核心解釋變量的內生性。草場稟賦包括承包草場面積、草場細碎化、草場質量、飼草料地面積和水資源可及性。通常,牧戶草場承包面積越大、草場質量越好、草場細碎化程度越低,其初始草場稟賦越好,對于額外轉入草場的需求就越小,轉入草場的概率就越小;飼草料地作為飼草料的另一主要來源,與轉入草場形成替代關系,飼草料地面積越大,牧戶轉入草場的概率就越小;水資源是制約草食畜牧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自家草場的水資源狀況影響養殖成本和牲畜存活,預期水資源可及性越好,牧戶轉入草場的概率就越小。人力資本特征包括牧戶家庭牧業勞動力數量、教育、健康和年齡。通常,牧業勞動力數量越多、勞動力健康狀況越好,牧戶轉入草場的概率就越大;而受教育水平和年齡對牧戶是否轉入草場以及轉入率的影響則不確定。牧業經營特征包括牧業收入比重、非牧就業率、年初存欄量和畜牧業固定資產。牧業收入比重越高,非牧就業率越低,牧戶對畜牧業依賴性越大,轉入草場的概率就越大;年初存欄量越大,牧戶草畜平衡壓力越大,轉入草場的概率就越大;牧業固定資產越大,牧戶越需要通過轉入草場實現要素匹配,改善規模收益,其轉入草場的概率就越大。家庭經濟特征包括家庭收入和家庭資產,收入越高、資產越多,牧戶的經濟實力越強,面臨的資金約束越小,轉入草場的概率就越高。村莊社會經濟特征包括村莊經濟水平、交通條件和可利用草原。村莊經濟水平和交通條件對于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不確定;村莊可利用草原面積占比越高,牧戶從本村轉入草場的可能性越大,其轉入草場的概率就越高。區域虛擬變量用以控制省際差異導致的牧戶草場轉入差異。
相關變量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三)模型介紹
牧戶是否轉入草場是一個二元選擇問題,采用二元Probit模型進行估計。將基準模型設定如下:
LZi=α0+α1SNi+α2SIi+α3Ii+βCi+γPi+εi(1)
其中,LZi為牧戶的草場轉入行為;SNi代表牧戶的社會網絡,具體包括關系網絡、親緣網絡、友緣網絡和關鍵網絡節點;SIi代表牧戶的社會互動;Ii代表網絡信息渠道,即互聯網使用;Ci代表可能影響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控制變量,Pi為區域虛擬變量,εi為隨機擾動項。α1、α2、α3、β、γ分別代表對應變量的回歸系數。
為了進一步揭示社會資本與信息渠道對于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是否存在互補或替代關系,在模型中加入社會資本與信息渠道的交互項,將模型設定如下:
LZi=α0+α1SNi+α2SIi+α3Ii+λ1SNi×Ii+λ2SIi×α3Ii+βCi+γPi+εi(2)
(2)式中,SNi×Ii和SIi×Ii分別為社會網絡與信息渠道的交互項、社會互動與信息渠道的交互項,λ1、λ2分別反映信息渠道與社會網絡、社會互動的關系。
基于草地流轉市場高交易費用的特征,為檢驗社會資本和信息渠道是否能夠通過影響草場流轉的交易費用進而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產生影響,設定如下中介效應分析模型:
TCi=α1SNi+α2SIi+α3Ii+β1Ci+γ1Pi+ε1i(3)
LZi=α′1SNi+α′2SIi+α′3Ii+bTCi+β2Ci+γ2Pi+ε2i(4)
(3)(4)式中,TCi代表交易費用,其他變量含義同上。參照已有研究[23-24],對交易費用的中介效應是否存在進行檢驗。此處不再贅述。
最后,通過分組回歸考察代際差異對社會資本、信息渠道影響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調節效應。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1.社會資本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表3中(1)~(3)列結果顯示,無論是反映牧戶整體社會網絡狀況的關系網絡,還是反映強連帶的親緣網絡和弱連帶的友緣網絡,均對牧戶是否轉入草場和草場轉入率沒有顯著影響,這與理論預期稍有不符。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傳統熟人關系網絡內的互惠、信任關系被經濟利益關系所取代,社會資本的非正式制度作用消散。草場流轉市場化進程中,即使是熟人間的交易也愈發遵循價格機制。對于草場轉出者而言,其草場轉出目標是家庭經濟利益最大化[12],轉出邏輯為一定范圍內的親友“價高者得”。其次,牧戶社會網絡的同質性。盡管牧戶的社會網絡規模存在差異,但草場流轉市場中的交易主要為牧戶間的交易,受交易半徑限制,一定區域草場流轉市場內潛在轉出者數量有限以及潛在轉入者間的關系網絡交叉重疊,導致牧戶的社會網絡趨于同質,弱化了個體網絡的資源獲取能力。最后,草場流轉市場可能存在信息隱匿。中國北方草場流轉市場的賣方市場特性決定了牧戶草場轉入面臨激烈市場競爭,理性牧戶在滿足自身草場轉入需求之前,并不會主動向其他牧戶傳遞草場供給信息,弱化了被動等待信息流入牧戶社會網絡的信息獲取能力。表3中第(4)列結果表明,關鍵網絡節點對牧戶是否轉入草場和草場轉入率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其邊際效應為相對于關鍵網絡節點為空的牧戶,擁有關鍵網絡節點使牧戶轉入草場的概率提高19.20%。這說明,在高度競爭的草場流轉市場,草場要素獲取有賴于牧戶在關鍵網絡節點的資源和信息獲取能力。以草原監管部門和農技推廣部門為基礎的關鍵網絡節點占據了結構洞位置,有可能拓展牧戶的交易半徑,從而在更大市場范圍內為牧戶匹配準確的交易信息或促成交易達成。進一步在模型中加入社會互動變量后,社會資本對于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如表3中第(5)列所示。結果表明,社會互動對于牧戶是否轉入草場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其邊際效應為:社會互動每提高一個單位,可以使牧戶轉入草場的概率提高5.97%。但是,加入社會互動變量后,關鍵網絡節點對于牧戶是否轉入草場的邊際影響下降,這說明社會互動對關鍵網絡節點具有一定替代作用。上述發現意味著,盡管社會網絡決定了牧戶潛在的草場資源獲取邊界,但由于賣方市場下牧戶間競爭獲取關系和信息壁壘的存在,能否轉入草場還受制于牧戶社會網絡資源的利用能力,即通過主動、頻繁就草場流轉進行互動,破除信息壁壘,進而獲得更多草場流轉信息,實現草場轉入。H1-1得到部分驗證。綜上,流轉市轉型中,社會資本對牧戶轉入草場的作用仍不容忽視,但其作用方式發生變化,并表現為:關鍵網絡節點作用凸顯,社會資本總量作用衰減;牧戶主動利用社會網絡能力的作用凸顯,被動依賴社會網絡信息資源流入的作用消弭。其積極意義在于:社會資本的稟賦依賴在一定程度上被能力依賴所替代。
2.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信息渠道對于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如表3中第(6)列所示。互聯網使用對于牧戶是否轉入草場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相對于不使用互聯網的牧戶,使用互聯網可以使牧戶草場轉入概率提高9.7%,即互聯網使用有利于牧戶實現草場轉入,從而促進牧業要素配置優化。上述結果表明,隨著草場流轉市場的發展和信息化建設,網絡信息渠道已經成為牧戶實現草場流轉的重要途徑之一,對于促成草場交易實現不可或缺。H1-2得到驗證。加入信息渠道后,社會互動和關鍵網絡節點對于牧戶是否轉入草場的影響未發生明顯變化。這意味著,草場流轉市場轉型過程中,網絡信息渠道作用初顯,且社會資本仍未失效,二者均對促進草場轉入有一定效果。從邊際效果上看,關鍵網絡節點影響最大,這意味著在賣方市場和交易信息尚不完善的情況下,網絡信息渠道對牧戶能否轉入草場的影響尚不如社會資本,牧戶實現草場轉入更加依賴于關鍵網絡節點。綜上,流轉市場轉型進程中,網絡信息渠道已經初見成效,但其作用仍然有限。可能的原因在于:中老年牧戶仍然是畜牧業經營的參與主體,牧民主導的草場流轉市場的網絡信息發布、更新等尚不及時;同時,政府主導的網絡交易平臺也尚未良好運行調研數據顯示,盡管部分試點地區已經建立“村-鎮-縣”三級草場流轉實體交易平臺和草場流轉網絡交易平臺,但是牧戶對于平臺的知曉程度和使用程度仍不高。。
3.信息渠道對社會資本的弱替代作用。表3中第(6)列結果顯示,加入互聯網使用變量后,社會互動、信息渠道對于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系數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因此,社會資本和信息渠道對于牧戶草場轉入行為很可能獨立發揮作用。為進一步檢驗社會資本、信息渠道在牧戶草場轉入中的關系,在表3第(6)列的基礎上,加入關鍵網絡節點與互聯網使用的交互項以及社會互動與互聯網使用的交互項,模型結果如表4所示。兩個交互項的系數均為負,與理論預期相符,即網絡信息渠道與社會資本間的關系為替代作用。但是,交互項系數都不顯著,這意味著在草場流轉市場轉型的現階段,社會資本與網絡信息渠道尚未產生顯著的替代作用,二者仍然獨立運行。H1-3得到部分驗證。
4.控制變量的影響。表3中第(6)列顯示,交易費用、承包草場面積、飼草料地面積、水資源可及性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有顯著負向影響,年初存欄量、畜牧業固定資產和村莊可利用草原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均與理論預期相符。這說明,草場資源稟賦和畜牧業經營狀況是牧戶轉入草場的主要驅動因素,交易費用是關鍵制約因素,這與Tan等的研究結論具有一致性[8,34]。
5.穩健性檢驗。(1)更換核心解釋變量。用“牧戶家庭是否有關系較好的親友在縣級及以上政府工作”測度關鍵網絡節點,通過“是否在與周邊親友的草場流轉交流中獲益”衡量社會互動,用“牧戶在網絡平臺獲取草場流轉相關供求信息的難度”表征互聯網使用,并分別在模型中替換上述核心解釋變量。變量更換后的估計結果顯示,社會資本與信息渠道對牧戶是否轉入草場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均未發生明顯變化。(2)考慮同一村域內的牧戶決策可能存在關聯性,將回歸標準誤聚類到村級以消除該影響模型結果與基準模型回歸結果一致,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依然顯著。(3)基于5 000次Bootstrap抽樣的經驗樣本進行重新估計。關鍵網絡節點、社會互動以及互聯網使用的真實估計系數均在經驗樣本估計系數的95%置信區間內,說明以上研究結果是穩健的。綜上,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是比較可靠的(篇幅所限未展示,感興趣可向作者索取)。
(二)交易費用的中介作用分析
1.結果與討論。從“關鍵網絡節點→交易費用→草場轉入”“社會互動→交易費用→草場轉入”“互聯網使用→交易費用→草場轉入”三條路徑驗證和討論社會資本和信息渠道是否通過降低交易費用促進牧戶草場轉入,結果如表5所示。
“關鍵網絡節點→交易費用→草場轉入”路徑不成立,且表現為關鍵網絡節點提升了草場流轉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交易費用,進而抑制了牧戶草場轉入行為,這與理論預期相悖。但從任意單一路徑上看,交易費用的負向中介作用均不足夠強,這可能與草場流轉市場特征和中國特殊的人際關系有關。首先,從交易費用的產生環節看,草場轉入的交易費用主要產生在事前信息搜尋環節和事中談判簽約環節;關鍵網絡節點對于牧戶草場轉入的作用更多體現為交易半徑的拓展,并非降低上述環節交易費用。同時,牧戶依托關鍵網絡節點聯結潛在草場轉出戶后,通常仍然需要節點成員作為中間人進行信息傳遞,有可能進一步增加事中交易費用。其次,從牧戶的人際關系特點來看,使用關鍵網絡節點類似于“求人辦事”,其實質是一種“人情債”。一般當牧戶自身能夠完成交易信息搜集時,并不會動用這一社會關系;一旦動用這一社會關系進行草場流轉交易,通常意味著其已經耗費了大量的信息搜尋成本,通過關鍵網絡節點獲取草場資源產生的任何費用都將成為額外的交易費用;即使牧戶從一開始就直接尋求關鍵網絡節點的幫助,“人情債”也使交易費用維持在較高的水平。最后,通過關鍵網絡節點達成的草場交易可能還會因為“殺熟”而增加交易費用。賣方市場特性決定草場轉出者擁有定價權,轉出者因為擔心草場被過度利用,會進一步將潛在交易風險內化到交易價格[6]。礙于中間人的“面子”問題,意愿轉入者不僅在討價還價上存在制約,還會擔心因為交易無法達成而損害中間人形象結果做出讓步和妥協,無形中增加了牧戶草場流轉的交易費用。“社會互動→交易費用→草場轉入”路徑成立,且表現為社會互動通過降低草場流轉的事前交易費用提高牧戶草場轉入概率,這與理論預期相符。但是,社會互動并未能通過降低事中交易費用和事后交易費用促進草場轉入,其主要原因在于社會互動的主要功能在于信息傳遞和信號釋放,在化解交易風險和減少簽約談判費用上的作用有限。H2-1得到部分驗證。
“互聯網使用→交易費用→草場轉入”路徑不成立,且主要表現為互聯網使用未能顯著降低草場轉入的事前交易費用和事中交易費用。可能原因在于:現階段草場流轉市場的線上信息發布平臺和交易平臺尚處于起步階段,交易信息發布、更新均存在一定的時滯性,增加了轉入戶搜尋潛在交易對象的難度;同時,草場流轉是牧戶間的雙向交易,任何一方網絡使用能力的欠缺都會增加交易難度,而現階段中老年牧戶仍是畜牧業經營的參與主體,其互聯網終使用能力有限,進一步增加了轉入方信息搜尋和談判、簽約的難度。H2-2未能驗證。
綜上,草場流轉市場轉型過程中,盡管社會資本和信息渠道均對牧戶草場轉入具有促進作用,但是交易費用并不是其作用生效的主要路徑。
2.穩健性檢驗。用總交易費用總交易費用=(事前交易費用×29.15%+事中交易費用×25.86%+事后交易費用×20.57%)/(29.15%+25.86%+20.57%)替代事前、事中和事后交易費用,對上述模型重新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社會互動→總交易費用→草場轉入”成立,即社會互動可以通過降低草場轉入的總交易費用進而促進牧戶草場轉入;“關鍵網絡節點→總交易費用→草場轉入”也成立,說明在事前、事中以及事后交易費用的疊加下,關鍵網絡節點的使用增加了牧戶草場流轉的總交易費用,進而抑制了牧戶的草場轉入。“互聯網使用→總交易費用→草場轉入”仍不成立。總體上,上述結果是比較穩健的。
(三)代際差異的調節作用分析
1.社會資本與信息渠道的代際差異。表6顯示,新生代牧戶占比略高于老生代牧戶,但比重均較小;中生代牧戶仍然是畜牧業經營的參與主體,占比接近新生代與老生代牧戶之和的2倍。從社會資本的代際差異上看,中生代牧戶關鍵網絡節點非空的牧戶占比最高,且與老生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中生代牧戶的社會互動頻率最高,且與新生代和老生代之間均有顯著差異。從信息渠道的代際差異上看,老生代牧戶的互聯網使用比例最低,且與新生代和中生代之間均有顯著差異。綜上,社會資本與信息渠道在代際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初步說明在草場流轉市場上,牧戶草場轉入憑借的信息和資源獲取方式可能存在一定差異。
2.代際差異的調節作用。表7中組間系數差異檢驗顯示,社會資本、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關鍵網絡節點對于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促進作用表現為老生代>中生代,社會互動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的代際差異雖不顯著,但也呈現出中生代>老生代>新生代的趨勢,互聯網使用對于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促進作用表現為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圖1顯示,關鍵網絡節點、社會互動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分別隨代際上升呈“U”型和倒“U”型,互聯網使用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隨代際上升呈持續下降趨勢。H3-1、H3-2得到驗證。
就新生代牧戶而言,關鍵網絡節點、互聯網使用對其轉入草場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邊際效應分別為相對于關鍵網絡節點為空的牧戶,擁有關鍵網絡節點可以使其草場轉入概率提高30.47%,相對于不使用互聯網搜集信息的牧戶,使用互聯網搜集信息的牧戶草場轉入概率提高51.52%;而社會互動的影響則不顯著。就中生代牧戶而言,社會互動對其轉入草場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邊際效應為社會互動頻率每提高一個單位,牧戶草場轉入概率提高6.05%;而關鍵網絡節點和互聯網使用的影響不顯著。就老生代牧戶而言,關鍵網絡節點和社會互動對其草場轉入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邊際效應分別為相對于關鍵網絡節點為空的牧戶,擁有關鍵網絡節點使牧戶草場轉入概率提高65.65%,社會互動頻率每提高一個單位,牧戶草場轉入概率提高4.83%,互聯網使用的影響則不顯著。上述結果意味著,社會資本有助于新生代牧戶轉入草場,但作用較為微弱,互聯網使用是其實現草場轉入、提高草場轉入率的關鍵;而中生代、老生代牧戶轉入草場僅憑借社會資本。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圈子”差異。社會互動具有選擇性,新生代牧戶多基于共同興趣愛好或與年齡相仿的個體構建起關系網絡并進行互動;然而,網絡中的個體同樣面臨缺乏草場的窘境,難以直接通過與同齡人的互動轉入草場或者獲得豐富的草場流轉信息。相反,中生代和老生代的社會互動更為高效,中生代作為最主要的牧業經營參與主體,承上啟下,互動范圍最廣,同時與其進行互動的群體相對新生代而言,擁有更好的草場資源稟賦,了解的草場市場信息也更為充分;老生代牧戶更習慣于口頭信息交流,其互動對象也以中生代和老生代牧戶為主,互動對象不但掌握更多的草場要素,且更易因勞動力不足、疾病等原因轉出草場;同時,老生代牧戶的活動能力和交易范圍受自身人力資本約束更強,對關鍵網絡節點的作用也更為倚賴。第二,網絡使用能力差異。新生代牧戶相對于中生代和老生代,具有較強的互聯網信息搜索和在線社交能力,網絡利用效率更高。相對于未使用互聯網進行草場流轉信息搜集的牧戶,使用互聯網搜集信息拓寬了牧戶的信息來源渠道,豐富了草場流轉交易信息,同時進行網絡社交加快了交易信息的傳遞,有利于提高其草場轉入概率。
3.敏感性分析。現有文獻對年輕勞動者的定義并不一致,而代際劃分的不同可能會對估計結果產生影響。為此,以國際勞工組織對年輕勞動者的定義為上限,將新生代界定年齡限定為40~45歲進行敏感性分析。總體上,社會互動、互聯網使用的影響對新生代界定年齡并不敏感。關鍵網絡節點的影響對新生代的界定年齡相對敏感(敏感值為40歲和45歲),但影響微弱,體現為影響系數變化較小且方向不變。綜上,采用40歲界定新生代牧戶比較合理。一方面,新生代界定年齡的改變并未使社會資本和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產生根本變化,研究結論比較穩健;另一方面,以40歲界定新生代,代表了80后牧戶群體,能更好地反映牧業經營主體的更新換代,研究結果更加精準地揭示了年輕牧戶的草場流轉特征和現實需求,對于草場流轉政策的調整和流轉市場的完善更具借鑒意義(篇幅所限未展示,感興趣可向作者索取)。
四、結論與建議
中國北方草場流轉市場正處于從傳統以熟人交易為特征的“關系型”市場向以陌生人交易為特征的“要素型”市場過渡的轉型期,并表現為高交易費用和賣方市場特征,制約了牧戶草場轉入,如何提高牧戶草場轉入效率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利用2020年在內蒙古和甘肅兩省區牧區的820戶牧戶調查數據,實證檢驗了社會資本、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以及二者間的作用關系,并深入探討了交易費用的中介效應和代際差異的調節效應。結果表明:(1)轉型市場下,社會資本仍能促進牧戶草場轉入,但作用方式發生變化,表現為關鍵網絡節點和牧戶主動利用社會網絡能力的作用凸顯,社會資本總量和被動依賴社會網絡信息資源流入的作用衰減。(2)網絡信息渠道促進了牧戶草場轉入,但尚未對社會資本的作用形成替代,社會資本與網絡信息渠道并行不悖。(3)社會資本中,社會互動通過降低草場流轉的交易費用促進了牧戶草場轉入,而關鍵網絡節點的使用可能增加了交易費用而對草場轉入形成抑制;網絡信息渠道則未能通過降低交易費用促進牧戶草場轉入。(4)社會資本和信息渠道對牧戶草場轉入行為的影響存在顯著代際差異,并表現為新生代牧戶轉入草場更加依賴網絡信息渠道,中生代、老生代牧戶轉入草場僅依賴社會資本。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認為提高牧戶草場轉入效率應該重點關注以下三點:(1)現階段中老年牧戶仍是最主要的牧業經營參與主體。網絡信息渠道尚未健全,應該注重強化牧戶社會網絡的主動利用能力。一方面,通過完善牧區基層群眾組織,豐富牧民的集體性文化娛樂活動等,為牧戶開展更為廣泛的信息交流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加快建立草場流轉實體交易平臺,落實“村-鎮-縣”三級草場流轉交易體系,為牧戶草場轉入信息咨詢和交易簽約提供便捷場所。(2)加快建立和完善草場流轉市場網絡信息服務和交易平臺。通過微信公眾號、手機APP、交易網站等多種形式,破解供需信息不匹配難題,并通過線上線下同步,即時更新市場信息,降低牧戶草場轉入的信息搜尋費用和簽約談判費用。(3)建立“互聯網+”草場流轉市場是大勢所趨。隨著牧業經營參與主體的更新換代,在牧區信息化逐漸完善和牧區地廣人稀的居住格局條件下,線上交流和交易將成為牧戶獲取草場流轉信息和完成草場流轉交易的主要渠道,線上互動和信息挖掘能力將決定牧戶是否能在競爭性市場上搶占先機和改善草場轉入效率。加強對牧戶電腦、智能手機等網絡終端使用能力的培育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譚仲春,譚淑豪.草地流轉與牧戶效率:“能人”效應還是“資源平衡”效應?[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28(03):76-85.
[2]胡振通,孔德帥,焦金壽,等.草場流轉的生態環境效率——基于內蒙古甘肅兩省份的實證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4,35(06):90-97.
[3]李先東,李錄堂,蘇嵐嵐,等.牧民草場流轉的收入效應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9(11):104-115.
[4]李先東,李錄堂.社會保障、社會信任與牧民草場生態保護[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03):132-141.
[5]劉博,譚淑豪.社會資本與牧戶草地租賃傾向[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8,32(04):13-18.
[6]劉博,譚淑豪.信息不對稱視角下的交易主體選擇與牧戶草地租賃行為[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7,38(06):194-200.
[7]郜亮亮.中國農戶在農地流轉市場上能否如愿以償?——流轉市場的交易成本考察[J].中國農村經濟,2020(03):78-96.
[8]TAN S,LIU B,ZHANG Q,et al.Understanding Grassland Rental Market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Pr China[J].Land Use Policy,2017,67:733-741.
[9]劉博,譚淑豪.社會資本與年輕牧民草地租賃行為[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9,33(06):46-54.
[10]羅必良,李尚蒲.農地流轉的交易費用:威廉姆森分析范式及廣東的證據[J].農業經濟問題,2010,31(12):30-40.
[11]仇童偉,羅必良,何勤英.農地產權穩定與農地流轉市場轉型——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的證據[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20(02):133-145.
[12]仇童偉,羅必良,何勤英.農地流轉市場轉型:理論與證據——基于對農地流轉對象與農地租金關系的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19(04):128-144.
[13]王曉毅.市場化、干旱與草原保護政策對牧民生計的影響——2000-2010年內蒙古牧區的經驗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16,127(01):86-93.
[14]錢龍,洪名勇,龔麗娟,等.差序格局、利益取向與農戶土地流轉契約選擇[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12):95-104.
[15]LIN N.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J].Connections,1999,22(01):28-51.
[16]羅必良,汪沙,李尚蒲.交易費用、農戶認知與農地流轉——來自廣東省的農戶問卷調查[J].農業技術經濟,2012(01):11-21.
[17]洪名勇,龔麗娟.農地流轉口頭契約自我履約機制的實證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5,36(08):13-20.
[18]陳浩,王佳.社會資本能促進土地流轉嗎?——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研究[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6(01):21-29.
[19]楊衛忠.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中的農戶羊群行為——來自浙江省嘉興市農戶的調查數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5,362(02):38-51.
[20] LIN 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4.
[21]郭士祺,梁平漢.社會互動、信息渠道與家庭股市參與——基于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14,49(01):116-131.
[22]唐林,羅小鋒,張俊飚.社會監督、群體認同與農戶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行為——基于面子觀念的中介和調節作用[J].中國農村觀察,2019(02):18-33.
[23]黃敏學,王琦緣,肖邦明,等.消費咨詢網絡中意見領袖的演化機制研究——預期線索與網絡結構[J].管理世界,2015(07):109-121.
[24]BALA V,GOYAL S.A Noncooperative Model of Network Formation[J].Econometrica,2000,68(05):1181-1229.
[25]張景娜,張雪凱.互聯網使用對農地轉出決策的影響及機制研究——來自CFPS的微觀證據[J].中國農村經濟,2020(03):57-77.
[26]AKER J C,GHOSH I,BURRELL J.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LCT for Agriculture Initiatives[J].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6,47(01):35-48.
[27]DIXIT A K.Lawless and Economics: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59-96.
[28]LYONS S,KURON L.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14,35(S1):139-157.
[29]董小蘋.尋找朋友、選擇友誼與青少年的社會化(上)——兼論中、日、美三國中學生的擇友取向[J].當代青年研究,1993(05):27-30.
[30]趙聯飛.70后、80后、90后網絡參與行為的代際差異[J].中國青年研究,2019(02):65-72.
[31]褚力其,姜志德,王建浩.牧民草畜平衡維護的影響機制研究:認知局限與情感依賴[J].中國農村經濟,2020(06):95-114.
[32]GRANOVETTER 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06):1360-1380.
[33]KNIGHT J,YUEH L.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China[J].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08,16(03):389-414.
[34]蔡起華,朱玉春.關系網絡對農戶參與村莊集體行動的影響——以農戶參與小型農田水利建設投資為例[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7(01):108-118.
[35]錢文榮,李寶值.初衷達成度、公平感知度對農民工留城意愿的影響及其代際差異——基于長江三角洲16城市的調研數據[J].管理世界,2013(09):89-101.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Channel on Herders’ Grassland Renting-in
Behavior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land Renting MarketSHI Yuxing,ZHAO Minj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Aamp;F University,Yangling,Shannxi712100,China)Abstract: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assland renting market,this study used the survey data of 820 herders in Inner Mongolia and Gansu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 on herders’ grassland renting-in behavi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The results show that:(1) Social capital can still promote grassland renting-in behavior of herders, but its mode of action has changed.The role of key network nodes and herdsmen’s active use of social network capacity is highlighted,while the role of the total amount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passive inflow of social network information is reduced.(2)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 has promoted the renting-in behavior of herders,but it has not yet replaced the social capital,and th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 operate independently.(3) Social interaction promotes the grassland renting-in of herders by reducing the transaction cost,while key network nodes and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 do not.(4)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 on grassland renting-in behavior of herders.The new generation herders renting-in grassland rely more on internet information channels,while the middle generation and old generation herders renting-in grassland only rely on social capital.Accordingly,we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social capital;information channel;grassland renting-in;transaction costs;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責任編輯:張潔)
收稿日期:2021-04-13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1.13
基金項目: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軟科學項目(2019131039);農業農村部、財政部重點專項(CARS-07-F-1);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生科技創新項目(JGYJSCXXM202101)
作者簡介:史雨星,男,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資源經濟與環境管理。
*通信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