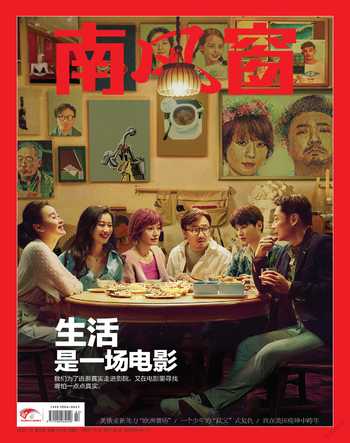直播電商從風(fēng)光到失色
胡泳
薇婭被罰、被封事件,輿論焦點在偷逃稅上。不過我更關(guān)心的是,這起事件對直播電商行業(yè)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在薇婭倒下之前,另一名頭部主播雪梨同樣因稅務(wù)問題“坍塌”,異軍突起成為電商新增長點的直播帶貨,會因這些超級主播的離場產(chǎn)生何種鏈式反應(yīng)?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幾乎能在家里的沙發(fā)上從事一切,購物當(dāng)然也不例外。直播電商看上去像是我們集體未來的一個愿景。這一模式本來算是中國電子商務(wù)的重大創(chuàng)新之一,源自幾種技術(shù)-社會趨勢的自然融合—流媒體、網(wǎng)紅、社交、智能手機、在線支付、物流—為消費品公司提供了一條通往消費者內(nèi)心和錢包的新途徑。
2020年,直播帶貨在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刺激下爆發(fā)式發(fā)展,幾乎成為各大平臺的標配。2021年雙十一,李佳琦、薇婭一天交易額達到近200億元,如此的繁榮表明直播電商可以成為消費者的一種深層習(xí)慣和零售商的一個重要工具。對于生產(chǎn)商來說,直播帶火了一部分新消費品牌,也有許多創(chuàng)業(yè)階段的新消費品牌打算從直播突破,認為這可以是一條捷徑。老的品牌商也發(fā)現(xiàn),消費者過去在從認識、到發(fā)生興趣、到購買、再到最后形成忠誠度的道路上走得很慢。但與頂級直播公司合作,這個過程則會縮短。
消費者何以對此趨之若鶩?一個是FOMO(錯失恐懼癥)的心理作用讓其不斷回到直播間:“如果有什么好東西別人搶到了而我卻沒有得到,真是個損失。”主播刻意利用買主對稀缺性的感知,直播時間短,而且多人同時在線,由于很多其他觀眾可能是潛在買家,人們感到更加緊迫。這種心理壓力可以促使人們快速行動,從而導(dǎo)致沖動購買。
其次,在購物的同時,中國消費者也一直在尋找娛樂、信息、真實性、情感和個性化。互動的購物體驗完全符合中國消費者的在線行為和社會偏好。薇婭的現(xiàn)場在線購物盛會,可以看作一種奇特的混合體:部分是綜藝節(jié)目,部分是信息廣告,部分是群體聊天。而且,在娛樂和購買之間不存在任何摩擦,這就是直播帶貨的重點所在。
再次,中國消費者永遠是價格敏感群體。直播帶貨的利器就是“全網(wǎng)最低價”。低到什么程度?比官方旗艦店、廠家直銷還要低。為什么可以這么低?因為頭部網(wǎng)紅擁有超大流量。直播電商實際上是一門流量生意,這從刷單成為直播帶貨界標配就可以看出。在流量邏輯下,部分主播作為平臺捧起來的“紅人”有綁架商家的嫌疑,甚至平臺也得讓三分。
然而,這樣的生意模式也埋下巨大的隱患:直播電商只有最低價和最大曝光量。從某種程度上講,獨家價格、獨家活動全網(wǎng)最低價,成為一種變相二選一;為獲取更高的坑位費和傭金比例,雇人刷單,逼品牌打價格戰(zhàn),成為一種變相的壟斷。
這樣下來,直播電商頭部主播的規(guī)范,終于成了眼下力度甚猛的平臺經(jīng)濟監(jiān)管的一部分。薇婭事件標志著直播電商的“野蠻生長”期結(jié)束了。此事有若干可見的影響:最直觀的就是直播的整體交易量肯定會下降,幾個頭部主播被封,缺口很難被重新填上。其次,稅的認定會影響主播的商業(yè)模式,接下來必然影響利益鏈條上每個利益方的商業(yè)模式。直播電商作為新興產(chǎn)業(y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了。再次,電商平臺會發(fā)現(xiàn),頭部越集中,風(fēng)險越大,在商業(yè)策略、流量分配等各個方面,需要重新認真思考平臺生態(tài)如何搭建。無論如何,直播電商從風(fēng)光走向失色,再次證明了互聯(lián)網(wǎng)行至今日,必然遵循的“冪律”鐵律:網(wǎng)絡(luò)以平等和民主化開局,但給世人留下的,幾乎總是馬太效應(y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