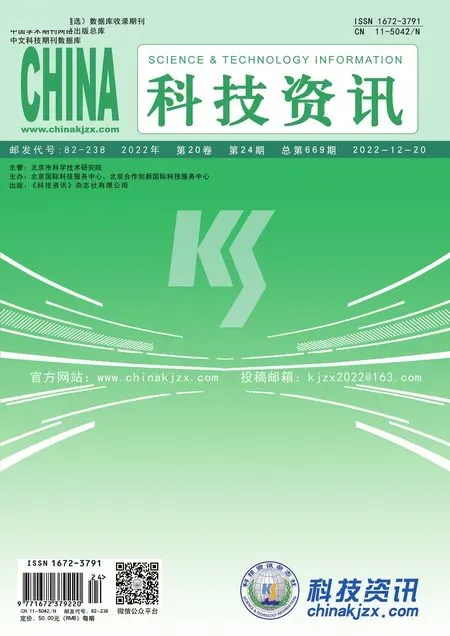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研究綜述
游弘正 孫嶠 呂苒
(大連大學建筑工程學院 遼寧大連 116000)
近年來,隨著我國“建筑工業(yè)化”發(fā)展方向的確立,裝配式建筑因其節(jié)能環(huán)保、施工效率高等優(yōu)勢而受到大力推廣。目前,我國裝配式建筑仍處于發(fā)展的初級階段,因施工技術和管理規(guī)范等不成熟問題,導致裝配式建筑在生產(chǎn)、運輸及施工階段存在比傳統(tǒng)現(xiàn)澆式建筑施工過程中更多的安全隱患[1],大量安全風險導致的安全事故阻礙了裝配式建筑在我國的推廣與發(fā)展。因此,有效識別裝配式建筑生產(chǎn)作業(yè)全過程中的安全風險并對其進行管控,已成為行業(yè)發(fā)展和學術研究的關注熱點。對該問題的深入研究,將有助于規(guī)避裝配式建筑生產(chǎn)作業(yè)全過程中安全事故的發(fā)生,有利于更好地推動裝配式建筑的發(fā)展。
雖然部分學者已經(jīng)從裝配式建筑領域進行了成果綜述[2],但針對其細分領域下的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的綜述成果相對較少。由于裝配式建筑存在多空間分布作業(yè)等特性,使其安全風險的評價與傳統(tǒng)建筑相比難度更大,需要對裝配式建筑安全與風險問題的研究進行獨立整合。經(jīng)過對近百篇中外文獻的比較閱讀可以發(fā)現(xiàn),國外裝配式建筑安全的研究起步較早且已經(jīng)將信息技術(物聯(lián)網(wǎng)技術、VR技術等)結合到風險評價中[3-4]。我國此類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該文首先在對國內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研究文獻進行比較閱讀的基礎上,按研究思路的不同,將相關文獻分為基于理論模型的安全風險評價體系構建、基于信息技術的安全風險管控兩類。隨后,再按時間順序對兩類研究的發(fā)展歷程、主要成果及特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最后,結合行業(yè)發(fā)展現(xiàn)狀對未來研究發(fā)展方向提出了展望,在豐富了基礎性研究的同時,旨在推動我國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研究的發(fā)展。
1 我國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研究現(xiàn)狀
從研究思路不同的角度出發(fā),現(xiàn)階段我國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研究可分為兩類:一是基于理論模型的安全風險評價體系構建;二是基于信息技術的安全風險管控。第一類研究在通過不同的理論模型識別出安全風險因素的基礎上,利用數(shù)學模型定量分析各安全風險因素的權重,構建裝配式建筑安全評價體系,進而為裝配式建筑的安全風險評價提供決策依據(jù)。第二類研究將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BIM、物聯(lián)網(wǎng)等)與裝配式建筑相結合,依據(jù)信息技術自身的特點(實時性、模擬仿真等),智能化的對裝配式建筑潛在安全風險進行預警。在預警評價的基礎上,通過智能分析提供安全風險管控辦法,在提高安全風險評價與管控效率的同時,有效避免了主觀人為因素對安全風險評價與管控有效性的影響。
1.1 基于理論模型的安全風險評價體系構建
國內裝配式建筑的發(fā)展起步遠落后于歐美發(fā)達國家,對其安全風險評價的研究開始時間也相對較晚,此類研究主要基于不同的數(shù)學或管理科學理論模型,構建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體系。我國對于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體系的研究大致起步于2015年,文敏等人[5]在現(xiàn)澆式建筑與裝配式建筑的對比分析中,初步探求了裝配式建筑安全事故的類型及其成因。楊爽[6]則較為系統(tǒng)、全面地選取了相關安全風險影響因素,運用粗糙集理論建立了裝配式建筑施工安全風險評價體系(以下簡稱“評價體系”)。在此之后,不同的學者開始嘗試基于不同的理論模型構建評價體系,風險分析也逐步從主觀定性分析發(fā)展為主客觀相結合的定量分析;從單一的施工階段安全風險分析發(fā)展為多階段安全風險聯(lián)動分析。李穎等人[7]在2016年利用事故樹和層次分析法,對裝配式建筑施工安全風險進行了定量分析,通過對不同評分的安全風險進行分級管控,有效保證了裝配式建筑項目的安全性。管理學中的經(jīng)典模型灰色聚類評價、系統(tǒng)動力學等也被應用到評價體系構建中,并利用主客觀相結合的方法,定量分析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因素[8-9],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安全風險評價的量化程度,但仍無法完全規(guī)避研究中主觀影響的問題。于是,2017年,李英攀等人[10]在層次分析法和熵權法計算指標權重的基礎上,運用云模型理論對裝配式建筑安全績效進行評價,實現(xiàn)了定性概念與定量數(shù)值間的不確定性轉化,較好地改進了系統(tǒng)動力學、灰色聚類分析等方法在安全風險評價過程中的主觀量化問題,并對安全風險因素間的模糊性與隨機性問題進行了探討。此后評級體系構建中的理論模型多采用能夠實現(xiàn)安全風險量化的模型為基礎,通過“風險量化”提高評價體系的客觀性,為裝配式建筑安全施工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jù)[11-17]。除此之外,部分學者嘗試將風險量化評價與其他項目管理因素(如成本控制、進度控制)相關聯(lián),以期更好地輔助裝配式建筑施工安全風險決策。2019 年,吳溪等人[18]利用馬爾科夫鏈和貝葉斯網(wǎng)絡相結合的方法對風險因素的發(fā)生概率進行了估計,以條件概率描述各風險因素之間相關性的同時,提供安全風險控制投入成本的配置策略,提高了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決策的全面性。與之相似,陳偉等人[19]運用敏感性分析及多目標規(guī)劃方法構建SD-MOP 模型,有效地解決了安全、進度、成本等多目標動態(tài)均衡優(yōu)化的難題,從多維度角度優(yōu)化了評價體系,并提出評價體系中可能存在多空間耦合影響問題。隨后,多空間耦合影響成為了裝配式建筑評價體系研究的熱點問題,學者們選取了更為適合的理論模型開展不同階段安全風險因素的聯(lián)動分析。陳偉等人[20]利用DEMATEL-BN 模型構建了裝配式建筑的安全風險傳導模型,得出了安全風險因素在裝配式建筑生產(chǎn)、運輸和施工空間中的傳導路徑,使得安全風險因素的確立從簡單的4M1E(人機料法環(huán))提升到了更為客觀、有效的多空間維度。此時,對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因素的分析似乎已經(jīng)較為全面,但由于裝配式建筑的設計比傳統(tǒng)建筑設計更復雜,致使其評價體系除了考慮各因素間的關聯(lián)性和多維度疊加性對施工階段的影響之外,還應考慮設計階段等對安全風險的關聯(lián)影響。2019 年,高欣[1]等首次從設計—施工兩階段協(xié)調的角度對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因素進行了分析,提出聯(lián)動管控措施方案。2020 年,陳為公等人[21]基于霍爾三維結構,從項目全壽命周期(決策、設計、生產(chǎn)運輸、施工、運營維護)的角度識別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因素,建立一種考慮脆弱性的評價體系。
表1 總結了“基于理論模型的安全風險評價體系構建”類研究常用的理論模型及其作用和特點。研究方法上,此類研究呈現(xiàn)從定性到定量、從單因素到多空間耦合、從單一施工階段到全壽命周期的發(fā)展趨勢,未來可能在多空間耦合和設計—施工階段聯(lián)動分析方面存在突破空間。盡管此類研究常選取不同的理論模型和分析角度,但研究的最終目標均為構建安全風險評價體系。安全風險評價體系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規(guī)避裝配式建筑生產(chǎn)作業(yè)的風險,但其風險防范措施在實施過程中易受主觀人為因素的影響,易造成安全風險防范效果不佳的情況。

表1 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體系研究常用理論模型
1.2 基于信息技術的安全風險管控
隨著近幾年國家住建部對建筑產(chǎn)業(yè)數(shù)字信息化的推動[22],以及裝配式建筑自身生產(chǎn)模塊化、管理信息化等特點,裝配式建筑的學術研究中開始出現(xiàn)信息技術(BIM、物聯(lián)網(wǎng)等)的身影[23]。2014 年,齊寶庫等人[24]提出運用GIS、Revit三維建模、施工進度管理平臺等BIM技術對裝配式建筑建造的全壽命周期進行安全、進度等多維度的評價與管控。同樣在2014 年,郭紅玲等人[25]提出一種基于RFID(射頻識別技術)和BIM 技術相結合的方式,充分運用信息傳輸技術,對裝配式施工現(xiàn)場進行精細的人員安全評價與管控。2018 年,苗震[26]對RFID技術的應用場景進行深化,將其運用到基坑施工安全及吊裝安全評價與管控等方面,進一步凸顯了RFID 技術在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與管控中的廣泛應用前景。2019年,鄒小偉等人[27]基于RFID技術和網(wǎng)絡通信技術,提出裝配式建筑施工作業(yè)現(xiàn)場的安全預警平臺的建立方法,能更快速、準確地對裝配式建筑施工中的潛在危險進行預報,有效減少安全事故的發(fā)生。隨著物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不斷發(fā)展,更多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不斷地被應用到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與管控中。2018 年,李英攀等人[28]利用云計算的高速存儲和數(shù)據(jù)分析能力,克服了BIM 技術關聯(lián)性不強的弊端,提出了基于Could-BIM 和UWB(超寬帶技術)的施工現(xiàn)場智能安全系統(tǒng),能夠實現(xiàn)場地分析、危險預警等功能,有效的降低了裝配式建筑施工現(xiàn)場的安全風險概率。2020 年,李強年等人[29]針對最易發(fā)生安全事故的裝配式建筑施工的吊裝環(huán)節(jié),應用可以長距離傳輸高信息量且低耗能的NB-IoT物聯(lián)網(wǎng)技術,對裝配式建筑吊裝過程進行了基于信息技術的安全風險評價與管控,降低了資源消耗,提高了智慧管理能力。2021年,劉占省等人[30]將較為前沿的數(shù)字孿生技術引用到裝配式建筑施工階段,通過虛實交互建模等手段,對吊裝階段的安全風險進行評價與管控,為數(shù)字孿生技術在裝配式建筑領域的應用奠定了基礎,也為裝配式建筑從信息化到智能化的發(fā)展做出了可行性的嘗試。
綜上所述,新興的信息技術在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與管控中的應用多集中在現(xiàn)場施工階段。以RFID(射頻識別技術)為代表的物聯(lián)網(wǎng)技術讓裝配式建筑精細化施工成為可能,同時也大大降低了主觀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安全風險。數(shù)字孿生安全模型的提出,描繪了未來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智能化評價與管控的發(fā)展方向。由于現(xiàn)階段我國裝配式建筑行業(yè)規(guī)范仍不夠完善,裝配式建筑項目信息化程度不夠高(僅占行業(yè)總產(chǎn)值的0.08%),信息技術尚缺乏廣泛的使用場景,短期內理論研究成果難以行業(yè)實踐有效對接。隨著住建部《“十四五”建筑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對裝配式建筑發(fā)展信息化發(fā)展的大力支持,相信未來會有更多信息技術應用于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與管控中,為其提供更精準有效的解決方案。
2 研究建議
通過對以上兩類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研究方向的介紹可以看出,第一種研究方法,也即我國對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研究以來較早出現(xiàn)、研究成果較多的方法,側重運用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等理論模型方法理論建立安全評價體系,以理論研究、方法和經(jīng)驗總結為主,缺乏可持續(xù)創(chuàng)新性;第二類與新興信息技術相結合的研究方向側重于高新技術的實際應用,能給裝配式安全風險評價與管控帶來更多突破性的創(chuàng)新方法,因此筆者認為,后者將是未來相關領域研究的主要方向。
然而,我國裝配式建筑的發(fā)展仍存在著諸多制約因素,同時也對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的研究與應用造成了不小的挑戰(zhàn)。常見的主要制約因素有技術因素、成本因素以及政策規(guī)范因素[31]。結合以上制約因素和理論研究現(xiàn)狀,筆者人認為可以通過以下手段支持我國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
(1)以政策規(guī)范為主要方式,推動裝配式建筑設計施工一體化。《“十四五”建筑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中明確指出,“要構建裝配式建筑標準化設計和生產(chǎn)體系,并推動生產(chǎn)和施工智能化的升級”。而行業(yè)現(xiàn)狀是,本該具備生產(chǎn)工業(yè)化、組裝高效化等特點的裝配式建筑施工卻存在著比現(xiàn)澆的施工方法更多的安全隱患。真正的原因還是在于我國缺乏有關裝配式建筑的技術指導和認定標準,使裝配式建筑設計構件缺乏標準化,相應地帶來運輸、組裝、堆放上的困難以及相應產(chǎn)生的安全風險。而上文提到的“安全評價體系建設”研究的系列成果,恰好能為裝配式建筑的設計與施工提供規(guī)范性的參考,推行采納后將能有效地控制裝配式建筑的安全風險,也能更好地幫助裝配式建筑的推行。
(2)經(jīng)濟補貼與市場激勵相結合,提升行業(yè)信息化評價與管控水平。隨著5G、物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發(fā)展以及BIM 技術廣泛的應用,運用信息技術進行裝配式建筑的安全風險評價與管控已成為大勢所趨。在2020 年住建部印發(fā)《關于推動智能建造與建筑工業(yè)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指導意見》之后,雖然已經(jīng)有一些裝配式建筑企業(yè)積極響應政策,已實現(xiàn)局域網(wǎng)的建立,在企業(yè)內部實現(xiàn)了數(shù)據(jù)資源共享,但對信息化技術資金投入缺乏進一步信心的背景下,安全風險評價與管控所需的更大范圍的信息流通與交互還不能實現(xiàn)。所以,需要政府給予一定的經(jīng)濟補貼。在前期,由政府財政給予技術研發(fā)或房貸補貼的支持,能夠在發(fā)展初期提升企業(yè)增加技術研發(fā)投入的積極性[31],更好地建設行業(yè)的信息化管理水平,使得基于信息技術的裝配式建筑的安全評價與管控能夠早日應用在實際工程中。
3 結語
我國的裝配式建筑行業(yè)由于各種因素限制,仍處于發(fā)展初期,而其安全風險評價難題又進一步阻礙了裝配式建筑的推廣與發(fā)展。該文對國內近10 年來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的研究理論進行梳理總結,將主要的研究方向分為“基于理論模型的安全風險評價體系”與“基于信息技術的安全風險管控”兩類,并通過對相關文獻和政策的分析,提出了以政府政策規(guī)范和補貼激勵相結合的促進裝配式建筑安全風險評價研究落地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