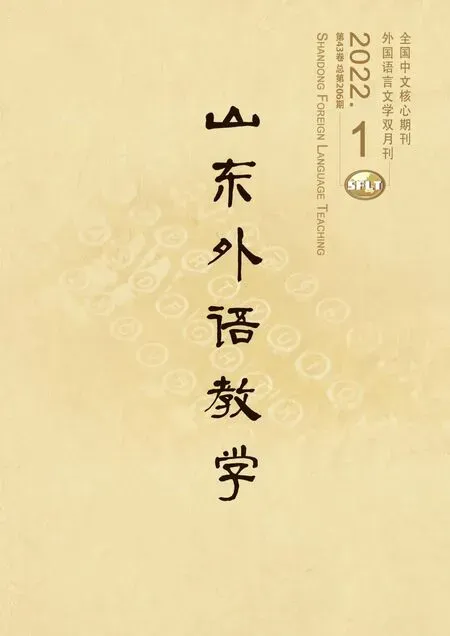學習者學業浮力:二語習得個體差異研究的新議題
劉宏剛
(東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1.引言
隨著近年來二語習得研究的“積極”轉向,研究者們開始探索學習者的積極品質對于維持動機和興趣的作用,引導學生積極應對外界挑戰(Kim et al.,2018),培養和提升學生的學業浮力①(Smith, 2015; Puolakanaho et al., 2019; Putwain et al., 2019),但是專門聚焦于二語習得中的學業浮力研究還不多見。深化學業浮力研究,可以從理論層面提升學業浮力作為學習者積極心理因素的關注度,為二語習得個體差異研究提供佐證。從實踐層面看,學業浮力研究能夠為學習者在二語習得過程中從容面對學習挫折,提升自我調節能力,優化二語習得效果提供參考依據,進而為提升語言學習質量提供助力。由于二語習得研究的跨學科特點(戴煒棟等,2020),有必要先理清學業浮力的發展脈絡及其在教育心理學中的研究現狀。為此,我們首先對學業浮力的概念和內涵追根溯源,而后對學業浮力在教育心理研究領域的研究方法和主題特點進行了回顧。最后,我們聚焦在二語習得學業浮力研究的主題和方法特點,并對未來二語習得過程中的學業浮力研究進行了展望。
2.學業浮力的基本概念
學業浮力這一概念最早由Martin & Marsh(2008a)提出,指學生成功克服日常學業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的能力。這些挑戰的范圍很廣,包括學業成績差、學習時間緊、考試壓力大、作業難度高等。二語習得過程中的學業浮力是該定義在外語學科中的具體化,是指“二語習得過程中,支持學習者應對日常語言學習的起伏,堅持不懈、克服挫折的能力”(Yun et al., 2018)。與浮力相似的概念是學業韌性(academic resilience),但學業韌性所面對的困境指的是學生遭遇的重大、長期的困境,它的主體通常指特殊困難情形下的少數群體,如貧困生、長期低成就者、學習能力差的學生等;而學業浮力針對的是所有學生,因為學生在學習中遇到困難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應對這些日常的學習起伏是學業浮力研究的核心(Martin & Marsh, 2009)。
3.學習者學業浮力研究的總體趨勢
為了了解學習者學業浮力研究的總體趨勢,筆者參考了Moher et al.(2009)提出的系統性評論和元分析的篩選過程,利用中國知網和SCOPUS數據庫進行了相關檢索。筆者分別以“學業浮力”“學術浮力”以及“academic buoyancy”作為關鍵檢索詞,以“主題”或“論文標題、摘要、關鍵字”進行檢索篩選,經過四輪篩選,共選出34篇SSCI文獻。其中只有3篇專門聚焦于二語習得領域內的學業浮力研究文獻。
自2008年學業浮力這一概念被提出開始,這一領域的研究陸續開展但并未全面興起。直到2013年,才迎來了第一個小高峰,此后一直起伏不定,并隱隱呈現出下降趨勢;2019年,相關研究迎來了一個增長節點,此勢頭延續到了2020年,達到一年內7篇高質量文獻發表的最高紀錄。而在二語習得領域,僅有的3篇文獻發表于2018—2020年,由此可見,二語習得領域內的學業浮力研究,在規模和深度上還有待擴充。
4.非二語學習者學業浮力研究主題和方法:特點與分析
由于二語習得領域內學習者學業浮力相關研究還很匱乏,所以我們首先對教育心理學領域的學業浮力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總結相關研究的主題特點和成果,從中探索未來二語習得學業浮力的研究方向與出路。在教育心理學中,已有的相關成果主要聚焦于學業浮力與社會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的關系研究以及學業浮力對學業表現的影響研究三個主題。
與學業浮力相關的社會文化因素包括教育、職業、文化背景等。在社會學特征方面,Yu et al.(2019)的研究表明,父母或看護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職業地位都與中學生的學業浮力呈正相關。此外,有學者開展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學生學業浮力情況的研究。對學業浮力進行的研究最初在澳大利亞興起,隨著研究的發展慢慢延伸到其他文化中,例如英國(Symes et al., 2015)、菲律賓(Datu & Yang, 2018)、中國(Yu et al., 2019)、芬蘭(Hirvonen et al., 2019)和土耳其(Aydln & Michou, 2020)等。對不同文化背景下學生學業浮力進行對比研究也是近來的研究特色。例如,Martin et al.(2017)對中國、北美和英國的12-16歲中學生進行了針對學業浮力和適應性、動機、參與度之間關系的對比研究。結果顯示,與北美、英國地區同齡的學生相比,中國地區的學生有著更高程度的學業浮力和適應性,三者之間的相關程度也更加顯著。
與浮力相關的心理因素研究主要包括積極因素(如動機)和消極因素(如焦慮)。已有研究表明,學業浮力與焦慮呈負相關(Martin & Marsh, 2008b; Putwain et al., 2016)。Putwain & Daly(2013)發現,浮力水平高的學生在考試中較少感到焦慮。當學生呈現低中度水平的考試焦慮、高水平的學業浮力時,可以在考試中呈現最好的表現。Putwain et al.(2015)的研究表明學業浮力與考試焦慮中的擔憂成分呈負相關,而與緊張情緒關聯不大。已有研究證明動機與浮力相互作用:一方面,動機因素例如自主性動機(Aydln & Michou, 2020)等可以顯著預測學業浮力;另一方面,浮力可以增強內部動機,從而間接優化學業表現(Datu & Yang, 2018)。
浮力對學業表現的影響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學業表現指的是學業成就、參與度、學習策略的使用、應對學業逆境等。研究證明,學業浮力可以優化學業成就(Miller et al., 2013),并且對不同學科(數學、英語、科學、體育等)的學習狀態都有所影響(Malmberg et al., 2013),對特殊學生(如多動癥群體)而言,學業浮力對學業表現的積極影響甚至更加明顯(Martin, 2014)。浮力還可以減少消極參與(Martin, 2013),例如在面臨學業挑戰時,減少回避行為,積極制定計劃等(Hirvonen et al., 2019)。學生的浮力水平越高,參與度也越高(Martin et al., 2017),學業浮力對學習者的行為參與和情緒參與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Datu & Yang, 2018)。在學習策略的使用上,浮力可以調節學業焦慮對學習策略使用的影響,在記憶、闡述、目標設定以及合作等策略使用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Collie, Ginns et al., 2017)。而對于浮力與學術逆境的關系,研究者發現學業浮力是幫助學生應對和克服學業逆境的重要因素(Martin & Marsh, 2020)。
在研究方法上,通過數據庫獲取的34篇文獻包括實證研究32篇,其中,定量研究有31篇之多,質性研究僅有1篇,未見到混合研究。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大部分研究聚焦于中學生(19篇,約60%),而對于小學生(6篇,18.75%)、大學生及研究生(4篇,12.50%)和混合群體②(3篇,9.38%)的關注度依次降低。由此可見相關研究在樣本的選取上存在著較大的不平衡性,研究者對基礎教育階段學生的浮力情況更為關注。在研究工具方面,以往學業浮力的常見工具是量表,以Martin & Marsh(2008a)的“一維度、四題項”的學業浮力量表(Academic Buoyancy Scale, ABS)運用最為廣泛。該量表在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下的學習者中進行了驗證性分析,如Datu & Yang(2018)在非西方環境(菲律賓)中驗證了其心理測量有效性和性別不變性。ABS最初應用于測量學生數學學習中的學業浮力,隨后逐漸被應用于多個學科,例如Malmberg et al.(2013)利用ABS探索了學生在不同學科(數學、英語、科學和體育)學習中的學業浮力差異性。
綜上所述,教育心理學領域的學業浮力研究揭示了學業浮力和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學習者因素(心理及學業表現等)的緊密聯系;研究對象以中學生為重點關注群體,而在其他群體中展開的研究相對較少;相關研究研發了一系列浮力測量工具,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定量研究方法的數量遠遠超過定性及混合研究。這些研究為開展外語學習者的學業浮力研究提供了給養。
5.二語習得研究中的學習者學業浮力研究:特點與分析
隨著積極心理學對學生正面特質的關注,對積極語言學習投入進行鼓勵的理念漸漸為人們所熟知,學業浮力也逐漸引起二語習得領域研究者的關注。Yun et al.(2018)首次將此概念引入了二語習得領域。此后,二語學習者的學業浮力研究植根于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從教育心理學的研究中汲取營養,關注浮力與其他心理因素的關系(Yun et al., 2018)、浮力的測量(Jahedizadeh et al., 2019),以及浮力對于學生二語技能的影響(Saalh & Kadhim, 2020)。
Yun et al.(2018)以787名韓國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探索了學業浮力與二語學習動機和成就的相關性。研究發現,根據學業浮力的高低可以將研究對象分為五類,分別是:繁榮成長型(the thriver profile)、積極投入型(the engaged profile)、努力成長型(the striver profile)、依賴型(the dependent profile)和脫離型(the disengaged profile)。此外,該研究還證明,自我效能、自我調節、理想二語自我這三個動機因素都能夠顯著預測學業浮力,而學業浮力能夠顯著預測學生的二語成績。除了對整體的二語學習成就有所影響,學業浮力的作用還體現在不同的語言技能上。例如,Saalh & Kadhim(2020)的研究在100名伊拉克大學生中展開,探究了學習者學業浮力在外語閱讀以及聽力技能上的差異。研究表明,學習者在閱讀技能上的學業浮力顯著高于聽力技能;此外,學業浮力在兩種技能中的預測因素也不同:在閱讀中,學生的浮力明顯表現在學術成就上,而在控制感上浮力較弱;在聽力中,浮力在師生關系因素上得以體現,而在抵抗焦慮方面不甚明顯。
二語習得學業浮力的已有研究均采用定量方法,研究對象均為大學生,并在工具開發上做出了一定貢獻。例如,Yun et al.(2018)針對學生在二語習得過程中遭遇的困境,對常用的ABS量表進行了改編,使之更貼合二語學習情境。Jahedizadeh et al.(2019)提出應更多地考慮到研究所處的社會背景、學校環境和學生的個體差異等因素,對于二語習得學業浮力制定更合適的測量方案,并據此開發了一套“4維27項”量表。量表的維度包括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即克服語言學習困難(如低分)的能力;規律性適應(regularity adaptation),即確立語言學習目標,定期進行學習規劃等;積極的個人資格(positive personal eligibility),即對于個人能力的積極看法,如相信自己能獨立完成學習任務等;以及對學業生活的積極接受(positive acceptance of academic life),即語言學習過程中的積極體驗,如能夠找到單一問題的不同解決方法等。該量表將學業浮力定位在二語習得領域,使測量更有針對性,而該項研究也是開發專門測量二語習得學業浮力工具的一次有效嘗試。
綜上所述,二語學業浮力的研究從教育學、心理學等領域汲取理論養分,關注外語學習的特點,揭示了學業浮力、外語學習心理、以及外語學業成就等因素之間的關系,但由于相關研究較少(僅3篇),因此在研究主題、方法和對象上都有較大的深入探索的空間。
6.外語學習者學業浮力研究展望
首先,未來研究要豐富研究視角,如積極心理學視角、生態學視角等,拓展語言學習者學業浮力研究的外延和內涵。在Oxford(2016)提出的積極心理學EMPATHICS③框架中,學業浮力與其中的毅力概念不謀而合,而對學業浮力的關注也正契合了外語教育研究的著眼點由消極向積極的轉變,因此后續研究可以探討其他積極心理因素與學業浮力的復雜關系,深挖這些因素與學業浮力在影響學習者語言習得過程中的作用。此外,采用生態學的視角,考察語言學習過程中個體因素與學習環境的互動(例如師-生、生-生、學生—學習任務—社會文化環境)也是學業浮力研究的一個新思路。二語習得過程與社會文化的密切聯系使得從生態學角度看待語言學習成為可能(van Lier, 2000),這種緊密聯系強調語境對語言學習過程的影響,凸顯了語言在教師、學生以及學習任務的復雜互動中的重要中介作用,充分體現了二語習得的動態性(Williams & Burden, 1997)。生態學視角下的二語習得研究關注互動過程中各個變量的“整體性”(秦麗莉、戴煒棟,2013)。因此,作為二語學習者的積極心理因素,浮力的產生與發展及其與學習結果的關聯必定也會受到這種復雜互動的影響。在學習者與語言學習這種特殊的“生態環境”互動中,從動態的、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視角研究學業浮力在二語習得過程中的角色有望取得新的研究進展。
其次,未來的研究要繼續從教育心理學已有成果中吸收養分,結合語言學習特點向縱深方向拓展。已有研究已經證明了學業浮力通過與社會或心理因素相互作用,影響學業表現。這種影響通常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一是浮力通過減少負面因素的影響,對學業表現起到緩沖和保護作用;二是浮力可以通過強化積極體驗(如積極情緒)等,優化學習結果。如學業浮力可以提升學生對外部支持的感知程度,使學生更有效地利用外部支持(Collie,Martin et al., 2017;Middleton et al., 2020),獲得他們在班級及學校環境中的歸屬感,從而增強迎接學術挑戰的動力,提升學習效果(Miller et al., 2013;Hirvonen et al., 2019)。語言習得與學習的過程是聽說讀寫等技能獲得和發展的過程,未來研究可以關注各項外語技能學習和提升過程中學業浮力發揮的作用。在培養學生自主英語學習能力方面探索學生學業浮力提升,保持樂觀心態,提高外語學習質量的有效途徑。例如,教育者可以通過提高學生的自我意識,培養他們接受和應對學業挑戰的能力,增強個人目標的設定能力,培養獨立行動的勇氣等干預措施增強學習者學業浮力(Puolakanaho et al., 2019)。
最后,相關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的選擇上要有所拓展。已有研究在“量”與“質”的方法使用比例上嚴重失衡,大部分研究以量化為主,開發了諸多學業浮力的量表,如ABS(Academic Buoyancy Scale)(Martin & Marsh,2008a)、SBI(Student Buoyancy Instrument)(Comerford et al., 2015)等,但質性研究的比例還有待提升。在收集數據時,可以更多地通過訪談、日志、影像等方式收集能詳細反映參與者真實經歷和想法的數據,通過質性研究的方法深入研究學業浮力。今后研究還可以考慮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綜合量化和質性分析的優勢(Creswell & Clark,2011),使研究結果更有說服力。此外,考慮到外語教學與研究的動態性及生態化取向(黃國文,2016),研究者還可以采用歷時的縱向研究,關注二語習得學業浮力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細微變化,從中總結其發展和變異規律。學業浮力對于二語習得的不同技能作用機制也可能各不相同,因此,可以采用實驗,探索學業浮力的作用機制,從而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教學實踐啟示。關于研究對象的選擇,教育學領域內的研究以中學生為主,小學生、大學生和混合群體的比例比較平均,而二語習得領域的浮力研究均聚焦于高等教育,對基礎教育的關注明顯不足。我們認為,未來的相關研究要避免類似的偏頗,努力發揮學業浮力在各群體中的積極作用,促進學習者在整個教育及成長階段的良性發展。
注釋:
① 根據Academic Buoyancy的內在含義,我們將其翻譯為學業浮力,強調的是學生在日常學習過程中克服學業困難、應對學業挑戰的能力。但為了避免翻譯差異而導致的文獻漏檢,筆者在CNKI數據檢索的時候用了“學業浮力”和“學術浮力”兩個檢索詞。
② 混合群體指的是參與者的年齡差距大,母語背景不同,外語水平參差不齊的學生及教師等。例如,Martin & Marsh(2008b)的研究對象為來自澳大利亞18所高中的高中生及教師,Martin et al.(2017)的研究群體為中國、北美和英國的中學生,上述文獻均被劃分為混合群體研究。
③ EMPATHICS框架包括:E: emotion and empathy; M: meaning and motivation; P: perseverance; A: agency and autonomy; T: time; H: hardiness and habits of mind; I: intelligence; C: character strengths; S: self factors(self-efficacy, self-concept, self-esteem, self-verification)。